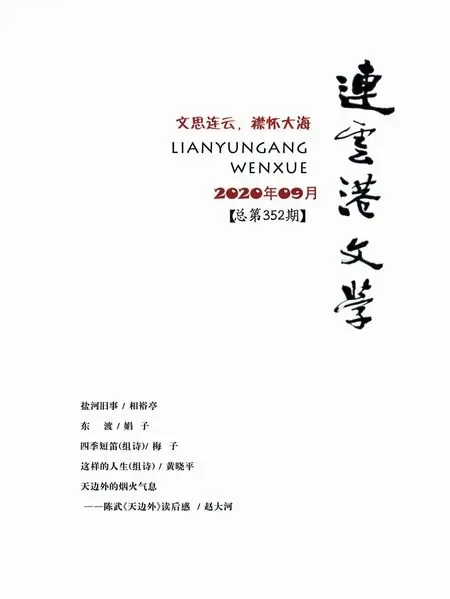盐河旧事
相裕亭
吞 扣
往日,日升三竿时,吴老爷可能早就坐上马车,跟田九奔城里听戏去了。可今儿,他连早饭还没来吃呢,大太太、三姨太她们都在小饭厅里候着。
吴老爷可好,他为内衣上的一枚小纽扣,正在大太太房里四处翻找。
昨晚,吴老爷在大太太房里说话,后来看天色过晚,就在大太太房里睡下了。早晨起床,吴老爷忽而发现内衣上的扣子少了一个。便喊住大太太身边的丫头兰叶儿,拉开窗帘,抖开床单,帮他床上床下地翻找。
那时,大太太已经先他一步,到厨房去帮吴老爷查看饭菜了。吴老爷却为一枚小小的纽扣儿,在那儿上火心焦。
吴老爷那纽扣,是东洋玩意儿,他可在意呐。
民国中后期,东洋人已经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经商。各种各样的花布、洋油、洋火等,随船过海而来。东洋人制造的物件儿,样样都比较精美、细致。像吴老爷所说的那种纽扣儿,不光是式样繁多,还分男女。
男扣,黑白两种。
而女式的扣子,就显得五花八门,红的、绿的、黄的,长的、方的、圆的,还有各种小动物状的,怪逼真,可好看呢!
可那个清晨,吴老爷为一枚小纽扣,把一家人吃饭的时光都耽误了。三姨太亲自过来请他去用餐,他还在那摸着衣衫,如同小孩子丢失了某个心爱的物件似的,痛惜而委屈地跟三姨太说:“我的纽扣丢了一个。”
三姨太说:“嗨,不就是一个扣子吗,再换一个就是了。”
吴老爷一脸惋惜,要找。
三姨太嘴角凝笑,她知道吴老爷赌场上一掷千金,可持家过日子,他又仔细得连一片被虫子嚼过的菜叶都舍不得扔掉。
三姨太说:“好好好,去找,去找,我这就叫人来找。”
三姨太问吴老爷这两天都去了哪些地方,她想帮吴老爷思量一下那枚纽扣可能丢在何处。
吴老爷支吾了半天,说:“也没去啥地方,无非是前院后院里走走,再就是来回的马车上。”
三姨太说:“那丢不了。”
三姨太问他:“是内衣上的扣子,还是外衣上的扣子?”
吴老爷说:“内衣上的。”
说这话的时候,吴老爷可能也觉得为一枚纽扣而兴师动众,多少有些小题大做了,便跟三姨太说:“算了,别派人去找了,就你陪我转转看看,找不着,也就拉倒了。”
三姨太依了吴老爷。
接下来,三姨太便伴着吴老爷从大太太房里出来,两个人就跟转着玩似的,从后院里慢慢地来到前院。他们先看骡马,又看工棚里伙计们的床铺,好像无心去找那枚纽扣似的,一路上两个人还悄声说了些天气呀、水井呀什么无关紧要的事儿,有意无意间,他们来到大管家陈三的住处。
陈三虽说也同伙计们一样住在前院里。可陈管家的住房相对比较宽敞,里外两间,卧室的那一间,还留有一个可以观望到后院的小格窗。晚间可兼管前后院里的动向——防贼呢。
吴老爷说他昨天午后,到陈三屋里喝了杯茶,没准那枚纽扣就掉到他房里了。
三姨太没有吱声,但三姨太提醒吴老爷,说:“这阵子,陈三怕是不在房里。”
陈三忙呀,家里家外都是他在张罗。尤其是盐区那边,每天收购上来的海盐,堆成小山一样高,陈三要在那儿指挥伙计们,天南地北地发货。再者,就是吴家上下,上百口子家眷、奴仆、盐工的吃喝,都离不开他陈三打理。应该说,这些年吴家盐田的生意越做越火,与陈三的操劳有着很大的关系。
吴老爷对陈三也不错,隔三岔五地把他叫到后院,让后厨炒上几个小菜,有事没事地陪他喝上几盅。天气冷了暖了,吴老爷总是第一个想到陈三该加被子了,或是该挂蚊帐了。
这些,说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可陈三打内心里感激他的大东家。陈三尽心为吴家效力,为吴老爷效力。
陈三把吴家当作他自己的家。在吴家莫大的家院里,凡是东家能去的地方,他陈三也都能去。陈三掌管着各个房门的钥匙。而吴老爷只掌管陈三门上一把锁头。
吴老爷把陈三房门的钥匙交给三姨太,让三姨太把陈三的房门打开。三姨太接过吴老爷那串铜的、铝的钥匙,一连试了好几把,都没有把陈三门上的锁头打开。
吴老爷提醒她,你试试那把黄铜的小钥匙。
三姨太按吴老爷所说的一试,那锁头果真是开了。
吴老爷坐到里间靠床边的一把木椅上,让三姨太帮他在陈三房里的地上、椅上、床上去找他那枚纽扣儿。
吴老爷说他昨天午后,在陈三的被垛上靠了一会,那扣子会不会掉到陈三的床上了。三姨太猫下腰,床上、被垛间、包括枕头底下,她都仔细地找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吴老爷一脸疑惑地站起身,并用手中的拐杖挑了挑陈三枕边的毛巾,说:“这里呢,你找过没有?”
三姨太惊诧了一下,但她很快又镇静下来,说:“找过了,没有。”
吴老爷轻“噢”了一声,说:“罢了,没有就罢了!”说话间,吴老爷两手往后一背,独自前头走了。
岂不知,刚才,三姨太在陈三的枕边,确实是找到一枚小纽扣。但,那不是吴老爷的扣子,而是她三姨太内衣上掉下来的一枚花纽扣儿,惊诧之中,三姨太趁吴老爷没有在意,悄然把那枚豆粒大的小纽扣吞进自个儿的肚里了。
打 鸟
一夜大雪,天亮以后,吴老爷想去海边打鸟。
那时间,盐区的沟壑、盐田,还有通往海边的道路,都被白茫茫的大雪所覆盖,哪里去寻找可以猎杀的海鸟呢。可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偏要陈三陪他到海边去散心。
陈三跟正在套马的田九鼓嘴说:“这样的鬼天气,大海边只怕是连只海鸟的影子都找不到。”可吴老爷兴致来了,他陈三和田九,一个是吴府里的管家,一个是大东家的马夫,东家要去打鸟,他们自然要陪着去乐呵乐呵。
结果,海鸟、野兔是一只没打着,陈三的小命却丢在海滩上了。起因是,猎枪走火了!
那一枪,原本是大东家抱着枪管,教田九去打一群栖息在一艘破渔船上的海鸟的。田九胆怯,他没有玩过枪。吴老爷手把手地教他,枪托要抱稳,瞄准要盯紧,等到大东家教田九扣动板机时,只听“统!”的一声枪响,栖息在破船上的鸟儿掠起一片雪雾飞走了,身边的陈三却“扑通”一声,栽倒在旁边的水沟里。
事情经过就是那样。
田九当场就吓傻了!
大东家却连呼:“田九,田九,你可惹下大祸啦!”
懵懂中的田九,感觉他没有去扣动扳机,那枪怎么就响了呢?吴老爷却大声吼道:“走火,你弄走火啦!”
田九傻呆呆地戳在那儿。吴老爷呵斥他时,他还在那儿怀抱猎枪,两眼发直,右手的食指正扣在扳机上。
死人的事,很快报到县里。
县里来了两个衙役,当场就把田九五花大绑地给捆扎起来。
临上路的那一刻,大东家吴三才当着田九的面,把两个衙役戳到一边,各赏了两锭银子,再三叮嘱他们:“路上,别让田九受了委屈。”
那两位衙役接了银子,点点头,都没有吱声。
吴老爷说:“田九喜欢喝点烈酒。”言外之意,路上用餐时,可以适当地给他弄点烈酒喝。
吴老爷说:“出了盐区,你们可以把他身上的绳子松一松。”
吴老爷说,田九那人怪老实呢。言外之意,即使给他松了绑,他也跑不了。可那两位衙役,不管吴老爷说什么,他们始终黑着脸儿不作声。
田九呢,在那两个衙役捆绑他的时候,他很顺从。他似乎早就知道县里要来人抓他了。
此番,衙役们给他上了绳索,田九四处张望寻找大快。吴老爷从人群中把满眼泪水的大快扯过来。
田九训斥大快:“你哭什么,好好听吴老爷的话。”
大快点点头。
田九好像还想跟大快交代什么,却被吴老爷用身板给隔开了,吴老爷告诉田九:“大快的事,你不用操心。”吴老爷没好说,以后,大快那孩子,就包在他吴老爷身上了。
田九拿眼睛直瞪大快,并隔着吴老爷,训斥大快,说:“你好好听话!”
田九说的“好好听话”,显然是让大快好好听吴老爷的话。之前,大快在吴家犯过错,吴老爷原谅了大快。田九打心窝里感激吴老爷。
说话间,街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田九心里想,快点上路吧,没准到了县衙,或出了盐区以后,那两个衙役给他松松绑,他会好受一些。要不,那细细的麻绳儿,紧勒到他的肉里去,怪疼的!
田九知道,打死陈三的那一枪,不应该算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是大东家吴老爷教他那样瞄准和扣动扳机的。可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话就不能那样讲了。吴老爷塞了田九不少银两,并交代他把事情暂时揽过去,待以后事态平息了,他吴老爷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来。
所以,县里来抓他的时候,田九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还十分配合。以至于那两个衙役押他上路的那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
在田九看来,他这样慷慨赴刑,是对吴老爷的一片忠诚。
但是,田九始终没有弄明白,吴老爷在教他打枪时,怎么就走火了呢?那一枪,原本是去打鸟的,怎么一家伙把陈三给搁在水沟里呢。
为这事,三姨太也曾起过疑心,三姨太拐弯抹角地问田九:“你打死陈三干什么?”
田九不语。
“有仇?”
三姨太知道,之前陈三带人割掉了大快的半拉耳朵,但那也不至于以命来抵换。所以,三姨太问田九:“你打死陈三,就不怕抵命?”
田九呢,他不想跟三姨太多说什么。因为,有些话,吴老爷已经交代他了。他只说,打死陈三,是他玩枪走了火。
可田九越是那样说,三姨太越觉得这其中有诈。三姨太知道,田九从来就不会打枪。
现在,田九把一切罪责都应承下了。
大堂上,几乎没用一棍一棒,田九便签字画押了。田九盼望的是吴老爷早点来保释他,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是秋后问斩。
行刑的当天,田九一看,真是死到临头了,他想翻供。可为时已晚,押赴刑场时,他脖颈上被人勒上了一根比筷子更细的细麻绳儿——让他失语。
事后,三姨太托人打听到,吴老爷为让田
九“失语”,先后往县衙里送了好几百两银子。那一刻,三姨太惊诧了!
绑 票
吠声急促的时候,匪徒们已经包抄了吴家的前后院落。
那帮匪徒,对吴家的情况好像很熟悉。他们上来先把吴家前院里的家丁们给控制住,呵斥他们:
“不许动!”
“谁动,就打死谁!”
随后,那几个蒙头盖脸的家伙,还教导被堵在被窝里的伙计们:“好狗,看好自家的门!”言外之意,眼下他们打劫的,是大盐商吴三才,与他们下苦力的伙计们没有关系。
说话间,有一个年纪尚轻的小土匪,走到伙计们睡觉的地铺前,还很轻狂地用脚尖踢踢他们的枕角,呵斥道:“不许动,嗯!好好睡。”
可此刻,翻墙潜入吴家内宅的匪徒,已经开始破门、捣窗了。
正在睡梦中的吴老爷,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喊身边的三姨太:“快,快起来!院子里进贼啦!”
说话间,吴老爷随手摸过枕边的短枪,冲着窗口,“咣!”的就是一枪。
吴老爷认为,盗贼们闻到枪声后,就会抱头后退。
岂不知,枪响以后,原先躲在墙角、蹲在檐口下的匪徒们,呼啦一下子,破门而入。
匪徒们早已知道吴老爷枕边的那杆短枪里,平时只压着一颗子弹。一旦吴老爷短枪里那颗子弹射出以后,再去拉动枪栓,重新按压子弹,那是需要时间的。
匪徒们就是在吴老爷按压子弹的间隙,呼啦一下子,涌入到三姨太卧室的,也就是吴老爷与三姨太睡觉的那间房子。
“不许动!”
一个眼尖手快的匪徒,上来先下了吴老爷手中的枪。
随后,一个高个、黑脸的家伙(匪首),踩着叮叮当当的皮鞋声,跨进三姨太的房中,但他并没有急着进三姨太的卧室,而是进门划一根洋火,先给自个儿点上一支烟,发现正厅的八仙桌上有盏洋油(煤油)灯,就手把那油灯也给点上了。
吴老爷没想到会是这样。
吴老爷被匪徒的枪管抵在床头,待外间的油灯亮起以后,有两个匪徒反拧着他的胳膊,将吴老爷擒到外间来。
油灯前,那个黑脸、高个的匪首,不紧不慢地走到吴老爷跟前,恶狠狠地瞪了他两眼,二话没说,上来就是“叭!叭!”两记耳光,质问吴老爷:“妈的,开枪打谁呢?”
吴老爷抖抖索索地说不出话来。
匪首一手捏住吴老爷尖瘦的下巴,一手晃动着他手中的盒子,问他:“你看看这是什么,大爷没给你还手,是给你面子了,懂吗?”
吴老爷抖动着他那有数的几根山羊胡子,战战兢兢地说:“哪路来的‘财神’?有话好说。”
匪首说:“少废话,你知道大爷今夜登门,是来干什么的吗?”
吴老爷说:“小老不知,小老不知。”
这时候,有人在里屋划亮火柴,高声喊道:“大哥,三姨太在这儿。”
那时候,三姨太已经从床上起来,正端坐在床前的一把椅子上不紧不慢地系着内衣上的花纽扣,她睬都没睬眼前那几个狂呼乱喊的匪徒。
外间的客厅里,匪首拿眼光威逼着吴老爷,问:“听到了吧,三姨太可在你里间里,是不是领出来,给爷们瞧瞧?”
吴老爷知道他们要糟蹋三姨太,连连苦求,说:“使不得,使不得!”并问那匪首:“哪路来的弟兄,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吴老爷想问他们需要多少银子。
那匪首却打了个手势,让把三姨太带出来。
三姨太呢,她嘴角咬着一根红头绳,正梳着蓬松的头发,斜披一件小花袄,从屋里出来时,可能是因为一时慌乱,袜子没来得及穿,趿一双紫花的红绣鞋,面团一样的脚面儿,迎着灯光走来时,一闪、一闪,可惹眼!
她撩匪首一眼。
匪首也看她一眼。但那匪首很快又把目光转向了吴老爷,问:“我们那边有点针线活,想请三姨太去辛苦一趟,你看怎样?”
吴老爷一听这话,立马苦求,说:“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匪首上来就是一拳,正打在吴老爷的脸上,骂道:“给你留条老命,就算是对得起你了。还不知趣!”
说话间,匪首打个手势,让把三姨太带走。
三姨太呢,她让匪徒们闪开。她自个儿进屋,点亮一盏更为光亮的油灯,先是对着镜子把眉眼描了描。接下来,她又里一件、外一件地穿戴整齐后,找出夏天的裙子、春秋的风衣,还有冬日里她喜欢围的那几条粉的、白的、蓝底白花的围巾……一件一件叠展整齐,打进包袱,如同主人吩咐奴才一样,让左右的匪徒们,给她一样一件地拎上。
最后,临出门时,三姨太还把床头两张她喜欢的挂画也取下来,卷了卷带上了。
吴老爷不知道这些,三姨太收拾东西时,吴老爷被匪徒们用一块黑布蒙上了眼睛,绑到当院的树上。
三姨太从屋里出来时,脚步很轻。吴老爷似乎没有察觉到三姨太从他身边走过。
后来,吴老爷听到院外吠声再次急促了,他这才知道匪徒们已经绑走了三姨太。
那时刻,吴老爷急了,他不等家人们把他身上的绳索完全解开,便猛追出院落。期间,匪徒们发现后边有人追赶,“咣!咣!”对天放了两枪。
吴老爷知道,那是给他的警告。再追,可能就有危险了。
当下,吴老爷与围护在他身边的家丁们,都很无奈地停下脚步。大伙儿一起望着远处一群晃动的黑影时,吴老爷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
“骚货!”
撕 票
兰枝在三姨太身边历练过。所以,三姨太走了以后,吴老爷就让兰枝把三姨太掌管的那摊子事儿暂且支应起来。这也正是后人所说的——吴府里管事的是个丫头。
最初,兰枝、兰叶,都是大太太房里的丫头。后期,大太太吃斋念佛,不怎么过问家里家外的事了,兰枝便被调到三姨太那边去了。
而今,三姨太被土匪们劫去,兰枝接管吴府内务,也算是轻车熟路。只是遇到大一点的事儿,兰枝不敢做主,她还要去请示大太太拿主意。
大太太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时而心烦了,一句话也不讲。
所以,三姨太被土匪劫走以后,大太太就跟吴老爷嘀咕:“家里丢只小狗小猫,还要出门去召唤召唤,你怎么不去打听打听三太太的下落呢?”
吴老爷心里正憋着一股气呢,他本不想去过问三姨太的事。
吴老爷觉得三姨太此番离去,不像是被土匪给劫去的,倒像是与土匪们里应外合,而另求新欢。这其中,也不外乎陈三吃了枪子以后,三姨太受到惊吓,她似乎意识到她与陈三的事,吴老爷已经觉察到了。所以,三姨太要离开吴老爷了。
而今,大太太既然那样说了,吴老爷思量再三,那就找个黑道上的人,打探打探三太太的下落吧。
于是,吴老爷想到了张大头。
张大头是什么人?地痞、无赖、盐区这边有名的混混。可那家伙脑子活套,什么人在盐区耍得开,他就往谁的身上靠。他手下纠集着一伙子人。名义上是维护盐区的一方平安,实则是吃大户、抢财主,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此人精通于黑白两道。吴老爷找到他时,还专门摆了一桌酒席。
酒宴前,吴老爷让兰枝丫头先呈上两块银锭。言下之意,那是探路钱。
张大头吞惯了大户人家的钱财,看到吴老爷呈上来的银子,眼珠子瞬间一亮,随之,蒲扇般的大手一挥,冲着他身边的王副官,说:“这事情,就包在王副官身上了。”
王副官满脸堆笑,他一边帮张大头收下银子,一边向吴老爷承诺,说:“小事情,小事情。”听他那口气,好像他立马就能把三姨太给找来似的。
吴老爷也觉得,尔等小事,只要他张大头用用心,应该不在话下。
果然,事隔两天,王副官来吴府禀报,说三姨太被太阳山上的钱三爷给掠去了。
钱三爷是苏北、鲁东南一带,最大的一股土匪,他手上有一百多号人,长年盘踞在太阳山上,专挑盐区的大户打家劫舍。而太阳山,顾名思义,太阳升起的地方。它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周边悬崖陡立,易守难攻,官府想缉拿他们,可一直没找到可行方案。
吴老爷想不明白,三姨太怎么去了那样一个鬼地方。
在吴老爷看来,三姨太此番被劫,应该步入一家更为敞亮的高门大院。吴老爷甚至想到,三姨太换了个环境,没准她会更加光鲜靓丽!
现在好啦,王副官打探到的结果是,三姨太上了太阳山。
吴老爷觉得这很意外。一则,三姨太不适应那种孤岛求仙的日子;再者,那天晚上,劫走三姨太的那个黑脸、高个的匪首,好像不是传说中的钱三爷。
但是,吴老爷当着王副官的面儿,他不想把话都挑明了。吴老爷跟王副官打哈哈,问:“你看到三太太啦?”
王副官支吾了一句,说:“只是远远地打了个照面。”随后,王副官报出钱三爷所要的赎金——五百现大洋。
吴老爷沉思良久,摇摇头,说:“罢了,随她去吧。”言下之意,他不想花那个冤枉钱。
吴老爷觉得三姨太此次离家出走,不是金钱能赎回她的心的。
可王副官不晓得这其中的内幕,他顺着三姨太被劫的思路往下说。王副官告诉吴老爷,钱三爷只给了三天的期限。
三天以后,吴老爷若拿不出五百现大洋,对方可就要撕票了。
果然,三天以后,王副官再来吴府时,带来了一个香烟盒大小的小锦盒,吴老爷一层一层地打开以后,里面包裹着的,是三姨太的一根小手指头。
王副官说:“钱三爷有话,隔一天,还会有更新的物件呈送到吴府来。”也就是说,隔一天,你吴老爷再不把五百现大洋捧出来,对方就要割三姨太的耳朵、鼻子了。
吴老爷知道那是土匪们的要挟,但他依旧摇摇头,说:“随她去吧!”
这下好啦,土匪有土匪规矩。他们说到做到。第二天给吴老爷呈来的,果然是一个更大一点小锦盒。
但这一回,吴老爷没有急着去打开。吴老爷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王副官聊起三姨太在那边的事。
王副官一看吴老爷关心起三姨太,面部的表情,顿时凝聚起一片阴云,他长吁短叹地说——
“那罪遭的,可真不是人受的!”
说到痛心处,王副官的泪水都快要掉下来了。
吴老爷也跟着难过了一阵子。但吴老爷在王副官愈说愈伤心的时候,他顺手从茶几底下,摸出前一天王副官送的那个小锦盒,轻轻地推到王副官跟前,问:“你帮我看看,这是三太太的断手指吗?”
王副官当即把脸贴到那锦盒上,好半天,他都没好抬头去看吴老爷。
原来,那锦盒里的半截断指,是王副官从乱葬岗的小死孩身上割来的,粗细与三姨太的纤指差不多。但,三姨太那指甲似小鸟的蛋壳,而锦盒里那顽童的指甲,却薄如蝉翼。
至于三姨太此番在哪,她跟着什么人跑了,王副官压根儿就没有打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