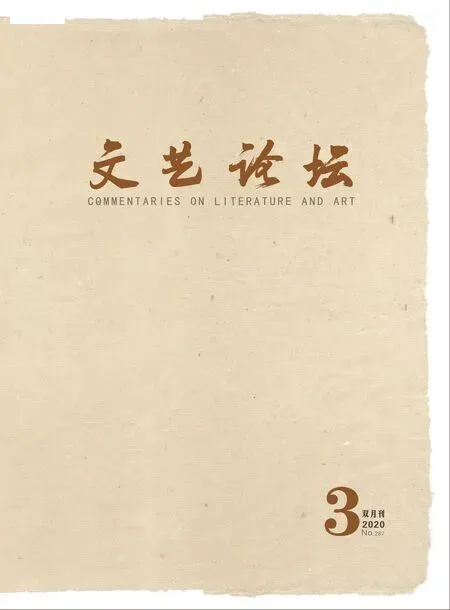文学或科学,生存与毁灭
——评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
◎ 刘诗宇
那就是,通过重复使用这些文学模式、语言结构、情感类型,消耗干净语言的抒情性、文学性。或者说,消耗干净语言、逐步清除文字,是这个答案的两部分。毕竟,抒情性的语言是最麻烦的。通向国王的不朽的路上,所有耽延人类的语言障碍物、文字绊脚石都来自文学,文学就是人类自身的病菌,抒情就是上帝驱逐亚当、夏娃时铭刻在他们身上的诅咒。
——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
一、“跨界”之作的意义
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是近些年长篇小说中的一个“异类”,已经很久没有作家以“严肃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去写“科幻小说”了。
在欧美地区,科幻文学因为发展早、成果多,与传统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并不鲜明。甚至很多严肃文学作者会将科幻作为一种“方法”,探讨现实主义创作无法触及的问题,比如著名的《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等。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科幻与严肃文学之间的互通则较少。近现代时期,一些最受尊敬的文学大家也写科幻小说,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的《猫城记》等。与西方作家近似,梁启超、老舍也是在借超现实题材,讨论一些深藏在现实之下的问题。但是到了当代文学阶段,严肃文学作家“跨界”创作的情况实属罕见,凤毛麟角的一些个例,无法掩盖科幻文学与严肃文学分离的趋势。高校在设置学科与专业时,将科幻文学放在了“儿童文学”的范畴中;从文学的传播和生产上看,科幻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类型”,被汇入通俗或类型文学之中,一些象征着严肃文学的期刊上鲜有科幻小说出现,主流的评奖中几乎也看不到哪个作家以科幻创作上榜。与之相对应,主要研究严肃文学的学者与批评家们也较少将科幻小说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
继莫言荣获诺奖之后,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则第二次提供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想象。严肃文学界对科幻文学的讨论多了起来,但二者之间的壁垒仍然存在,因为刘慈欣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内的“科幻圈”而不属于“严肃文学圈”。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与抒情诗》的意义是明显的。李宏伟的身份更像是“严肃文学作家”(这样的概念也属不得已而为之,动态鲜活的当代文学中,总有一些难以名状但又确实存在的群体与场域),《国王与抒情诗》首发于《收获》,这是国内严肃文学的最高舞台之一,作者的身份与文本的状态决定这部小说为打通当代严肃文学与科幻之间的壁垒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便《国王与抒情诗》作为科幻小说无法达到《三体》的高度,但是当以“十七年”文学、先锋文学为研究对象、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为方法的批评者们开始尝试言说这部作品,“茅盾文学奖”等主流文学奖项将这部作品纳入考量范围,这种“打通”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二、未来想象:科技带领资本,公司取代国家
即便是像《星球大战》那样借着科幻的外壳,讲老套的中世纪骑士故事的作品,也为受众提供了完全迥异于现实的“设定”,例如无坚不摧的“光剑”、种类繁多的外星人形象等。作者提供了那些对技术的设想,社会制度的推演,日常生活的变化的想象——为受众提供怎样的“脑洞”?这始终是科幻小说接受评价时面临的第一个诘问。
《国王与抒情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不远的将来——小说给定的时间点是2050 年,视觉层面虚拟与现实的障碍已经打破。
例子是小说中描写了一种被称为“自在空间”的技术,虚拟时空中的信息、图像可以无障碍地投射到主体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这种投射不是从神经层面对感官的一种“欺骗”,除了使用者,其他人也可以看到“自在空间”中的内容。
第二,藉由“意识晶体”“移动灵魂”和“意识共同体”,人和人之间的意识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
意识晶体指的是一种植入人类身体中的微小设备,可以实现对人感官、记忆、思想的捕捉,并将其信号化。移动灵魂近似于进化后的手机,负责发送与接收这些信息。意识共同体指的则是一种近似于互联网,但从根本上取代了互联网的新型信息交互、储存平台。以意识晶体的信息捕捉、编码、传递功能为基础,人们在意识共同体上可以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方式交换、获取信息。这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的意识相互连接,因而成为了“共同体”,人类意识的可塑性也不断增强,掌控意识技术的人甚至可以实现对个体未来的全面控制。
第三,这种技术的运行对人工与资本的要求相当高,尚未发展至自足状态。因此这种技术必然以商业形态出现,由某一公司集中运营。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资本与权力的转移,必然波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国王与抒情诗》中的“国王”指的就是拥有并垄断意识共同体技术的公司的掌权者。公司对于国家的取代在小说中已是明显趋势,在一个高度信息化、信息可操控化的社会里,“国王”的权威超越了民族与地域的界限。
第四,一切皆可信息化,包括意识与记忆。这导致资本与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催生关于永恒或永生的“妄念”。
作者塑造的“国王”形象兼具“专制君主”与“哲人王”的特点,他希望以意识共同体系列技术将人类的思想或“灵魂”完全信息化,进而通过注入其他肉体的方式实现思想的永生与统治模式的永久延续。在这方面“国王”类似于那个希望让自己的国家二世三世直至万世统治的始皇帝。但与此同时,“国王”作为人类的面目又是极为模糊的,这使得“国王”显得相当神秘,他缺乏人类情感,或者说他的种种情感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一种伪装成感性的理性。关于企业的运转和人类的未来,他有一套清晰的理念,即消灭语言的“抒情性”,就相当于取消了语言的“歧义”,语言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方案”,阻碍了人类的交融与统一,一旦语言的“歧义”消失,通过意识的交流,人类将重新“一体化”,进而实现群体性的“永生”。
作为一部严肃文学与科幻文学的“跨界之作”,《国王与抒情诗》延续了前人的设想和现实的趋势。例如人类将意识接入网络的构想,在1980 年代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系列中已经出现;意识晶体、移动灵魂、人类意识数字化的概念在2011 年上映的《黑镜》电视剧中有近似的呈现;通过阉割人类个性以实现大一统的理念也曾在世纪之交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完结于2014 年的《火影忍者》中风靡世界;“公司”对于“国家”的取代,在1930 年代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1980 年代“神经漫游者”三部曲中已经有了雏形;又比如文中最重要的设想“国王”与他以“帝企鹅”为名的巨型企业,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马化腾和“腾讯”公司(以企鹅形象为标志) ……
但是《国王与抒情诗》在这种继承中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新变,例如对“公司”代替“国家”的描写。1932 年的《美丽新世界》中,人类生活在“福特纪元”——生产汽车的那个跨国公司的名称,直接变成了全人类的年号。而社会的运行方式,也与福特公司创造的“流水线”模式高度一致,极端追求“效率”的公司制度作为一种可行的统治形式,加剧了人们对极权的恐惧。在“神经漫游者”三部曲中跨国公司对政府的取代,与当时崛起的日本经济威胁美国、跨国金融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有关(作者威廉·吉布森是美国人),当然,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从1970 年代末期开始,类似“神经漫游者”这样的“赛博朋克”小说中,日本文化就时常是作者们向往、焦虑的核心。
而在《国王与抒情诗》中,一切矛盾似乎都是“内部矛盾”,小说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和“国王”看上去都是中国人。主人公名为“黎普雷”,这看上去是一个音译的欧美名字,但实际上主人公姓黎,名普雷——虽然不知是否向“异形”系列主角“雷普利”致敬,但这是地道的中文命名方式。小说并没有体现出对国别、民族问题上的焦虑,一切问题的焦点在于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与权力高度统一。
通过意识、信息方面的技术,“帝国文化”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操控,这种操控甚至能够精确到客体写下的一字一句,甚至小说中宇文往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操控的结果。宇文往户真的写出了诺奖级别的文字,但这不再是他个人才智和创造的结果,而是“帝国”公司通过掌握一切信息,再反过来渗透到宇文往户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进而完完全全塑造了这个人。
这个极端的例子生动诠释了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有关话语的学说。过去反乌托邦文学里的暴力、镇压不见了,资本让技术运转起来,由此公司对个人的控制已经水到渠成、无需强制。
三、科技或文学,毁灭者还是救世主
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唯一贡献……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编织出了真正的事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画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哪里呢?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唯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丹·西蒙斯《海伯利安》
在开篇部分我复述的《国王与抒情诗》中的一段话,与丹·西蒙斯在《海伯利安》中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正体现了科幻文学内部的一种传承。科幻文学是一种文学类型,但科幻在很多时候也超越了类型的范畴,成为探讨现实问题或思想问题的一种方法。《海伯利安》和《国王与抒情诗》之间的共鸣,正为我们探索、摸清这种方法的情况与意义提供了线索。
西蒙斯借小说人物之口,指出在科学技术发展到匪夷所思的阶段时,反而文学和语言才是人类最值得称道的发明创造。技术改变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这毋庸置疑,但论及人类对宇宙的贡献时,语言——人类的语言具有唯一性。因为其他技术都是对既有物理、化学技术的运用,是一种“发现”,而只有词语才是真正的无中生有,是一种“发明”。
李宏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语言和文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使人类的灵魂永生成为可能,抒情、语言代表的个体差异则成了唯一的障碍。在李宏伟架构的未来世界里,公司代替了国家,在科学技术面前政治、经济、军事也许“不值一提”,而能够和技术站在同一高度并阻止技术进一步改变人类的,只有文学和语言。
西蒙斯或李宏伟谈论的都不是构成了《海伯利安》《国王与抒情诗》或其他少数故事的字词,而是语言本身。在他们的讨论中,语言就像一个不停翻转着的硬币:一面是无可奈何,人和人之间必须交换信息却找不到一个没有“延异”、比文字更好的媒介;另一面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语言的存在见证着人的千差万别,差异性就是个性,是美好而不可或缺的。
“国王”希望消除语言,打通所有个性,让人类变成一个统一、永恒的存在。这让人想到《圣经》中上帝担心人们建成巴别塔,将自己的天庭刺穿,因此用语言将个体分开,让人永远也成不了上帝。但是《国王与抒情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人如何推翻上帝统治的“革命”寓言。作者无疑看到了语言或文学对人的束缚,以及人类这种动物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但作者也深深沉迷于这种“残缺”——抒情和人性正由此出现。而在故事的结尾,小说又卖了一个充满“歧义”的关子,如若人变成上帝,发现上帝其实拥有另一种“抒情”,那么人类之前的抱残守缺是否失去了意义?
“等你执掌这个庞大帝国,明白它十多万员工的运作,看到世上数十亿人如同漫天星宿,看似毫无规律,实则精密地绕着帝国的‘主脑’旋转、汇聚、奔流,等你体会到我今天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运思推演的结果,而不是妄念与狂想控制下的信口开河,你会明白,这是另一种抒情,与你的抒情实为人类之两翼。至于这两翼会合力飞向何方,我有我的确信,但我不后悔、不惧怕任何结果。这不是赌一把,这是帝国的抒情……”
结局部分,“国王”向黎普雷揭示了有关帝国、意识控制、消灭语言、人类永生计划的一切,并邀请黎普雷成为第二代“国王”。在黎普雷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一邀约之前,故事结束了。
当读者翻到下一页时,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刚刚结束的只是“第一部”,接下来还有“第二部”。第二部有70 页的篇幅,但里面却没有完整的人物、故事,通篇都是意义不明、没有标点的短句或词语。极端者如第8 章,全由吃、呦、咳、哼、啧等“口字旁”的字组成。我不想用“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之类的词将其一笔带过,身为读者,我想姑且对作者的意思进行猜测,这大概是作者在描述不同人的记忆,通过意识晶体汇合到同一个场域之后的情景,无数碎片化的情景、感受在同一个空间中以文字的形式激荡着,形成一幅极为混沌的画面。而那些“口字旁”的字,则在提示我们文字原本的多样性,3 页密密麻麻的小字,其实仍未穷尽所有的“口字旁”汉字,而已经列出来的这些字里,至少已经有三分之一已经相当“陌生”,“消灭语言”也许危言耸听,但我们正处在语言丰富性流失的过程之中。
在第二部后面,还有五篇极为短小的附录,写的是与意识共同体等技术有关的一些生活细节。《国王与抒情诗》的结局是开放的,但从附录描写的未来世界看,“帝国”以及相关的技术基本在“国王”预言的轨道上发展着,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令人失望,但似乎也不一定更好。
评价《国王与抒情诗》这样的作品很难,它的故事层面与思想层面是“两重天”。从故事的角度看,它提供的技术设想在前人的作品里已现端倪,全书后三分之一颇为独立的高潮迭起,让前三分之二的铺垫显得有些漫长。与其他优秀的科幻小说相比,《国王与抒情诗》也许并不是最出彩的作品之一。从思想的层面看,这部作品背后的东西隐藏很深,深到甚至可以和故事本身分而治之,但这种思想确实有着无底洞般的可阐释性,尤其是当其与科幻小说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时。并且在阐释思想的过程中,作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立场,最后“国王”对于意识数据化的“抒情”阐释,说明作者基本是用“进化论”的眼光在看待故事里人类的发展。“存在”即是“合理”,未来看似“泯灭人性”的变化,其实用古老的“抒情”概念一样解释得通。
这部作品在讲故事和阐述思想间的游移,一如主人公黎普雷在“继承”与“拒绝”之间的犹疑,二元对立的背后,是资本与技术掌控的时代,与有着情感和灵魂的人的对立。不仅是作者,也许整个时代里也没有多少人能从中得出确切的答案。相比之下,更重要的应该是用文学的方式提出问题,以及解释问题的尝试。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完成了任务,借着《国王与抒情诗》,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当代严肃文学和科幻文学有进一步的交融,期待这一类问题在更多作家的笔下呈现、深化。
注释:
①⑤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中信出版社2018 年版,第191 页、第255 页。
②无论从身份的归属,还是主题的类别、作者本人的价值观上看,《国王与抒情诗》和《三体》都属于两种路子。《国王与抒情诗》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作为科幻作品的阐释,而《三体》从出现之际就是“纯粹”的科幻小说,以至于其思想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国王与抒情诗》强调情感在技术发展面前的特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启蒙主义思想观念;在《三体》中,人类文明在先进文明的威胁下体现出的愚昧与智慧充满一种冷酷的“进化论”色彩,相比之下人类的所谓理智与情感反而常常将人类引向歧途。
③就像刘慈欣将人类在面对三体人时的行动写得极为具体,但整篇小说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三体人形象,因为这是目前人类认知范围内不存在之物,强行塑造只能降低神秘感。
④[美]丹·西蒙斯著,潘振华、官善明、李懿译:《海伯利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版,第216-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