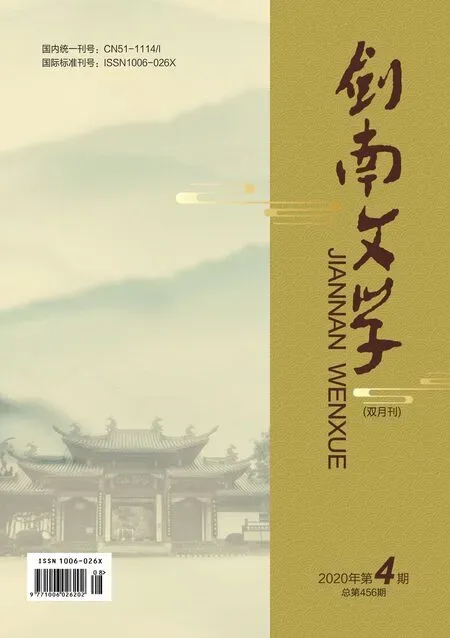屋顶上的猫
□亚 男
1
张是这个小镇食品站的,是不是有庖丁解牛的技艺,在小镇众所周知。他养了一只黑色的猫。
几只猫在屋顶上,那么悠闲自在。一只灰色的猫,和一只花色的猫,还有一只黑色的猫,远远地看着,它们虎视眈眈。11 岁的我,也想如猫一样自由自在。
张的黑猫对张的旨意能心领神会,是一只奇猫。
夜是黑色的,又是狂澜的。夜是一件盛大的外衣,罩着了我小小的世界。至于那只猫是如何神奇,还是有点懵懂。
猫伏在屋顶上,与这个世界隔绝。它的痛苦和疾病都不容易发现。只有叫声深刻、尖利,甚至是锐不可当。时常叫的是那只黑猫。孤傲的黑猫,狂放的黑猫。
那时小,刚上初中,家距离学校远,寄居在亲戚家。不知道猫叫是缘于内心的疼痛,还是被外界环境的某种气息唤醒。但猫绝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远离亲人的孤独和青春懵懂的心事,往往是揣摩猫叫的理由。
青石板的街面,木板的墙,灰色的瓦,翘檐,构成了老街的沧桑,也构成了老街的生生不息。一条河,一排吊脚楼,高高矮矮的,错落有次,沿河而建。至于年代有待考究。是这个小镇给我独特的记忆。一片连一片的水田,又让这个小镇有十足的江南水乡的味道。
下晚自习的时候,天很黑,风很紧,吹在我脸上,是冬天。隔壁住的谁,我没有问过。但我还是知道了,是一个姓周的女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很多时候一躺下就听到屋顶有猫在叫。叫得孤绝,还有点忧伤。叫声之后,是窸窸窣窣的响声。忽然间,猫的叫声凶猛,狂躁。继而有厮打声混着在隔壁响动。我大气不敢出,躲进被窝,用被子捂住耳朵。但那声音总是钻进来。喘息的声音,还有摸索的声音,又不时地灌进我的耳朵,撞击着我的耳膜。猫在屋顶上走动。一觉醒来,又听到。这是谁家的猫,不让人安宁。
一个不上晚自习的夜,伏案解相遇问题,已知的,未知的,速度和距离,究竟有什么关系。咬着笔头。猫叫了,一声,两声,三声,喵喵,喵,喵,一声比一声紧。开耳门的声音,有人走动的声音。
“别急。”
我疑惑,“别急”。谁在急,为什么急,急什么?
这声音很低,却发自胸腔,有一种火的味道,并有殃及全身的趋势。急,从心尖上跳出来。整个屋子是慌张的,是急迫的。猫继续在叫。
好奇让我的眼睛靠近墙缝。一只眼睛放大隔壁的场景。男人张抱住女人周。灯亮着。看不见两个人的脸,但我能感觉出他们是激动的。分不清是谁抱紧谁。猫又叫。接下来,灯熄了。猫叫声被淹没了。窸窸窣窣的响声,紧张,窒息。
隔壁是镇长的家。
天突然下雨了,啪啪地打着窗棂。这个晚上的作业只能是一道空白。那些应该填写的数字,或者方程式,我懵懂地认为这就是无解。
我住的这个吊脚楼下,河水涨了,水声蔓延着。整个夜晚我都在想他们为什么抱在一起。身体与身体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秘密。天快亮的时候,猫又在叫。耳门开了。有人走了。又一个疑惑: 好好的大门不走,却走耳门。难道这耳门就是为他开的?
很多次,我注视着耳门,齐腰高的一个洞,在墙上似乎显得有些孤独和无赖。人从耳门进出并不那么方便,可偏偏有人要进出。很多时候,我看到猫就蹲在耳门口,假寐着,一动不动。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明白耳门是做什么用的。
猫和耳门的关联,秘而不宣。
第二天,我一早出门上学,一只猫在屋檐角萎靡不振。身上有伤痕。那是一只流浪的猫,从什么地方来的,无人问津。它自己疗着伤,一次次舔着伤口。眼睛里的孤独看着很凄婉。那么孤零零的。我想一定是昨晚战乱中受的伤。另外的猫去哪儿了?
下午,我放学回来。在门口遇到她,她对我笑了笑。
这个晚上没有自习,她给我讲少年维特的烦恼。她说,我和维特的年纪差不多。她说维特时的语气和语调都有一种魔力。我看着她,问有这本书吗? 她说:“你现在还是不看吧。”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歌德一本自传体小说,也是歌德的成名作。眼前这个女人,还读过这本书,一定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
小镇对读书的人很崇敬。
2
很多时候,女人周是根据猫的叫声来判断是否又能够相聚的。
同样张可以根据猫的叫声判断女人周是否安全。
这天,天气很好。
小镇从安静里起身,隔三岔五就热闹一次。又是一个当场天,满街的人在黄昏散去。散去了人的街道,有些空洞,也有些呆板。斑驳的木板墙和青石板街面,是安静的。只有猫在屋顶上走动。
光从瓦缝漏下来,在我身体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也许是刚刚在夜色里拔节的荷尔蒙。我忍不住贴着墙缝,去探究隔壁。嗯,我知道隔壁有更值得探究的秘密。隔壁住着的女人怎么总是一个人在家。她的男人也不见回家。夜里,她习惯在灯下洗涤自己一天的风尘。脱去身上的疲倦,细腻、圆润、丰满和高挑,就露出来了。视觉和色彩都具有震撼力。女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上帝雕刻出来的美,是来净化人间的。
耳门响了,猫也叫了。这是一只花猫在叫。
我疑惑,是哪里来的花猫? 紧随着黑猫也叫了。我的目光随着声音移动过去,一个身影挤了进来。耳门是一个很诡异的词,带有内心的秘密和不为人知的诱惑。
不久,视角一直很好的耳门,关了。电视天线从屋顶上移动了位置。白天,猫躲到不见了。或许是因为它一身灰暗色的毛,不容易发现。晚上的猫和白天的猫是不同的。目光炯炯,射出来的光是绿色的。很多时候猫在白天酣睡。一定是养精蓄锐,以精力充沛去屋顶上迎接挑战。我不止一次两次猜测,三只猫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头破血流。
猫叫很直观,毫不掩饰对一种事物的渴望。在屋顶上走来走去,叫声孤独,忧伤。也许是它发现了什么秘密。叫声总是不期而遇。有时深更半夜,有那种突发的奇思。我不是猫。每一次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也不能叫,只有屏住呼吸。
很自然,猫一叫,我就贴着墙缝偷窥。猫在屋顶,一定是从瓦缝看到了女人质感细腻的胴体。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身体,心震颤了一下。我明显感觉到呼吸急促。猫从屋顶跳了下去扑在女人的身子上,吓得女人打翻了洗澡盆。那时女人周没有领悟到猫叫的原因。水滴滴答答往河里漏。身上香皂也没来得及洗净。女人追着打猫,猫一个劲儿地叫。这叫声与往日的叫声截然不同。猫跳在房梁上,悠闲信步。女人望着,无可奈何。
后来,每到女人周洗澡时猫总要叫。女人就对猫说,一会儿就好。猫自然离去,要不了多久,女人周就会听到耳门的响声。
女人周越来越喜欢张的这只猫。油光发亮的黑毛,细腻柔滑。不但机灵,还心领神会女人之意。
女人周和猫睡在一起,爱抚着她的身子,暖暖的。女人周洗澡,也会给猫洗。猫叫女人周起床,出门。
很久,猫都没有叫了。猫没叫的屋子是空的。每到夜里,一觉醒来,莫名地忧伤起来。女人吃饭的桌子上多了一个碗,青瓷的碗。和她说起过猫叫的事。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耳门并不是她设计的,猫也不是她养的。
很多时候,女人周坐在吊脚楼上,默默地看着河水,猫陪着她。河里的水透出几分忧伤,不紧不慢地流着。如果河的水面是静止的,一定会看到一张姣好的脸。我不知道夜里的脸是什么样子,有种声音可以印证,是美好的。
有个晚上,我回来得很晚,猫又叫了。我怀疑猫是不会睡觉的。一双碧绿的眼睛注视着女人。我不知道它发现了什么,我怀疑猫的天性已经丧失。难道它不去捕捉老鼠了?这些天,老鼠上蹿下跳的,闹鼠患。老鼠和猫对视着,桌子上也不敢放饭菜。一不小心老鼠就钻进米坛子,和人抢粮食。晚上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个不停。耳门又开了。我忍不住从墙缝窥探: 女人迎了上去,饱满的身子,有手在扑腾。握住了,火焰在升腾。我看清楚了这人不是镇长。究竟是谁,我一时半会想不起,似乎见过,但就是想不起。凶猛的匍匐,撕裂着女人,女人压抑着呻吟。猫在身边叫,一声紧过一声。翻腾的云,有雨聚集而来。一个身影闪过耳门,夜又归复安静。
我看到女人在流泪。此刻的屋子清冷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有些漠然。虽然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流泪,但我感觉到她内心里一定有什么被触及。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夜。
3
镇长是个横行霸道的人,居然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动他的女人?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镇长长什么模样,他似乎是一个神秘人物,一直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出现过。不过传闻很多,各种版本难辨真假。
我一直在想,是镇长的装聋作哑,还是真的被蒙在鼓里。也许我的年纪小,还想不明白这件事。女人走在街上,笑声很自然,一双眼睛透露着某种意味。她直视我,笑的样子很真诚。我躲开她的目光,心跳紧张。还有一种感觉是莫名其妙的。脑子里总是晃动着夜里的事情。
屋顶上的猫又出现了。猫是一只不消停的猫。猫嗅到了镇长的来龙去脉,在屋顶上走动着,看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
闷闷不乐的猫,回到镇上,一溜烟跑不见了。寂静的小镇,回到孤独里,河水也是寂寞的。猫不再叫了,耳门响的时候也不叫。小鱼在河里,猫学会了抓鱼。无辜的鱼,蹦跶着,猫用爪子拨动,逗乐着。鱼无辜地挣扎着,但还是死了。猫独爱这鱼的腥味儿,从味蕾里发出呼呼的响声。这声音是在告诫什么? 我不懂猫的语言,但我从意识里认为猫是善良的。
猫注视着死去了的鱼,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猫也装死。那一天,我内心的河,鱼跃而出。茂密的两岸,猫穿行其间。梅花的脚印,镶嵌了古老的虔诚。我膜拜夜,隐藏在生命里的忧伤,一定有撕裂。灌满猫的叫,正好。屋顶是灰的。屋梁,正对着一张床。生在床上,灭也在床上。那年冬天,我看到一个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去了。紧闭的眼睛,猫也没有能洞悉到生命的尽头是如此的哀伤。干枯的手,抽去了生命。紧闭的双唇,曾经的豪言壮语,再也发不出声了。有人在哭泣。猫也泪眼汪汪。
不叫的猫是安静的。
女人看着床上的女人,一言不发。
死是突如其来的。“那一天,我是不是也这样躺着,再也起不来。”女人想。
这是一个年轻就守寡的女人。她知道这个女人一生的坚韧。她从心底吐出一口气,“这下好了,再也不煎熬日头了。”嘴唇上的苦难,不说也能看出来。
年轻时,她也爱过。男人死后,在唾沫星子里度日如年。后来干脆死了去爱的心。一个人守着日头,起早贪黑。把自己熬成老人。死是她最好的归宿。那时,猫也守着她叫,叫得满城风雨。一天天,容颜褪去色彩。自然女人在小镇是具有传奇的。那些离奇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演绎着小镇的历史。
小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猫和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猫是捉老鼠的。这种猫科的肉食动物,什么时候有了人性,和人生活在了一起。猫比人自由。行走在屋顶,是别有用心,还是想看得远一些,不得而知。也许人类的秘密,在猫眼里就不是秘密。
很多天,我都发现屋顶上只有一只黑猫在东游西荡,有些孤单。其它的猫去哪儿了? 女人想着猫的爱情是不是和人的爱情一样复杂和揪心。
虽然她有男人,但仅仅是一个摆设。男人究竟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是融入灵魂,还仅仅是陪伴生活。人有灵魂吗? 她总是相信,爱着的那个人就是她的灵魂。见不到心就空了,心神不宁。
洗一次燃烧一次。
猫在黑暗处,认识女人的伟大。不虚掩的门,不关闭的是豪迈。创造生命,延续生命。门是一道坎儿。门又是一扇欲望的门。人间的欲望是躲避不了的。美就在欲望中。拯救灵魂是需要美的。
月光下的猫,叫声凄美。
她想明白了为什么猫会叫,在无尽的长夜,叫得是那么凄婉。女人周知道有事情发生,赶忙叫张离开。果不其然,张穿好衣服,一离开,男人就回来了。
他回来,女人周正在天井洗澡。从天井漏下的月光,落在女人的身上,很灵动,似乎是女人捧起月光在洗身子。多么美好的身子,月光落在上面,美更为奇妙。月光包裹着火。我看到了火的声势,谁也不可阻挡。
但男人没有来纠缠女人。
很长一段时间女人和猫一起消失了。
4
我忘不了小镇那只通人性的猫。
回到小镇就想起猫。猫真的有灵魂吗?
屋顶灰暗。光在屋顶上也是灰色的。
很多时候,女人身体是充满了灰暗的。只有遇见自己想遇见的人,她的身体才会焕发出光芒。这光芒是两个灵魂融合的光芒。
小镇在悄悄变样。吊脚楼摇摇欲坠了。沿河的一排,改朝换代一排钢筋水泥楼。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见猫。但猫又如幽灵一样在我的生命里总是出现。
特意在镇上住了一晚。
过去的楼阁没有了。
猫不再抓老鼠,而是宠物。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女人抱着灰色的猫,描了很红的口红,眼睛里有不易察觉的妖气。我外出求学就没再回过小镇。听说镇长离婚了。由此,离婚在这个小镇打破了格局,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
外出打工,成为这个小镇一个新的话题。有人从外地带回来猫。我又一次听到猫叫。这是那个女人抱着的猫吗? 我想这一定会是一只有狐性的猫。但我的潜意识里猫不是这样的。
隔壁是谁?
这是我的条件反射。街上遇见镇长的前妻。和过去一样走在大街上是安静的。这么多年她的身体依然隐隐约约有一种光,是那种不经意洞穿内心的。她看着我,笑了笑。我说我看了歌德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她说,也许小仲马的《茶花女》更好看。当然这本小说我读过,对于小仲马表达的爱情,是高于现实的。我问她看过《简爱》吗? 她摇了摇头。
下午,一个人坐在河边,河里鱼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一只猫,安静地卧在我身边。有人在河对面打情骂俏。如河水一样的声音,清脆,干净。
离开小镇这么多年,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女人周看着我,相视一笑。我问那只猫还在吗?
她说,是从耳门进来的那只猫吗?
我点了一下头。
她说,不在了。
“嗯,一次车祸。”
她又笑了一下。但我察觉到了她的忧伤。我想问,是什么样的一次车祸,但我没说出口。
这究竟是怎样一次车祸,没有人去追问。
似乎这个小镇的故事就在这里,没有再延续下去。
听说,她之后暗淡地生活着,一个人住在吊脚楼。至于什么时候那只猫不见的,她也说不清。
没有猫的日子是空荡荡的。整个的魂不守舍。她望着河水,独自流泪。那些来骚扰她的人,被她骂得狗血淋头。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判断一个女人的活法,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爱去活。是的,这是有爱的活。
夜晚,猫是有灵性的。再一次出现,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这回不是从墙缝,而是从心间。我站在阳台上抽烟,一支烟接着一支烟。那些明明灭灭的记忆,总是从某一处冒出来。身体上的痣,或者胎记,透着女人的性感。我甚至想说出女人某处的美好,但我没有这个胆量。十年了,镶嵌在我的记忆里,有一种生命的搏动。
抬头一望,屋顶上又有一只猫。是一只瞎猫。耳门没有了。
我上到已经建成了平房的屋顶上,张开双臂,大呼。安静的小镇有了动静。一盏灯接着一盏灯地熄灭了。这样的夜晚能听到心跳。我还是听到了猫叫之后那个女人的抽泣。低沉,哀婉,压抑,沉闷,但又包含着火山一样的凶猛。
猫是有九条命的。起死回生的猫,一夜未眠。
女人周开了小镇第一家旅店,生意很好。她打理着每天的时光,猫一直跟着她,只是不再叫了。
后来,女人遇到了一个来小镇旅行的男人,至于是怎么擦出了爱情火花的,没有人去问。夜里,再次听到猫叫的声音,小镇有了意想不到的生动。
小镇不再孤独。
屋顶上的猫,就此有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