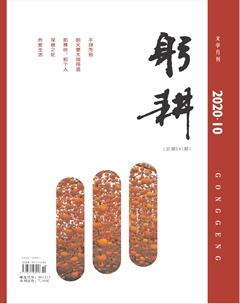袁店河故事(四题)
赵长春
哑科
紧病慢先生。
这句话用儿话音发出来,好听,有韵味;特别是用袁店河的方言,更有意味儿:紧病儿慢先儿生。先生是指中医。好像是说病人状况十分危急了,医生依然不慌不忙。肖纾聃后来才悟出这句话的道道儿。
后来是指他成为袁店河的名医后。他在自己的医案里特意称道了这句话:好中医是急不得的。
肖纾聃就不急。他坐门诊是袁店街头一景。端坐,双脚着地,合闭双眼,目光方向为关元穴,肚脐下三寸,静默,意守半分钟或者一分钟后,手指才触及患者手部的寸关尺部位。无论来诊者多急,在他的这种气场下,也静下心来,平稳了脉搏,回到了自然状态,肖纾聃就能更好地把脉诊病了。这时候,肖纾聃的淡定从容让患者更信了他的医术。
于肖纾聃而言,闭上眼睛后,意守关元,既阻隔外部光、色、音等的干扰,又气守丹田、内护自保。毕竟,把脉凭心,用的是精、气、神,把诊下来,耗费元气。肖纾聃多用望、闻、切,问得少,就已经把准了病因。然后,甘草、二花、大青叶、泻白散、紫雪丹等,三天五副,药不贵,却管用。
肖纾聃主攻儿科。或者说,他显名于儿科。中医儿科,比较难。小儿手不能指,口不能言,身上不舒服就多用哭闹表达,而啼必有因,所以他留下的医案里称儿科为“哑科”。中医儿科,看准病情后,草药为主,去病如抽丝。不若西医儿科,糖衣药片、糖浆药汁或者输液,不苦口又去病快。
对此,肖纾聃却不认可。他的医案里,用蝇头小楷表达了一种担忧:“小儿生机勃勃,五志萌芽,七情渐增,当如春风吹草细雨润苗,父母者只喜去疾快,殊不知根本已被药伤,反积大患矣……”
王福强出生的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不若以往吃奶后安眠,只大哭不止。王福强他奶非常着急,拿起他的一件衣服站在院外的雪地里,一声声地叫“强娃儿回来!强娃儿回来!”王福强他妈在油灯下抱着他,一边拍着一边连声地应着“回来了!回来了!”用老辈们传下来的安抚小儿惊悸的“叫魂”法。可是,不灵。王福强他妈越拍,王福强哭得越凄婉“哇哇!哇哇!”没有办法了,王福强他爹抱起王福强扑进风雪里,敲开了肖纾聃的门。
肖纾聃灯下细看,“这孩儿没有啥毛病啊?”他用温水洗了手,触王福强额头,不烫。再用温水洗了手,解开包裹,七个月大的王福强竟然转啼为笑。肖纾聃眉头一皱,温手轻摸,细皮嫩肉,王福强不哭了,眼睛水汪汪的。谁料肖纾聃的手到了他的腿间,王福强又哇地哭了。同时,肖纾聃觉得指头肚儿被什么刺了一下,再看却是一别针,已经将王福强那里扎破!王福强他妈图省事,用别针系软布围其屁股……
还有李小青,也就刚一岁的样子。从城里的姑家回来后乳食锐减,无精打采。一有人来,李小青无非从母亲胸襟转出头来,稍一观望即又以面贴怀。李小青的姑就带回来保和丸、胃蛋白酶啥的,心疼有加,可是李小青仍不领情。没有办法,爹妈就抱着李小青来找肖纾聃。
肖纾聃刚把在袁店河边挖拾的芦根儿放下,李小青的爹妈就进来了,差点儿跪下,把肖纾聃吓了一跳!肖纾聃急忙洗手,没有温水,就用手对搓后,摸额头按肚腹再看舌苔,“没有啥呀?”一問,说是从姑家返回时,其表哥正冲她开玩具枪,她当时还不想回来,由笑而哭。肖纾聃说,“那不用吃药了,明儿个叫她姑给她买个一样的玩具枪吧。嘿嘿,这小妮儿,念想怪大哩……”果然。李小青一见枪,笑了,好了。为啥?“小儿亦有心思。所欲不得,忧思伤脾。”就使起小性子来了。
肖纾聃写一手好字。过年自己写春联,联嵌药名儿:春至但闻藿香木香,人来不论生地熟地;天冬寒水石上流,地黄梅花雪里开等等。他在墨汁里加了中药,字有香。闭眼,现在还能感觉到那香味儿。
人都会老。肖纾聃也老了。手哆嗦了,他就去放羊。他说,手劲儿不准了,再看病就有些糊弄人了。
肖纾聃想收个徒弟,可是没有人学,都说下不了那样的真功夫。再说了,街头、村尾,小诊所多得是,头痛发热就挂水,省事,快。中药得煎得熬,半碗一碗,黑糊糊的,喝起来还苦。
肖纾聃更老了,放羊也没有精神了,总打瞌睡,走到哪里就睡到那里,枕着一个蓝布包。八十七岁的那年秋天,肖纾聃睡过去了,人们发现他所枕的蓝布包里,是一套厚厚的医案:哑科。可惜得很,那医案被脑油浸润得粘连一起了,目录里有“夜尿”“口疮”“不啼”“伤食”“百日咳”“腹痛”“水痘”等等条目。模糊不可识。
可惜得很!一位医学教授如是说。
四重屏
屏风,可以屏障风也。
屏风入画,不新鲜。屏中画屏,重屏,国画传统技法。画者不多。不好画,也画不好,不敢轻易下笔。
齐云埭画屏风。
那时候,袁店河不少家户置屏风。迎门、堂内、室间、绣房、塾屋,四扇相连,三扇隔档,两扇对开,一扇堵面。再讲究的,六扇、八扇,木框、绢底。不济的,也竹制框、皮纸。摆放好了,请齐云埭画;或者,画好了,拉回来。
谁画的?齐先生!
齐云埭更喜欢的是画屏风。面对熟宣,静思,默对。沉吟,呼气,笔尾敲纸,指甲按纸,定了间架结构,提、放、连、顿、挫,三扇屏,左、中、右。中间的那“扇”上,心思放得多,会再设置“屏风”……画里,大小、高低、胖瘦,总有一两个小姐的形象,脸儿很相仿,眼神不一样。
人们喜欢齐云埭的屏风画。画里有画,画中套景,层次递进中,显得屋身宽阔,人心也敞亮了。闲坐柳圈椅,捧壶,品茗,看画者会琢磨一上午,花、枝、叶、石、鸟、泉、人、松、书,一个个细节,都逼真,透着儒气,雅味。
人们就不由自主赞叹:这个放羊娃子!在心里。
齐云埭是在给周家放羊后,开始学着画屏风的。
周家羊多,牛马多,人多,很大的院子,院子套院子。那天,一只山羊,蹦跳如猴,各院乱窜,跑进了最后一重院子。齐云埭追撵,跟了进来。
小院里,更干净。也有花草,更好看。还有一道好闻的气息。两棵桃树间,扯着一道绳,悬着一幅画:重屏。画前,山羊站着了,仰鼻闻嗅画上的草。齐云埭愣住了,看那画上读书的小姑娘,依着花窗……他和羊都有些入迷时,头顶有声悄悄的咳嗽。抬头,画上的那个姑娘依着花窗,执一本书,线装。
你是干啥的?
放羊的。
喜欢画?
好看。
咋不读书?
……没钱。抵债,放羊。
好好读书吧,我教你。放完羊就来,别给谁说。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天,桃花正开!
齐云埭离开周家后,开始画屏风,画来了一套院子,就在周家院墙外,相邻周家的后院……
齐云埭留有一幅重屏,四重的。一重,三扇,左花鸟,右山水,中间是端坐的自己,老态,唇吸闭开合,若有话说,目光对视看画人。二重,就在一重的中屏,依然有屏风,三扇,中间是读书的自己,抚髯,神形若蹙。三重,在二重的中屏,依然三扇屏风,中间是站立的自己,青春盎然。四重,就在三重的中屏,依然三扇屏风,中间是少年的自己,髽髻,亮额,目光清纯;腿边,依著一只羊。
气韵流畅、典雅恬淡,笔墨工细、人物自然。多年后,齐云埭的重孙女站在这幅画前,低低地评价了一声。她在省城读大学,美术专业。她听爷爷说过,太爷画重屏。找到这幅画很不容易,就在老屋的顶棚上。老屋就要拆了,当时要直接推倒。暑假回乡的她说,稍等一下,我给老屋拍照,留影,给我三天时间。
她发现了这幅重屏。画展开时,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屏风的左扇里,还有一个女性,从小到大,形变神不变,眉眼就是一个人;而她的目光,总是看着齐云埭!
她拿着放大镜看,双方的瞳仁里,都有一个彼此,倒置的,一丝不苟。
画轴下端的轴心上,一行字:此幅悬于云埭书屋西墙正中,左右下各距三尺。小楷。
云埭书屋?
对照着老屋旧图,她找到了书屋位置,好在没有坍塌完毕,西墙还在。她搬来梯子,按照尺寸,将“重屏”悬了上去。重屏有些晃悠,屏中的齐云埭好像在笑,很欣慰。恍惚间,她觉得齐云埭在说着什么,目光看着一个方向……画幅静止了,顺着齐云埭的目光,是斜对面的墙角,一口烂缸,蛛网蓬勃。
烂缸里什么也没有。敲击地面,墙角下空。挪开横竖老砖,一穴,檀木小箱,内有《重屏艺法》两卷,几枝笔,几方老墨!
她把这些带回学校,读画,写就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重屏讲究空间重叠;最高一重是看画者与画的对视、感悟,在画外。
但是现在,不讲究了,屏风少了。也没人画屏风了。
至少,在袁店河。
上岁数的人说,谁敢画?能画过齐先生?
不过,省城有个画室,画屏风,重屏,还教了不少学生。
画室名为“漪姝”。
人们说不好认,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画室的男老板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其实,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名字,不是他的名字。
大工
瓦刀,建筑队的基本工具,可砍,可铲,可抹。
掂瓦刀,是建筑队中大工的标志。
掂瓦刀,得从小工干起。小工,搬砖、运瓦和泥、清料,累活、苦活,都得干。干着干着,师傅觉得你可以,就把瓦刀递过来,叫你砌上几块砖,看你抹泥、勾缝,点头或者摇头……再后来,师傅把瓦刀给你,叫你砌会儿墙角,看你平砖、立砖、勾砖,抹泥、勾缝,磨“抱”墙角的功夫;磨得能“抱墙角”了,就离掂瓦刀不远了。再后来,师傅给你买了瓦刀(自己买不算),腰间一插,就是出师的大工了。
这个过程,少说的话,得三四年的熬炼。
罗迭阳插瓦刀那年,二十四,这个年龄能当大工的,很少。罗迭阳高兴自己可以改轻口味了。小工的口味都重,咸饭,添力。同一锅饭菜,当小工的,就多加酱、辣椒。
可是,那年形势不好,建筑队解散了,各找各的出路。罗迭阳觉得特遗憾,吃喝都成了大事儿,哪还顾得上口味。各找各路,各回各家吧。
不想回老家,罗迭阳就腰间插了瓦刀,出了城,转。转,转到了袁店河,转到了小汪庄。村口阳光下,罗迭阳倚着一家院墙想歇口气,却坐在了地上。两天没有正经吃东西了,额头沁汗,已经脱相。听见动静,汪老婆出来,一看脸色一摸头,吆喝媳妇儿赶紧端出一碗米汤,叫罗迭阳喝,慢慢喝。
一碗米汤,有些稀,却缓过了罗迭阳的精神。罗迭阳眨眨眼睛,汪老婆又要给他拿馍时,媳妇儿的脸色有些为难。家在村口,往来要饭的多,婆婆见不得人可怜,就总是多熬些米汤,稀稠不拘,好歹活人……可是,给人送馍,就会夺了家人口粮的。
慢慢站起来,罗迭阳抽了瓦刀在手,把两个女人吓了一跳。罗迭阳瞄瞄汪家的院墙豁口,“俺不是要饭的。”
罗迭阳径直进了院子,取了脸盆,就着汪家门口塘坑的水,和了一摊泥巴在院墙豁口处,蹲下去清出墙根脚,拾掇出碎砖石块,唰唰唰,铲、砍、抹,将被大雨冲毁的一段院墙垒好、砌稳,线直,泥净!
干完活,脸盆洗净,瓦刀抹净,罗迭阳弯身致谢,“俺不是要饭的。俺是大工!”
看着他这般模样,汪老婆揉眼睛了。那媳妇泪水汪汪,端出一个馍来,配着一碟儿咸菜丝,“吃吧。吃饱了再走。”
罗迭阳摆手。
汪老婆也摆手,“别慌。你把俺家鸡窝垒了吧。”
就垒了鸡窝,在媳妇儿的窗下。
罗迭阳干活时,村上还有其他人家来看,媳妇邀来的。看罢,定住去另外一家砌墙,盘灶台,盖猪圈……罗迭阳在小汪庄竟然呆了五六天,走时,背了半袋子馍,黑馍、花卷、玉米面馍,还有两个白馍,那媳妇悄悄给的。
罗迭阳说,吃饭当工钱,不能要馍了。
汪老婆说,带回家吧,俺袁店河地好雨顺,都知道的。
罗迭阳接过,想鞠躬,瓦刀硌住腰,就拱拱手,走了……
罗迭阳再回来,是十年后的腊月二十三,小年。他径直跨进汪家院子,放下肩上装满年货的大麻袋,冲着汪老婆跪地就磕头。正在收鸡蛋的汪老婆眼睛有些昏花了,发愣。
嘣嘣嘣!磕完头的罗迭阳说,“我是那个瓦工,小罗。”
汪家媳妇从屋里出来,抱着孩子,笑了,“大兄弟,壮实了!没有大胡子的话,更好认!”
罗迭阳说,自己在城里有了建筑公司,有了楼房,想接汪老婆去城里住,过个春节。
汪老婆不去,“心意我领了……”
罗迭阳说不过,就说过了春节,来给盖座房,上下两层的,水泥、钢筋、亮窗。
汪老婆说,心意我领了……要不这样吧,带带我们村的年轻人,跟你学,当大工,掂瓦刀……手艺儿,能当饭!
罗迭阳就拱拱手,笑了……
七八年后,袁店河有了第一支建筑队,队长姓汪。
又几年后,袁店河有了第二支建筑队,队长姓王。
再几年后,袁店河有了第三支建筑队,队长姓李。
接着,袁店河有了第四支建筑队,队长姓袁……
这几支建筑队的大工,都說自己的老师姓罗,罗师傅。
每年腊月二十三,罗家人都来小汪庄,看看汪老婆。其中一个不能少的仪式,要观摩那个鸡窝。小鸡窝,工好,柱是柱,角是角,勾灰,抹缝,毫不含糊。后来,成了罗家的习惯。
还有一个习惯:罗家下米时,总要从量好的米碗里,再拨回米缸里一些,至少是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弹拨回去。无论谁做饭,都这样。
包括新进门的媳妇,也要学会这个,遵守这个。
罗家其中的一个媳妇说,“怪了,谁还缺那一把米?”悄声说的。
说着,瞄瞄墙上的相框。里面,那个人,好像正看着她。一盘络腮胡子,很浓。
赶牛
赵老二闲不住。
上地回来,他的手里会多一把草,剁碎,拌麸子,搅匀,喂院子里的鸡鸭。嘣嘣嘣,鸡们鸭们抢食,吃得欢实,屁股翘翘的。赵老二看着高兴。
赶会回来,他的篮子里会多几块砖瓦。碎砖,烂瓦,人家撂在一边不用的,他捡回来,积在墙角。过些时日,盖了个鸡窝,结结实实的。赵老二看着高兴。
人们说,这是穷命。
赵老二说,这是我的活法。说完一笑,这叫日有“进项”。
进项,袁店河一个很雅致的说法,就是收入。不同于人家的钱款,赵老二的就是这些,贴补家用,居家过日子。
细想,这,也是钱。
还有一个进项,别人基本不干。这个活路也在行,叫“拉捎”,就是载重量大的架子车上坡吃力时,走上前去,拉起车把一端的绳,俗称“捎绳”,勒在肩头,帮一把。车到坡顶,人家给报酬,或钱或物。有的只是一笑,说声谢谢而已。赵老二也就一笑,“没事儿,搭个帮手,不算啥。”
这个时候,有人笑他。他说,“力气算龟孙,用完了再拼。叫人家说咱袁店河好,就好。”
还有个进项,赶牛。袁店河边有个牛市,经营牲口买卖。牛经记看牛估价又准又权威,交钱交货后,就找人把牛赶往屠坊,或者送往买牛人约定的地方。按头数,给个赶脚费。块儿八角,不多。赵老二不嫌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个活儿,他多是趁着晌午头去的。他不歇晌。午饭后,赵老二觉得正有劲儿,走走路,能消化粮饭,还能多个进项。大中午睡觉,划不来。还有,可以走过女人的坟前,拔拔草,说几句话。
那个中午,赵老二在赶牛路上,被人盯住了。他走的是近路,穿地,庄稼稞子高,密。正沿着田埂边走边唱戏的他,觉着不对劲儿,就走在牛前面,抽出腰间镰刀,边唱边吆喝牛,“好好走,哪有狼?敢出来我砍死它!”
说着,赵老二唱起了“十大劝”,第一劝做人良善,用的是河南坠子腔。就这样,唱着走着,快到河边,那人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往回走,不再跟了。赵老二没有回头,他瞄着河面上那人的影子,认出是原小五,就提高了嗓门,“叫声小孩你听心间,听我劝别再这样干,走正道靠力气,一样能吃饭!”
赵老二干了一辈子活,赶了一辈子牛。后来赶不动了,他就赶着一头老牛,跟在牛后面,晃。牛也老了,他也老了,都走不动了,就都晃。河边,村口,牛在,人就在。形影不离。
这头老牛,原本是要送往镇上屠坊的。
那个中午,从牛经记手里接过缰绳,赵老二看看老牛,“老牛老牛你别怪,你本就人间一道菜。”念罢,第一次,他心里掠过层层悲哀,有着浓重的凉。不再说话,不再哼曲,赵老二前面走,老牛后面跟。牛有灵性,知道要去屠坊,也不惊;不若猪羊,惊叫狂跳。不过,走着走着,赵老二拉不动缰绳了,回首,老牛向后挣住身子,一脸泪水。稍一迟疑,牛扑通跪下了,冲着赵老二点头,一下,又一下,清泪如流,汪汪地淌。
赵老二也就哭了。他憋一路了,哭得放声,有些孩子气。他想起早晨出门,儿媳妇给他递饭碗时的白眼,伴着一声埋怨,“就会吃,啥也不干。”声音很小,保证就他能听见……自己干一辈子了,老了,咋就不中用了呢?赵老二想着,泪水也就出来了。
火热的阳光下,赵老二慢慢地蹲下去,手哆嗦地按着地,坐好,坐在地上,扶着牛头,抱紧,擦拭着老牛的泪,就在那滚烫得有些粘稠的风中,想了好大一会儿,包括早去的女人……后来,他把牛赶回来了。牛在前面走,带着他。进院子时,牛经记正在问询他儿子。赵老二走到牛经记面前,把赶牛的钱递上去,回屋,取出一个手绢,拿出一卷钱,数好,给了人家,就卷起一床铺盖,住进了牲口屋。
现在去袁店河,最好先来一碗炝锅烩面,配着千层火烧。吃罢喝罢,再到河边走一走,就能遇到赵老二和他的那头老牛。奇怪的是,赵老二更精神了,老牛也特别精神,毛色光亮。他们很精神地在袁店河畔,成为一道风景。
还有,遇到赵老二的话,如果想和他谈,就说关于牛的故事。他能讲很多很多,并且都特别有意思。
赵老二多半会从他小时候讲起。他喜欢放牛。他觉得牛最温顺听话,并且不挑不拣什么样的草都慢慢地吃。他会讲起牛的功劳,犁地、耙地、播种,从不闲住,总是浑身的汗水,吃的总是那些干草,还总是挨着鞭子。
讲着讲着,他就把目光放远了,望着远处的罗汉山,“我们两个一起去放牛。她一头长头发,扎成大辫子,垂到胯骨……后来她嫁了,骑着牛走的,我们一起放大的牛。我们一起骑过,她抱紧我的腰……”
这时候,赵老二粗糙的脸庞上,泛起红。细瞅,他的眼角潮润润的。
——让他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