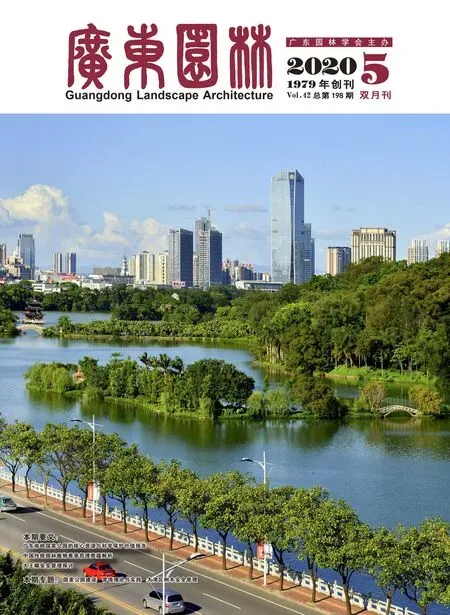星球城市化:风景园林的新理论基础
蔡淦东
1 星球城市化——风景园林发展的新背景
长期以来,城市研究对人居环境的定义建立在城市与非城市的二元论之上,从而划分出人口、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密集的城市建成区域,而郊区、乡村、旷野等地区都被归纳为非城市区域。然而,当研究城市的视野提升到大都 市 群(megapolis)、由 多 城 市组成的巨型都市区域(mega-urban regions),甚至是跨越国界和洲界的尺度时,城市与非城市的二元论已无法解释正在发生中的各种城市现象。星球城市化正是建立在对此二元论的批判和分析上而提出的一套立足全球尺度,对当下城市问题进行探索研究的理论。对该理论的研究与教学起到核心作用的城市理论学家布伦纳(Neil Brenner)与 施 密 德(Christian Schmid)认为,在星球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边界变得模糊和难以辨认,非城市地区却因全球化经济和物流运输的带动,承担起了部分城市功能,两者更像是一个连续体(urban-rural continuum)。因此,遵循以往的观点来区分城市与非城市区域已没有意义,两者都是全球城市肌理的一部分[1]。
在城市理论研究中出现对非城市区域的兴趣与关注,一方面大大拓展了城市理论的涉猎及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城市之外广袤的土地—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及郊野景观等区域带来了新的理论观点,对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星球城市化为研究方向的多位学者均在其研究中展示出对景观的理解。腹地(Hinterland)一词过去多指城市与城市之间欠发展的大片内陆景观地带,而布伦纳认为,这一类型的景观地带已被可操作化(operationalised),是星球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施密德同样认同城市研究的去中心化,并强调星球城市化的复杂性本身就包含着地区间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地区的城市建设如何被实践在大地上(on the ground)至关重要[3]。
现代风景园林的三次重大思想发展①瓦尔德海姆于2016年“新景观宣言”(The New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claration)峰会演讲中提到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的3个重要发展节点,分别是19世纪末学科的创立,20世纪60年代环境导向规划,以及21世纪以来的风景园林的复兴。瓦尔德海姆会议上演讲详见:https://www.lafoundation.org/resources/2016/07/declaration-charles-waldheim都与城市理论及实践研究息息相关。19世纪下半叶,西方语境下的风景园林学科诞生于针对工业化城市的规划思想与实践,城市规划专业亦在19世纪末建立。20世纪60年代,以“景观宣言”(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claration)以及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生态规划思想为代表的第二次学科重大发展,回应了当时针对城市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讨论。第三次重大发展则始于20世纪末并延续至今,体现为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兴,包括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等理论的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景观实践的多样性。当下风景园林的发展与正在经历中的星球城市化密不可分,后者一方面直接为风景园林学科提供了新的讨论背景与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间接为风景园林带来更多跨学科协作的机会。近年来,建筑学、生态学、土木工程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开始以星球尺度重新审视和分析自身领域的现状与发展。同样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风景园林学科,其研究、教育和实践虽早已受到星球城市化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加以系统的介绍、分析与讨论。本文在分析星球城市化缘起和概念的同时,关注该理论通过跨学科形式对风景园林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不同专业领域基于星球城市化的研究成果进行解读,论证当代风景园林的研究实践与星球城市化的紧密相关性,并认为风景园林学科将凭借其综合性与包容性,在星球视野下的人居环境营造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2 星球尺度下风景园林的跨学科发展
星球城市化的理论内核与风景园林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对两者间关系的论述却不多见。事实上,星球城市化把城市研究的关注点从城市建成区域转移到城市腹地的主张,正体现了城市理论学家近年来对全球自然景观区域的重视。以星球城市化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思想,尝试从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等角度诠释星球城市化在多个领域的影响。而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新思潮,也为风景园林在新时代之下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1 星球城市化
星球城市化尝试以星球视野观察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套建立在对全球化经济、信息、技术的理解之上的城市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下的城市研究已无法只把注意力放在“前方”—全球的大都市区域,而应同时深入地研究位于城市“后方”广袤的景观[4]。布伦纳以城市化的“新陈代谢机制”(metabolic urbanization),说明城市区域的运行需要多方的输入来维持,包括劳动力、材料、能源、水和食物等,同时又输出大量的副产物,如废弃物、污染物和碳排放。这些城市的输入与输出流,来自也最终回归到城市以外的自然区域,即作为城市腹地的全球景观[5]。城市理论学家正是通过批判19世纪以来城市研究对非城市景观的忽略或简化描述,力图将环境纳入城市讨论语境当中,构建一套弱化边界而强调互相关联性的星球城市化理论体系[6]。
布伦纳和施密德以大型基础设施、大城市后方腹地、能源开采地、工业化农业用地以及自然荒野5种空间类型,描述星球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现实(urban reality)所包含的非城市区域[7],反映了城市研究对自然景观空间的转向,论证星球城市化理论与风景园林研究、实践结合已成为当下一种跨学科的新思潮(图1)。除了理论著作,布伦纳创立的城市理论研究室(urban theory lab)聚集了一批以星球城市化为研究课题的学者,通过课程、展览、出版物等多种方式丰富了该理论的发展方向。由布伦纳教授主持,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风景园林专业协作完成的研究“星球城市化下的操作性景观”(operational landscape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①该研讨课于2013、2014及2016年春季学期开设,课程名曾为“Extreme Territories of Urbanization”,后改为“Operational Landscape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课程的研究对象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自然区域,包括亚马逊热带雨林、北极圈、外太空、戈壁滩、喜马拉雅山脉、太平洋、撒哈拉沙漠、以及西伯利亚地带。,在2013—2016年对全球范围内多个重要的自然景观区域进行了持续的分析研究,论证了这类偏远区域的发展或退化与全球城市化的密切关系。研究通过一系列开放性成果支持了上文提到的观点,即星球化语境下的城市并不局限于建成区域,原本被认为位于城市后方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风景园林学科的重要研究范畴,早已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城市/自然二元论的影响下,风景园林往往被狭义理解为仅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学科。即使于城市中,风景园林的研究对象也多被局限于公共景观,如公园、街道绿化、社区绿地等。相比之下,城市研究则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域内的核心地带,鲜有针对城市外自然区域的关注。星球城市化学说的出现及发展,为城市自然二元论的消融提供了理论力量,也大大拓宽了风景园林学科的关注尺度与范围。诸多建立在星球城市化理论之上,同时体现了风景园林学科思考方式的新理论与观点,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并接受。
2.2 星球建筑学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规划学院院长Hashim Sarkis指出,建筑学在面对日益明显的全球性问题对建筑实践带来的影响时,习惯于利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凭借技术手段应对,缺乏对全球尺度下空间变化及社会进程的宏观理解[8]。Sarkis通过《The World as an Architectural Project》一书的写作,收集摆脱了上述局限的“星球建筑项目”,清晰地梳理出项目的时间脉络,展示了19世纪以来以建筑学为出发点,人类对星球化议题的思考和想象。
书中提出星球建筑学的特点如下:1)基于地理学的想象力(geographical imagination)。过去建筑学实践多以独立的体量与形式展示在大地之上,而非与大地融合。为融入星球化语境,建筑学开始了对地理学的关注,提出地形建筑、毯式建筑等概念,把建筑想象成跟随地表形态起伏变化的“面”,而非“点”。2)现代主义的新解读。以往理解的现代主义“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是以统一的形式语言及建造工艺解决全球问题,这样的总体设计观点显然不符合星球化时代对全球多样性的理解。Sarkis提出对现代主义的星球化新解读,即以世界系统(World System)思维设计一套能在全球各地形成连接的网络。3)思考价值先于实施价值。与传统建筑学以可实施性为优先考虑不同,星球建筑学由于尺度与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真实委托项目,其思考的价值远高于实施价值。如其他艺术学科一样,星球建筑学可依托于纪录、分析与虚构等手法构建一种社会情景,并借此进行以全球为对象的建筑设计构想[8]。
以设计全球为线索,Sarkis构筑了一部鲜为人知的建筑学历史。在星球化背景下,这部历史将被更多人发现,其中的项目也将更多被当代建筑师研习。星球建筑学并非建筑学科的创新之举,而是长期被忽视的建筑全球视野在当代的复兴与再发展。
2.3 星球生态学
随着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到来,人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地球生态环境进行着影响与改造。当以往用于定义生态系统种类的概念无法准确概括人类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时,一种全新的概念—新型生态系统(Novel Ecosystem)便出现在生态学领域,并逐渐以跨学科衔接的方式进入到风景园林学科的视野中。由于新型生态系统专指在人类行为直接或间接干预、管理和操作下出现的一种由新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类型,因此国内亦有把该词翻译为“人类世生态系统”。杰克•埃亨则提出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Novel Urban Ecosystems),把这一生态学概念与城市规划及城市环境设计相关专业的思考、实践联系在一起[9]。事实上,除了在时间维度上对应目前人类所处的21世纪外,新型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对应着全球尺度,其正是星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复合了生态学、规划与设计学的全新概念。
城市生态学家与植物园科学家彼得•德尔•特雷迪奇对新型生态系统中的植物选择曾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提议使用“全球性都市植物”(Cosmopolitan Urban Vegetation)一词来描述、分析和评价星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态多样性[10]。其中的多个概念立足于对全球尺度与城市化现状的批判性思考,为当前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带来了全新角度,包括:1)考虑城市极端环境对植物的影响。在星球城市化背景之下,现处的都市环境不可避免地布满着由混凝土等非自然物质构成的市政道路、停车空间、高架桥、物流集散地等,这些极端城市环境对大量植物的生长不利,却为另一些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些适应城市生活的植物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和使用。2)本土与外来物种共荣。引入外来物种而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加上近年来对使用乡土植物的强调,使得城市建设中的植物选择过于偏向本土物种,而把外来物种定义为有害植物。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外来物种因对土壤、水分等条件适应性强,而具备强大的城市环境生存能力,在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创造微气候等方面的表现优于本土植物。因此在设计选种上不应片面的排除外来物种,而应综合考虑本土与外来植物的共荣。3)消除对“野草”的偏见。“野草”(weeds)一词不具备生物学上的具体含义,而是人类根据自身审美,认为应该排除的一类自发生长的 植物(spontaneous vegetation)。这样的概念是文化与主观的产物,因此在一方语境下的“芳草”,在另一文化之中成为“野草”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对个别物种的主观偏见应尽量在全球性的城市和风景园林实践中避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意识到,城市建成环境已是诸多动植物必须适应并建立全新栖息模式之地,针对城市而做的生态研究如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成为了新的关注点。而从城市生态学到星球生态学,则体现了新时代之下城市定义被拓宽后,研究对象从单一的城市转向更广阔的城市领域, 风景园林师与城市生态学家尝试站在全球尺度重新理解城市中的生态环境,并提出诸如本文提及的全球性都市植物等具有全球视野的生态学应对策略。
2.4 星球化基础设施
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谈论的城市基础设施一般指由能源、给排水、道路交通、通信、环境卫生与防灾六大系统组成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它们在城市空间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却并非空间的“主角”,又因其多为大型工程建设而缺乏设计特色,常被认为是城市中的“灰色”基础设施。近年随着环境问题的备受重视以及风景园林在城市建设中作用的逐渐凸显,诸如景观基础设施(landscape infrastructure)、生态基础 设 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等“绿色”基础设施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原本由市政工程师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有了更多风景园林师和城市设计师的加入。
星球基础设施则是在星球化背景下对基础设施的新思考和探索,并赋予了基础设施更多的理论价值。皮埃尔•比朗格尔(Pierre Belanger)把“食物流域”(Foodshed)称为一种全球化的基础设施[11],认为在全球化经济的今日,由食物的供应、运输和消费构成的基础设施网络早已突破了城市与地区的限制,成为了一种星球尺度的结构,支撑着全球的食物供给系统(图2)。比朗格尔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关注还涉及能源设施(全球能源与资源开采)、军事设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或废弃军事设施)、水利设施(五大湖区流域基础建设)等,长期以研究与教育实践的方式推动着基础设施理论的发展与演化。他系统性地提出星球化基础设施有利于生态与经济、社会与政治、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历史等多组对立关系的消解,而由风景园林学科引领实践的景观基础设施因强调学科融合与协作,将在星球基础设施时代当中扮演重要角色[12]。
如果说布伦纳与施密德等学者把星球城市化从一种现象描述提升到一种理论研究来分析,比郎格尔则是运用了相似的逻辑,把长期以来缺乏理论支撑的基础设施领域理论化、概念化。同时,作为拥有风景园林学科背景,并长期从事设计与理论教学的学者,比朗格尔把星球尺度下的诸多新视角引入到研究教学当中,极大拓宽了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涵。
3 星球城市化对风景园林发展的启示
风景园林的发展向来与城市、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以全局思维及地球视野观察、研究并塑造地表,是风景园林一直以来与其他空间设计学科最大的区别。孙筱祥教授主张把“Landscape Planning”理解为地球表面空间规划,进而提出“地球表层规划”(Earthscape Planning)的概念,并把之列为风景园林学科的中心工作[13]。该理念可被视为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的对象从传统的庭园、城市公园,向全球地表空间拓展的信号,从尺度上与本文讨论的星球城市化相对应。但就讨论内容而言,星球城市化对全球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理解,对城市与非城市区域之间关联性与流动性的洞见,以及从设计、工程与环境学科以外,寻求社会学、经济学及地缘政治学等学科观点补充到城市讨论中的研究方法,都是目前风景园林学科基于全球问题的讨论没有涉及到的。笔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以孙筱祥教授的地球表层规划理念为代表的风景园林理论发展已接轨星球化时代,但本文讨论的星球城市化理念及其在其他学科引起的新思想仍能够为学科发展带来新机,成为风景园林新理论基础的重要内容。
星球城市化如今在理论研究、城市规划、生态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均有深入影响,对风景园林在当代的实践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种立足于全球尺度的跨学科协作并非单向地从其他学科引入理念和知识到风景园林专业之中,而是一个双向和互相促进的有益过程。例如,布伦纳在描述全球城市腹地时认为,这种覆盖地球70%以上地表的自然景观如“黑盒子”一般为城市学者所不熟知,并提倡需要提炼一套系统性的语言用于精准描述这一类非城市空间[14]。事实上,风景园林学科对此类非城市景观在空间特征、生态效益、社会功能、开发潜力等多个方面均有着丰富的认知理解与实践经验,能为星球城市理论带来重要的内容补充和拓展。上文提到的星球生态学与星球基础设施也存在着类似的双向促进的潜力,即星球化理论拓宽风景园林的研究与实践范围,同时也通过吸纳风景园林学科的知识完善自身的理论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星球城市化作为一种着眼全球尺度的理论,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认为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以西方世界为中心、以一概全的霸权式认识论,忽略了地方性、本土特色与日常真实体验[15]。星球城市化是否存在以上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广泛的讨论,但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新思潮,风景园林学科在学习星球城市化理论的过程中的确需要注意本土化与实用性,避免研究的空洞与过于抽象化。布伦纳与施密德等人的星球城市化理论建立在对北美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与分析之上,其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特雷迪奇的全球性都市植物作为一种认清全球化城市环境现状而提出的倡议,虽对城市生境管理具有指导意义,但具体操作仍需结合风景园林师的综合空间设计能力(基于文化、美学、行为心理等),方能为城市提供植物选择的最优解。
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举办的一场以乡村区域发展为主题的讨论会上,布伦纳从星球城市化角度出发,提出乡村作为城市的大后方,承担着生产、装配与提供资源等功能,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会的风景园林系系主任安妮塔•贝里兹贝缇雅(Anita Berrizbeitia)则从风景园林学科角度补充强调:乡村景观除了在资本经济层面与城市息息相关之外,其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保证食物安全,提供旅游目的地,保护历史遗产等功能也是当代城市的重要部分①该讨论会(The Countryside I: Ruralism)举办于2015年9月,重点讨论了资本经济之下乡村主义与城市的关系,访问链接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uRyZfzqIhY&t=3376s。。
由此可见,立足于全球视野的星球城市化理论通过多学科的形式,对风景园林的研究与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为学科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与操作手法,同时也促进了风景园林与多个学科之间的良性交流与补充。在星球化时代下,城市抑或非城市区域都需要从理论到实践的多学科知识的支撑,风景园林将有机会凭借其研究对象范围广、关注尺度跨度大、运用知识综合性强等特点,以星球城市化理论补充关键的学科知识与思考广度,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以地球表层规划及管理为工作核心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