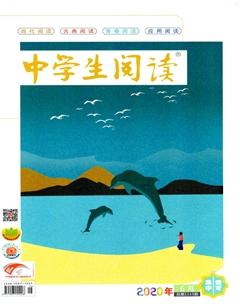“诗谶”
刘志坤
诗人若在诗句里埋下日后坎坷的兆相,或透出生死的线索,就会招来批评:他很不幸地写了一句“诗谶”。这种抽取诗作里的话头,反证诗人“一语成谶”的例子,在古书里简直多得可怕。
比如,“初唐四杰”里的卢照邻,晚年不堪病苦,投水自尽。有人就说,卢诗《曲池荷》云:“浮香繞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一生命运,“已谶于此”。
孟郊中第,大慰平生,有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料以后却仕途坎坷。有人就说,孟诗气象窘迫,“宜其一生局蹐”,况且,长安花“一日岂能看尽”,“此亦谶其不至远大之兆”。
宋代范仲淹深孚人望,世以宰相期许,最后却只做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距宰相终差一级。有人说,范诗《八月十四夜月》云:“天意将圆夜,人心待满时。已知千里共,犹讶一分亏。”其仕途不够圆满,宜矣。——“诗岂独言志,往往谶终身之事。”
当然,你若觉得“诗谶”只限于个人的吉凶,我们可以继续举证:唐代从宣宗皇帝起,至懿宗、僖宗,天下纷乱四起,有人摘宣宗诗“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据此得出结论——“作波涛之语,岂非谶耶?”
你若觉得“诗谶”只限于个别的词和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举证:宋真宗时,蜀中王均叛乱,名士王岩被胁迫接受伪职。有人就说,王岩的诗,往往开篇雄壮,到了终篇,就“气衰兴缓“。王岩的“晚节不完”“,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好在,并非所有的人都迷信“诗谶”。
代悲白头翁
[唐]刘希夷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①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②,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白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注]①“洛阳城东桃李花”四句:东汉宋子侯《董娇饶》诗云“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从诗意上看,《代悲白头翁》前四句借鉴了《董娇饶》的写法,是毫无疑问的。不同之处在于,《董娇饶》是代女子立言,表现了封建社会女子的悲惨命运,《代悲白头翁》则是写花落香残和人事的盛衰,更有一种沧桑感。②松柏摧为薪:《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中有“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句。
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和“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不同,刘希夷存世的诗歌不算少,但最负盛名的只有这一首《代悲白头翁》。后人也喜欢拿他这首诗和《春江花月夜》比较,大概是因为和《春江花月夜》一样,里面有极为深长的叹息和“人生的思索”(葛兆光《唐诗选注》)。盛唐孙翌编《正声集》,刘希夷的诗被称为“集中之最”。可见,虽然刘希夷的诗曾经因为“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但到了盛唐,就被一些诗评家认可了。
按《大唐新语》记载,诗人写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就后悔了,担心和石崇的“白首同所归”一样,成为“诗谶”。待又写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更是惊心,觉得仍近乎“谶语”。不过,最后他终究觉得“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个人的死生怎能是诗决定的呢?“即两存之”,不做删改,这几句遂得以保留。
《大唐新语》的这个说法其实不够严谨,“白首同所归”不是石崇的诗,而是潘岳为石崇金谷宴集而作,最后两句是“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意思是说,我们意气相投,所以把这首诗赠送给你,希望我们能一起白首老去。后来潘岳、石崇被石秀构陷,夷没三族,《晋书·潘岳传》就感叹潘岳《金谷诗》“乃成其谶”。
中国人忌讳“一语成谶”,所以喜欢说吉利话,讨好彩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自不会相信这种“由后追前”的神秘主义的附会。据说,北宋的郭功父晚年作诗不辍,有一天他说:哎呀,我恐怕不能久居人世了。别人好奇地问原因。他说:我最近写了两句诗,叫“欲寻铁索排桥处,只有杨花惨客愁”,这诗“岂特非余平日所能到,虽前人亦未尝有也”,这可有点不吉利!不到一个月,果然去世。李之仪听说这故事后,扑哧笑了,说:如果诗写得好是不吉利的事,真不知杜少陵是怎么活这么久的。
每一个迷信“谶语”的人,都该读读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