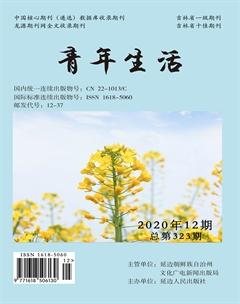天韵遗音 游丝一线
吴欣晨
摘要:本文基于对新天韵社实地考察,从老天韵社物品的回归、曲唱传统的恢复、乐器演奏的消逝三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并认为老天韵社在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位先生的大力推广之下,其曲唱传统因孙玄龄教授的继承而并未丢失。
关键词:天韵社;文人清唱;昆曲曲唱
历史记载中的天韵社是一个著名的文人清唱曲社。它(下文称“老天韵社”)创立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起初没有固定的名称而称为“曲局”。曲局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最为繁盛,社员数量达到数百人,分为南北二局进行会唱。辛亥革命之后,曲局在1920年迁入无锡公花园(今无锡梁溪区箭河街3129号 ),定名为“天韵社”。
天韵社历史传统醇厚,曾因战乱而几度中断。清咸丰十年(1860年),无锡被太平军攻占,城内战火纷飞,大量民宅被毁,曲局也因此一度停歇[6],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又被纳入清政府统治,曲局(当时还未定名)也因此中斷,由于战乱持续的时间较短,并没有给当时的曲局造成很大的影响。天韵社的第二次中断在日军侵华期间,“至日军侵华期间,旧社友流离失所,相继死亡。天韵社于此中断”[2],这次中断直到1948年才复社。“在抗战期中,曾一度停顿,胜利后因社员星散,未能恢复,至最近筹备就绪,于昨日在公园旧址,举行复社”[7]。随后的几十年内,因为种种原因,天韵社逐渐沉寂。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天韵社仅剩唐慕尧与沈达中两位社员,随着他们的逝去,老天韵社的文人曲唱在无锡地区消失。
幸运的是,天韵社在当时出现了两位杰出的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位先生。他们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昆曲课上,将天韵社的清曲(即文人曲唱)传授给了现今的孙玄龄教授。孙玄龄教授在30年后,又将天韵社清曲带回了无锡。
在曹安和先生2004年去世之后,以文人曲唱为特点的老天韵社告别了这个时代。在2013年12月15日,短短的9年之后,无锡又再一次成立了天韵社(以下称“新天韵社”)。在成立之初,新天韵社与老天韵社并无联系,可以看做是两个独立的曲社。但在2015年孙玄龄教授将天韵清曲带回无锡之后,新老两个曲社逐渐产生了传承的联系。
一、《天韵社曲谱》的回归
在新天韵社复社之后,一批老天韵社的物品回归到无锡,这其中包括《天韵社曲谱》、与老天韵社相关的录音、《天韵社纪事诗六绝》影印件、三支杨荫浏制作并用过的曲笛、老天韵社社员的通信稿件等。
《天韵社曲谱》是老天韵社历代传抄的手抄本,1927年吴畹卿[8]离世之际将自己的手抄本与紫檀三弦赠予杨荫浏。在此之前,杨荫浏曾在1918年对对这份手抄本进行分卷缮刻,定名为《天韵社曲谱》,并油印100份分赠曲友。2015年2月,孙玄龄教授将曹安和先生生前所用的油印本《天韵社曲谱》三册(6卷)赠送给现无锡天韵社。在他的细心保存之下,曲谱只有封面破损,内页保存完好并未受到影响。在新天韵社的努力之下,《天韵社曲谱》的影印本在2018年得以出版发行,让后人有幸再一次看到吴畹卿所传之《天韵社曲谱》。
重新影印出版的《天韵社曲谱》分为三册六卷,收录一百二十出,并加上了叶长海与田青两位教授的序言、杨荫浏的《<天韵社曲谱>述评》、新天韵社社长陈倩的《<天韵社曲谱>后记》。《天韵社曲谱》收录了昆曲经典折子戏之外,还收录了《长生殿·疑谶》《千钟禄·劈车》《洛阳桥·下海》等罕见选段。俞伯平曾高度评价该曲谱,认为它“惟其独立成书,与他谱不相为谋”[9]。
这版《天韵社曲谱》上留有曹安和先生学昆曲时的笔记。老天韵社在学习昆曲时“以曲韵的研究为必要条件,初学十余折,必须经过查曲韵,逐字注明分韵分调之符号以后,交请老师改正之阶段”[10]。在知道四声之后,还应知晓如何收韵,吴畹卿在《读曲例言》中把所有字的收韵唱法归为六类并有特殊记号指代,分别是穿鼻(自)、展辅(从、已)、敛唇(吴)、抵腭(△)、直喉(戈、□)、闭口(闭)[1]。现在所见《天韵社曲谱》上的笔记,正是印证了这些说法。
二、天韵社曲唱的传承与复兴
天韵社的曲唱传统其实一直在传承,从未中断。在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位先生的教学生涯中,他们坚持以天韵社文人曲唱的方式开设昆曲传承课,现今不少著名的学者都曾上过两位先生的课。两位先生开设这门课最初的目的是宣传昆曲这一传统文化。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学者乔建中、伍国栋、孙玄龄等都上过曹先生的昆曲课。
在乔建中的《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世纪的音乐生涯》[2]一文中,记述到了曹安和先生用天韵社的曲唱传统来教习昆曲。文中记述到,曹安和当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班开了一门“昆曲课”,该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是指用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学习昆曲中字的音韵,实践部分是指曹安和口传《牡丹亭·游园惊梦》。课程的考试方式则是当场抽签背唱。笔者与孙玄龄老师的交谈以及孙老师自己所写的《上善若水——忆曹安和先生兼谈其昆曲演唱的成就》[2]中详细地涉及了天韵社的曲唱。孙玄龄教授在1979年刚到中国艺术研究所不就之后就跟随已有七十多岁高龄的曹安和先生学唱昆曲,前后共计8年左右。据孙玄龄统计,他掌握了《牡丹亭·游园》、《金锁记·斩窦》、《紫钗记·折柳》、《邯郸记·扫花》、《铁冠图·刺虎》与《昭君出塞》七折。
曹先生上课时非常重视音韵学,要求学生翻阅《中原音韵》,把昆曲唱词中的每一字都标上。这种学习曲唱的方式是天韵社的独特之处。天韵社作为一个文人曲社,极其重视曲唱中的每一个音韵。老天韵社的习曲传统是“讲解音韵原理,说明曲词音韵与唱曲技术的关系”,并“教他利用韵谱(如王鵕的《音韵辑要》)查明每一歌字所属韵部及其四声阴阳的殊异”[2]。对每一字每一音的严格要求,体现了文人阶层对格律口法的钻研精神。
自新天韵社之后,孙玄龄教授不仅赠送了所有与天韵社有关的旧物,并每年赴无锡进行天韵社曲唱教学与讲座开设。孙玄龄教授作为杨荫浏和曹安和的学生,学习了正宗的天韵社曲唱,可以算作是天韵社的一份子,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孙玄龄教授的到来是把老天韵社与今天韵社串联起立的关键人物。在新天韵社众人的努力与坚持之下,老、新两个天韵社通过孙玄龄教授这“游丝一线”得以重新连接了起来。
新天韵社每年都会邀请孙玄龄教授来无锡小住,一是为了请他讲述与曹安和先生以及天韵社有关的历史记忆。二是为了向他学习正宗的天韵社曲唱唱法。2018年十一期间,孙玄龄教授从日本来到无锡,期间不仅开展了两场讲座,教授曲唱。孙玄龄教授传授天韵社唱法时,先放曹安和先生的昆曲录音,等把一曲基本会唱之后,便一字一字地进行口法上的纠正。在把每一个音韵唱对之后,会再次对比曹安和先生的录音,体会如何在曲中唱情。现阶段的天韵社已经可以唱完整折的《紫钗记·折柳》、《青塚记·昭君》、《西楼记·楼会》等等。
天韵社曲唱的传承与复兴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邀请学者普及天韵社的历史、明确今韵社的自身定位;其次,邀请知名曲家进行曲唱教学,例如苏州大学博导周秦、常州毗陵曲社社长周豪、宜兴昆曲研习社社长高峰;再次,积极开展与周边曲社的雅集交流活动,周期为一个季度举办一次。历史记载中,天韵社也经常组织雅集活动,创建交流平台。
三、天韵社器乐演奏的消逝
文人清唱是指注重曲唱表达情意,而非通过身段表演的方式,且伴奏时不用金锣等喧闹的打击乐。杨荫浏认为“惟清唱,故曲情细腻,三弦鼓板,能传古来稀有之音,使后来之研究考证者,犹能就此公园一角,二三遗老之间,寻得清唱与伴奏之丝毫遗绪。”[5]天韵社认为最能代表清曲伴奏的三样乐器为三弦、鼓板与笛,只有这样的伴奏组合可以保证其音响清越。据历史资料记载,老天韵社不仅昆曲曲唱水平高超,乐器演奏能力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老天韵社的吴畹卿、蒋旸谷、杨荫浏等擅长演奏三弦,陸振声、张敏斋、吴子芳、李朴斋等都擅长鼓板。曾有人评价“畹师之三弦已臻神境,与范君鸣琴之鼓板,沈君养卿之笛堪称三绝,故是日亦独奏为苏人所拜倒也”[11]。
虽然三弦、鼓板、笛为老天韵社的器乐传承,但他们日常也演奏其它民乐。“曲友中亦有习琵琶、古琴等乐器者,或互相指导,或受之于畹卿先生”[12],“闻该社定本月十八日起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为昆曲、古琴、琵琶、合乐四组至演奏时间”[7],从中可以看到,在老天韵社除了文人曲唱与昆曲伴奏之外,还擅长一些民乐演奏。
其次,天韵社的器乐演奏水平高超,广受好评。曾有文评价“虽弗商周古乐,而是盛世元音”[13],以及“人籁兼天籁,如闻盛世音”[14]。不仅如此,天韵社还收到电台的邀约,“无锡天韵社古乐梵音,来沪演奏,今晚九时至十二时,在亚美麟记电台演奏”[15],两日后天韵社又“应大中华唱片公司之邀,由王云楼、阚献之率领来沪,灌制唱片”[16]。
老天韵社作为清工的载体,以钻研词曲为主要目的,谈论音韵、格律与曲情,为了达到曲唱的清越意境,他们对曲唱与伴奏要求极高。吴畹卿教授社员琵琶演奏时,要求他们每天早、晚各练两小时,沈养卿认为伴奏者应以演唱者的角色而改变自身擪笛的方式[1]。
小结
复社时的新天韵社只是一个昆曲爱好者的聚集地,他们喜爱看舞台昆曲表演,喜爱跟随昆曲名旦学唱戏。他们与老天韵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并非是清工曲社。但自从他们开始搜集老天韵社的历史资料,遍访老天韵社的后人,找寻老天韵社的旧物,尤其是天韵清曲的回归,他们也开始力求成为昆曲清工。也因此,新天韵社与老天韵社之间原本的分界线被打破,逐渐融合。
新天韵社在成立之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昆曲爱好者的俱乐部,经过近8年的发展之后,它不仅找到了传承的物质载体——《天韵社曲谱》,也找到了传承人——孙玄龄教授,更是找到了精神的传承——以老天韵社为代表的梁溪风范。笔者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建构的过程 ,天韵社以曲社作为一个稳定的框架,集体记忆在其中便如一条河流在不断地流动,并对过去模糊的记忆进行塑造,使其在历史的蒙尘中逐渐趋于清晰和完整。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曹安和音乐生涯》,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3].吴曾祺传谱,杨荫浏校录:《天韵社曲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
[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编.天韵社曲谱(上中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
[6]“咸丰年间,毁于兵燹”——参见曹同文《天韵社纪事诗(六绝)》.
[7]天韵曲社昨日举行复社[N].锡报,1948-2-16.
[8]吴畹卿,名曾祺,江南著名曲家,曾任老天韵社师席长达50年.
[9]杨荫浏.<天韵社曲谱>述评[N].锡报(昆曲特刊),1937-1-1.
[10]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上海万叶书店 1952年版.
[11]禅.天韵社赴苏会唱记[N].无锡新报,1922-10-25.
[12]李静轩.天韵社溯源(下)[N].锡报,1925-10-19(004).
[13]张宗曜.聆听天韵社元音[N].锡报,1947-12-28(004).
[14]治?.汪氏芝蘭草堂聆天韻社諸公雅揍[N].锡报,1947-12-30(004).
[15]本报特别广播——无锡天韵社演奏古乐[N].申报.1947-11-1(004).
[16]本报特别广播——无锡天韵社演奏古乐[N].申报.1947-11-3(004).
基金项目:
本文为南京艺术学院2018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曲局记忆——无锡天韵社复社情况调查》(项目编号KYCX18_174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