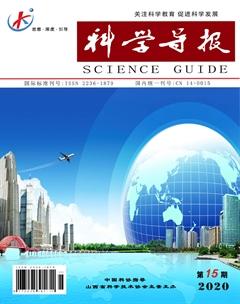满族传统刺绣的功能变迁及可持续发展初探
摘 要:满族传统刺绣深受萨满文化影响,是集生活体验、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审美意识为一体艺术形式,具有简洁、艳丽、夸张等特点,在宗教功能、礼制礼仪功能方面都曾起过重要作用,进入现代社会,这些功能逐渐被弱化,目前,在发展中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发挥优势,突破困境,在政策引导与经营拓展、传统题材的继承与发展、传统元素与现代养生的融合等方面寻找出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满族,传统刺绣,原始宗教,礼制礼仪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产生了大体相同而又有差别的艺术文化,这种艺术文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塑造了特定区域的民族民族文化性格与习惯,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艺术题材,成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刺绣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刺绣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地域性特征,如苏绣、湘绣、粤秀、蜀绣“四大名绣”,还有汴秀、闽秀等地方名秀,另外,各少数民族也有自身颇富特色的民族刺绣,满族刺绣便是其中之一。满族刺绣是在继承中原汉族传统刺绣基础上,并吸收别的民族刺绣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刺绣形式,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其画面寓意的思想内涵与情感表达,也为各民族所认同。满族刺绣是满族民族性、地域性和生活化的一种艺术形式,集生活体验、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审美意识为一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民族成长、发展、演进的全过程,是其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满族刺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满族手工刺绣技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满族刺绣功能变迁的分析,审视其当下的存在状态,希望通过该方面的研究既能对满族刺绣在功能上的演变给出学理上的建议和思考,又能为东北传统手工技艺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探寻满族刺绣在功能变迁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满族刺绣的文化内涵,以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提高人们的休闲文化情趣与品味。
一、满族传统刺绣概况
满族传统刺绣,俗称“针绣”“扎花”“绣花”,主要采用针、锥、剪刀等工具,绣出富含平安吉祥或信仰崇拜等內涵的工艺品,表达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满族妇女根据自身审美实践、宗教传统等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在这个过程中还融合了中原等地区的刺绣构图、色彩、技法,最终形成简洁、艳丽、夸张等鲜明特点。满族传统刺绣包括女真钉线、满族补绣,其技术的提高、普及与汉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大致有辽金、明清两个阶段①。
辽金时期,满族先人女真人在与中原汉族政权的长期交往中,在吸收中原汉族刺绣技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风貌的女真钉线;明清时期,满洲族在传承女真人钉线技艺的基础上,继续吸收汉族刺绣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满族补绣。也就是说,同属于满族刺绣的女真钉线、满族补绣均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满族补绣又根植于女真人的钉线。钉线是女真妇女为防止狩猎中彼此拿错工具而在箭囊和马鞍坐垫上绣的比较粗糙简单,而又能相互区别的花草鸟兽图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工艺。
尚白贵黑是女真人的习俗,所以钉线往往在白色粗布和四周边缘绣上装饰性黑线,以示“黑白分明”,整体呈现对比分明而又和谐,粗犷有力而又不失自然的风格。满族补绣虽源于女真人的钉线,但在颜色、图案的设计等方面与女真人的钉线有一定区别。女真人的钉线通常只用黑色的线,而满族的补绣在色彩上更多地吸收了汉族多种色彩并用的特点;女真人钉线多用白色粗布和白色皮革做底衬,满族补绣则吸收汉族刺绣风格,选用彩色布料作底衬;女真钉线的花边往往只是黑色花边,而满族补绣的花边往往有比较完整的花鸟图案和吉祥文字;另外,在用途上也有区别,女真人的钉线多用在箭囊、马鞍坐垫上,而满族补绣则在枕头、衣服、手帕等方面广泛使用。随着历史的变迁,满族刺绣在用色方面逐渐比较自由,但基本上以红、黄、蓝、白为主色调,这与其生活环境有关,“红色是代表太阳的,黄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水,蓝色是代表天空的”[1],并且有色彩对比强烈等特点。
在图案的设计方面,无论女真人的钉线还是满族补绣,刺绣者往往把不同物象或同一物象的不同部分进行了打散、重组,试图寻求表现内容的新形式,最终形成能表现自己情感、心愿的新画面,既展示了当地的民俗风情,也间接地反映了刺绣者的审美与情感,从而成为祈福送愿、传递情感的独特载体,是中华民族千差万别的吉祥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绣品与物象的这种差异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感知、对人生的体悟、对技法的提炼、对经验的总结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如同书画创作意在笔先一样,实现自然之物象到胸中物象的转化,最终把胸中物象一直一线地转化为一个完美的绣品。这种通过对实物的凝练概括,继而抽象表达,在“似”与“不似”之间求得平衡,实现“不似而似”的效果。
二、满族传统刺绣的功能变迁
满族传统刺绣深受萨满文化影响,在人们的日常使用过程中逐渐被强化。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原始宗教的信仰逐渐被弱化,满族刺绣中的原始宗教功能也相应被弱化。满族传统刺绣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廷,无论在婚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礼制礼仪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迁,满族传统刺绣的礼制礼仪功能被减弱。
(一)原始宗教功能及其变化
满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国东北及现俄罗斯与中国边境一带,属于高寒地带,气候寒冷,满族先民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创造了相应的物质文明,刺绣便是其中一项。最初,刺绣只是满族妇女漫长冬季不便劳作情况下,消磨时间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满族妇女的刺绣内容主要是由动物、植物、人物故事、建筑、器物、文字、几何形等组成的图案,这些刺绣纹样根植于满族先民的日常生活,并深受萨满文化的影响。萨满文化脱胎于远古时代,当时生产力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由恐惧进而敬畏,便产生了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特征。萨满教认为神的种类既有动物,也有植物,动物如鹿、马、虎、喜鹊、乌鸦、蟒蛇等,植物主要是大树,这些动植物被尊奉为神。这种敬畏与崇拜凸显在满族刺绣纹样中,天地自然元素随处可见,各种动植物俯拾即是,比如,对乌鸦的崇拜,这是满族自然崇拜的古俗,他们认为乌鸦是满族人黑夜中的守护神;再如,对鹿的崇拜,鹿往往被满族人称为“鹿神”,还被个别部落作为氏族神,在萨满祭祀中有祭“抓罗妈妈”(鹿奶奶)的仪式;另如,对马的崇拜,满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中难以须臾或离,于是马也被视为神灵,因此,乌鸦、鹿、马等动物在满族刺绣纹样中大量出现。除了以上动物,一些植物也被满族人奉为神祇,比如柳树等,满族先民认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树木,树木还是众多神灵的栖息地,于是各种树木也被神化,受到崇拜,因此,以柳树等树木为题材的满族刺绣纹样也比比皆是。供奉祖先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习俗,满族也不例外,他们尤其注重对创世祖宗的推崇,在满族人心中,这些创世祖宗是本民族的祖先神,满族崇尚的祖先神一个是布库里雍顺,另一个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打造了大清三百年的基业,被奉为神,比如满族刺绣纹样中的“努尔哈赤打虎”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满族刺绣在色彩的选用上也有明显的宗教特点,比如崇拜乌鸦,进而喜欢用黑色,崇拜雪神,进而喜欢用白色,从而形成“崇白尚黑”的特点。如上文所述满族先民认为乌鸦是他们在黑夜中的守护神,在绣品中黑色被广泛使用,满族作为北方狩猎民族,也许是当地皑皑白雪的缘故,比较崇尚白色,在萨满神话中,雪神便被称为“尼亚其妈妈”,并像人类慈爱的母亲一样,会扶危济困,救助苍生,也正因此,“清代皇宫里,对联也是白色的”[2],这与汉文化迥然不同。
以上富有浓厚萨满教风格的满族刺绣纹样作为非语言的物化符号,表现了人们对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富贵平安、友情长存、仕途顺利等价值观念的追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信仰而使用,因使用而被强化。这些富含吉祥寓意的满族绣品在被使用过程中,自身及家庭若达成了香火旺盛、平安吉祥的事实,那么这些绣品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永久记号,并代代相传,从而使得满族刺绣的原始宗教功能逐渐被强化。
满族传统刺绣是特定地域和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体现本土地域文化的手工技艺,无论在构图与造型,还是在技法与色彩的构思与表达中均蕴含自然、人、宗教元素,然而,宗教居于统摄地位,這与先民生产力水平有关。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信奉的萨满教,并将对万物的崇拜展现于满族刺绣中,表达祈福观念和心理愿望,希望依赖萨满神的庇佑得以平安幸福。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崇尚科学、信服真理不断得以强化,人们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则逐渐被弱化,满族刺绣中的原始宗教功能也相应被弱化。
(二)满族传统刺绣的礼制礼仪功能及其变化
满族刺绣在枕头、幔帐、荷包、旗袍、绣鞋等方面都有广泛使用,尤其是枕头顶绣,因其应用广泛,富含民俗元素,特色鲜明,更具有民族艺术代表性。这些各种绣品的图案本身缺乏行为符号,它只是物化符号,但作为绣品却具有了行为符号的功能,可以沟通人际关系,反映人生礼俗,满族礼俗又推动着满族刺绣的发展,比如满族的婚嫁习俗。
满族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谁家姑娘枕头顶绣得越多越好看,就说明这家姑娘心灵手巧、贤惠、能干、有家教,因而绣品图案的创作主要靠女子经验的传承、自觉的认识和真情的寄托。枕头顶绣作为满族女孩出嫁时的必备嫁妆,在出嫁前便一早忙着赶工,到结婚时,许多满族女子所绣枕顶多的达到上百对,在去婆家的路上要一路展示,以表明自己心灵手巧,到了婆家,枕顶绷在布帘上,挂在洞房最显眼处展示,技艺水平高低一目了然,技艺高者会得到婆家人、亲朋好友及邻里称赞,丈夫脸上生光,新媳妇的地位也自然就高。满族新婚女子要拿出自己最中意的枕头顶绣缝到自己和丈夫的枕头上,一部分留下自己使用,并将精品压在箱底留给女儿,还要把一部分作为见面礼一一送给亲朋长辈。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满族独特的婚俗礼仪,枕头顶绣在满族妇女的婚姻礼仪中占有重要位置,并成就了独特的枕头顶绣艺术,丰富了满族刺绣的文化内涵,使满族刺绣发展为具有礼制礼仪功能的民间传统手工艺。
在清代的满族习俗中,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人们习惯随身佩戴荷包、香囊、扇袋等小件饰品,若腰间不配香囊,会被认为衣帽不整,对他人不敬。这些饰品源于女真人用兽皮做成的囊袋,逐渐演变成精致小巧的配饰,其上绣有图案,内装香料。后来,刺绣配饰逐渐成为宫廷赏赐、官场送礼的佳品,社交的必备之物,比如荷包,荷包的“荷”与合谐的“合”谐音,因此,送荷包便有了特殊的含义,清代宫廷,皇帝在选后妃时,遇到中意的秀女,便将个荷包系在该秀女的衣扣上,表示合意,在民间荷包也成为满族青年的定情信物。可见,从满族刺绣的发展过程看,无论是其文化特性,还是在礼仪制度、人际交往、人生礼俗等方面具有了表达情感、展示才艺等象征意义,已经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欣赏、穿着用品,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儒家的礼教对女子的行为有种种的规定和限制,无权学习知识及参加工作,只能进行一些家庭小手工业或者干农活,且不作为女性的价值财富,而维持家庭运营的责任便落到了男性身上,家庭男女的这种自然分工,使得男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了男尊女卑思想和家庭妇女文化,因此,满族妇女自幼就描花样、学刺绣,并亲手绣制嫁妆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人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他们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参与其他工作的权利,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化,施加在妇女身上的与刺绣有关的传统礼制礼仪也不断被瓦解,女性不再整日忙于刺绣度日。另外,随着社会的变迁,封建时代的传统礼制、等级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满族刺绣中蕴含的具有等级差别的元素信息逐渐淡化,比如龙凤图案以及黄色的应用已不再是皇族的专利,清朝官员补服上的各种鸟兽图案也不再有阶级的涵义,已经成为现代各阶层人士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寄托。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迁,满族刺绣的礼制礼仪功能在减弱,满族刺绣作品往往成为馈赠亲友,联络感情一个媒介。
三、满族传统刺绣的优势、困境与出路
满族传统刺绣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满足并适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礼制、宗教习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迁,满族传统刺绣在原始宗教功能和礼制礼仪功能方面发生了逐渐弱化的历史变化,并且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但作为人们一度长期使用的绣品,无论在文化传承、内心情感还是在实用价值上都决定满族传统刺绣会得以存续发展,关键是要发挥优势,突破困境,寻找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的更好。
(一)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满族刺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在不断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汲取新的素材和技法,融入现代新元素,以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要,这也是满族刺绣能够继续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花纹图案,还是款式造型,满族刺绣都会对现代服装设计带来一定的灵感和参考,比如得到改进的旗袍、马褂等满族服装款式大体表现为宽袍大袖、端庄凝重的款式造型,尤其是直线式的裁剪处理,平面化的结构造型,体现出简单舒展而又端庄的风格特征,使着装者更显文雅、修长的身材,娴静、大方的风韵,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在构图、色彩等方面的运用上满族传统刺绣不自觉地与一些现代艺术理论暗合,比如光效应理论②、打散构成理论③等,从而使得画面清新脱俗,富有创意,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成为当前艺术设计汲取传统艺术元素的一个重要源泉,从而备受市场青睐。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广泛使用,传统手工艺逐渐被挤压,现代机器刺绣快速、平整、精美、价格低廉的优势日益凸显,满族刺绣也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复制,能够源源不断地满足人们不同程度的需求,但是,传统手工刺绣也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并受到收藏界的热捧,价格也一直飙升,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而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满族传统手工刺绣是由刺绣者花费大量时间一针一线绣出,饱含其辛劳、情感与智慧,其绣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了其价值量的大小。
(二)困境:在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手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交换,因此,传统满族妇女的刺绣作品大都自家使用或送予亲戚朋友,自家用不完的配饰由行庄收购,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并被转卖,以满足社会需要。这种情况决定了传统满足刺绣技艺只是在家族内传播,有面临失传的危险。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思想的解放,社会地位的提高,女人作为家庭妇女的状况在悄然变化,她们不再单纯靠刺绣消磨光阴,而是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投身自身的社会工作,男耕女织的传统劳作逐渐被现代工农建设所取代,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发展,刺绣幔帐、枕头顶等传统刺绣品類也并非家庭生活的必然选择,而少数传统手工刺绣品类越来越高端化,其收藏价值逐渐替代实用价值,从而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更多的是机器刺绣,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手工刺绣的生存空间。
(三)出路:以上一系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成为满族传统刺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为保护、传承传统民族技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政策引导与经营拓展
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固然是满族刺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也离不开国家、政府及一些社会组织的大力保护、扶持、推广,整合人、财、物各项资源,加以政策引导,使之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展示出新的活力,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要在改变传统的家族传承模式,整合资源,形成品牌,实现规模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并建立专门网站,加强宣传工作,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等方面下功夫,这样既可以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软实力,又可以带动地方旅游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新内涵,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2)传统题材的继承与发展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大力扶持、发展民间刺绣团体,聘请民间相关老艺人,深入挖掘民间刺绣素材,举办各种学习班,使这项古老工艺得以传承,在技艺、题材等方面传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传统特色的坚持与时代精神的弘扬方面,实现绣品题材的拓展,比如融合环境保护、中国故事、中国梦等时代主题。
(3)传统元素与现代养生的融合
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健康、焦躁等问题,通过传统文化的有益元素来缓解这一问题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尝试。自古至今,远离疾病、避免灭害、祈求平安都是人们的美好夙愿,满族刺绣通过一幅幅吉祥符号或图案均寄托了这种心理诉求,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呵护人们内心幸福健康的重要元素,若能加以充实、提高,则功效倍增,比如通过闻取中草药的气味实现疾病治疗,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的一个重要疗法,满族刺绣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荷包、枕头等能够容物的绣品中装入适合不同人群的具有一定香味的中草药,便具有美观、实用、健康等多种价值,对“健康中国”的实现无疑是有很大意义和帮助。
综上所述,满族传统刺绣是在继承中原汉族传统刺绣,吸收别的民族刺绣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刺绣形式,集生活体验、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审美意识为一体,是其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构图、色彩等方面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总体具有简洁、艳丽、夸张等特点。满族传统刺绣深受萨满文化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廷,无论在婚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曾具有重要的礼制礼仪功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迁,其宗教功能、礼制礼仪功能逐渐被弱化。满族传统刺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发展内涵,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需要发挥优势,突破困境,寻找出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姣.萨满文化对满族刺绣纹样的影响[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5:15.
[2] 吕佳宁. 满族枕头顶刺绣纹饰研究[D].沈阳大学,2019.
[3] 刘兴敏,王冬岩.承德地域满族刺绣文化的传承与开发研究[J].大众文艺,2019(06):56-57.
[4] 施立学,刘京.谈满族民间刺绣独有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色[J].艺术教育,2019(08):189-190.
[5] 李友友.善绣的满族妇女——承载民俗文化的东北满族刺绣[J].民艺,2019(02):79-83.
注释:
① 张成义,周松林认为,满族刺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乌桓山区乌桓族的刺绣。时至辽,丝绣业大发展,还设有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绣品,与同时期北宋刺绣并驾齐驱。女真灭掉辽建立金国后设有少府监,其下设纹绣署,刺绣之风也比较兴盛。张成义,周松林.满族刺绣纹样起源考证与研究[J].美术,2010(8).
② 光效应理论:认为眼睛在长时间注视黑白条纹构成的图形时,会出现闪烁的彩虹般的色彩奇观,20世纪50年代,现代派画家据此创造了“光效应艺术”,这一艺术对纺织品图案设计产生了一定影响。王纪,王全,王纯信著,满族枕头顶刺绣图鉴,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10,第108页。
③ 打散构成理论:就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分解成多个部分,然后根据一定的构成理念重新组合,这一做法有利于抓住事物的内部结构和特征,从不同角度去观察、解析事物,从一个具象的物象中提炼出抽象的成分,用这些抽象成分再组成一个新的形象,产生新的美感。王纪,王全,王纯信著,满族枕头顶刺绣图鉴,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10,第104页。
作者简介:孙婉迪(1994.8-),女,汉族,辽宁海城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民俗学,研究方向:区域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