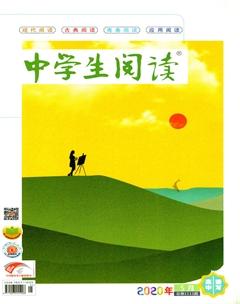春花依然盛开
迟子建
在我的故乡大兴安岭,庚子年的春节与以往的春节似乎没什么不同,含有福、禄、寿、喜字样的春联,依然在门楣左右对称地做着千家万户的守护神;高悬的红灯笼仿佛是赴了多家酒宴,也依然在小城的半空,呈现着一张张红通通的醉脸;噼啪燃响的爆竹也依然给洁白的雪地撒上一层猩红的碎屑,仿佛岁月的梅花早早绽放了。但今年的春节又与以往有所不同,拜年串亲戚的人少了,聚餐聚会的人少了,外出佩戴口罩的人多了,围聚在电视机前关注疫情动态的人多了。
是的,去年年底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像一条不断拉伸的毒蛇,已蔓延全国。当太阳在蒙着霜雪的玻璃窗后冉冉升起时,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疫情动态。看到雄鸡版图的深红颜色范围逐日扩大,警报一声比一声急,我的心阵阵作痛。这期间一些读者和友人给我留言,说在重读我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我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由俄国西伯利亚传人哈尔滨的大鼠疫,清政府任命剑桥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伍连德亲临哈尔滨指导防疫,他在一个简陋的平房里,做了中国医学史上首例尸体解剖,发现这是一种可以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肺鼠疫。在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他果断上奏朝廷,要求控制铁路和公路交通,调动陆军封城,在哈尔滨傅家店设立隔离区,家家户户消毒,号召疫区人们佩戴口罩,而这种号称“伍氏罩”的口罩,也是伍连德发明的。它是用双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做成的能遮住人半张脸的口罩,能有效抵御飞沫感染。现在口罩奇缺,“伍氏罩”是否依然适用?如果可行,纱布和棉花易得,相关企业可以加班加点做口罩。我当年在省图书馆查阅鼠疫期间出版的哈尔滨报纸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趣闻和广告,有哄抬物价的不良商家,更有慷慨捐助防疫物资的有情有义的商人。有被鼠疫吓得精神失常的懦弱者,也有不惧感染给患者送饭的有担当的百姓。那时人们迷信用生锈的钉子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所以锈钉子成了金子。但最终战胜鼠疫的,还是科学。我的《白雪乌鸦》有两章的小标题,就是《封城》和《口罩》。
初六我从故乡小城返回哈尔滨时,火车站是层层设防的检疫人员。由于我捂得太严实,体温在临界值,医务人员让我暂留。摘掉棉帽和围脖再测,结果显示正常。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而体温异常者均被安置到隔离区。登上列车,见所有的乘客都佩戴口罩,车厢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这次的疫情防控是决策科学、积极到位的。医疗战线的人员在一线救死扶伤,作家们此刻能做什么?黑龙江省作协发出了对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倡议书,号召作家在积极配合防疫的同时,用手中的笔,书写和记录这个时期的感人时刻、动人瞬间。我们的倡议书发出仅仅几个小时,专有邮箱就收到了几十件原创投稿,作者中有九十二岁高龄的老诗人,也有在校的大学生。他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传递给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您外出佩戴口罩,就是对他人和自己最大的关爱;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向疫区武汉的每一个居家留守者致敬,同时也友善对待在外省的武汉人,当然每一个在疫情高发期出来的武汉人,因为病毒存在潜伏期,即便您没有症状,也要先期做好个人防护,防患于未然。前年两会白岩松做了一个提案,大意是说如果放纵地域歧视,容易造成一个民族的撕裂。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碰见他,说我要给你的提案点个赞。此时万众一心地科学防疫,所有人都是手足。
我相信病毒这条毒蛇,终究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消灭,春花依然会迎风盛开。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東西太多太多,比如:我们是否把野生动物看作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在山里长大,知道它们也有满含着情感潮汐的湿漉漉的眼睛。我们的社会公德心该如何加强?我们对医疗的投入是否有待加大?等等。
(选自2020年2月1日《黑龙江日报》,有改动)
阅读点击
文中插入《白雪乌鸦》的情节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