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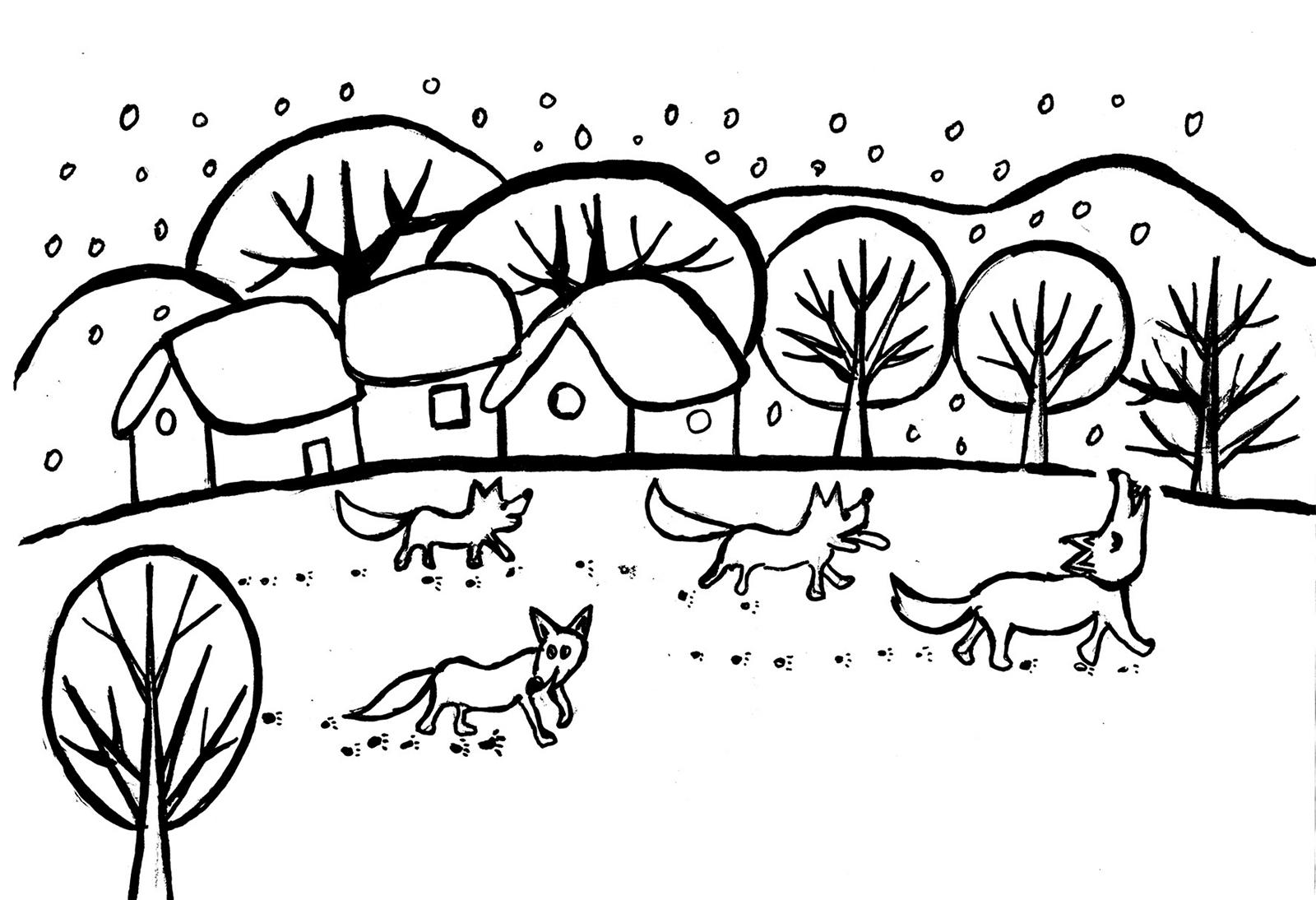
来自草原的苍狼
大雪下了几天几夜,山地上白茫茫一片。
雪后总是要刮风的,大风。那风长了翅膀,裹挟着雪雾,长了毛一样,在山地上撒泼打滚,像一群淘气的疯孩子。
大风很多时候会在有月亮的夜里停歇下来。
道路、河谷、草地、农田,都被风雪抹平了。月光在上面滑过,一水的亮白。
野兔们在洞窟里猫了几天,开始探头探脑打量这个明晃晃的世界。几棵老树扭伤了腰身,折断了枝丫,道路也没了踪影,眼前是个完全陌生的冰雪世界。但是,也有松塔从高不可攀的树冠上刮落,也有挂在枝头的干果被摇落到了地上。野兔们转动大大的耳朵,开始探听洞外的消息。
“嗷……”
“嗷……”
这时常常会传来草原苍狼凄厉的号叫声。
红山文化发源地的故乡,紧挨着科尔沁草原。那里的雪更大,食物更匮乏。草原苍狼会越过低矮的丘陵,穿过背风的山垭口,顺着古老的狼道来到这片山地。它们知道,山地里散落着树木籽实,那散发着秋香的颗粒是山兔与田鼠的最爱。而那些温热的血肉之躯,可以让它们熬过寒冷的冬天。
“嗷……”
草原苍狼的嚎叫透进窗子,让孩子们在被窝里紧紧抱住大人。想象它们月色里亮黄的眼珠、冷森森惨白的牙齿,胆小的孩子脊背发凉,恨不得缩到妈妈的身体里。
大人们却一点儿也不害怕。村庄里的狗也不冲着山野吠叫。公鸡们在黎明时分照样此起彼伏打鸣,仿佛村庄外面十分安宁,并没有那些远道奔袭而来的杀手。
事实上,草原苍狼从来都不攻击村庄。它们在山地里捕猎那些肥硕的野兔,还有脑满肠肥的田鼠。山地的豆粒、籽实,漫山遍野,它们拿走了人们的果实,虽然没有人少见多怪,但却也都担心它们过度繁衍,与人争食。草原苍狼的到来,正巧控制了那些鼠科动物的泛滥。
月光清冷。雪地上的脚印被草原苍狼踩得十分零乱。
那些刚劲的利爪,要在雪地上刨画一个冬天。
大雪吱儿、吱儿地在阳光下融化时,草原苍狼才会在山地里消失,大雪再次到来之前,它们都会无影无踪,好像它们从未在山区里杀戮过。
但哪个孩子会记不住那些回归故乡的草原苍狼呢?
亮白的月光下,雪地中冷森的白牙,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
“嗷……”
羊群上空的老鹰
羊群是村庄的宠儿。
牧羊人是村庄里最浪漫的人。
群山、田野、河流、草地、白云、清新的空气、自由的行走,牧羊人放牧羊群,也放牧白云,他是村庄里最自在的诗人。
夜里,牧羊人的家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熟悉村庄周边的一切。春天哪片野荆花最先开放,夏天哪棵野杏树最先熟甜了果实,秋天哪处的野枣树最先红灿灿一片,冬天哪只小野鹰最先学会了捕食,都是牧羊人最先發现的。
孩子们最爱探听关于野鹰的故事。
村庄南面五六里地,是落鹰崖,那是方圆百十公里的高地,险峻、陡峭,正适合野鹰栖息。
羊群是野鹰最好的一致行动人。
野鹰在天空上盘旋,常常在蓝天上定格。它们追随羊群在山地上漫游,黑青色的翅膀在草地上移来移去。
突然,羊群惊动了在树窠里隐藏的野兔。羊群炸开,野兔奔逃,慌不择路。也许野兔知道天敌就在天空,它的逃跑是蹿跃式的。
但野兔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野鹰仿佛黑色的闪电,一道黑影划过,野兔已在鹰爪之下,迅疾滑向天空。可怜的野免,四个小蹄子在空中胡乱踹踢。
“咩……”出生不久的小羊羔懵懂地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它和善的眼睛里还有丝丝惊恐。母羊却视而不见,因为刚才的一幕它已看过许多遍。
但是,野鹰的俯冲也有失足的时候。牧羊人就曾经救助过一只折断单翅的野鹰。他给大鸟扎好骨伤,看着它侧歪着翅膀斜飞向天空,消失在头顶无尽的蓝色里。
牧羊人说,他从此再没见过那只折翅的野鹰。
他说,那只鹰也许变成了蔚蓝天空中的云呢。
他继续牧羊。
照样有野鹰追随着羊群。连草原苍狼都远远避开,野鹰连苍狼都敢捕捉。
羊群、野鹰、无涯的山地与天空,一切都仿佛伴生着,相互依存。
田鼠大妈
田鼠在山区是被称为“田鼠大妈”的。
这称谓实足地形象。
那些与山地肤色一样的生灵,体态饱满,神情自若。它们刚从豆子地里出来,怀揣着果实,在人们面前列队走过,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
田鼠大妈的洞穴一般隐藏在长满荆棘的沟坎里。隐蔽,巧妙。它们一般会在五六平方米的范围内设立三四个洞口,有气孔,有明路,有暗门。
它们的四个小爪子会打洞,却不会种田,便只能靠山吃山。好在山地中食物不断,春天植物的根茎甜润;夏天各种果实漫山遍野;秋天更是籽实满地;冬天它们粮仓里的储蓄十分充实。
田鼠大妈掠食庄稼,但并不冒犯土地的主人。它们像那些生存在同一块山地的女主人,勤俭持家,但从不让哪块田地绝收,它们总是在洞穴四周的田地里,每样食物都索取那么一点点儿。
田鼠大妈热爱储存余粮的美好品行,曾经救济过整个村庄。
一个人祸大过天灾的冬天,没有余粮的人们开始在山野里寻找田鼠洞穴。当散布在沟沟坎坎的田鼠家园被挖开,人们仿佛开仓放粮一样兴奋。黄豆、黑豆、玉米、高粱,还有人们不屑一顾的野杏仁、野枣核、野松籽,应有尽有。最大的田鼠仓里,可以挖出几十斤食物。
这些余粮让断粮的村庄重新升腾起折断的炊烟,让人们平安度过了饥馑的冬天。瘦弱的孩子补充了营养,村庄里恢复了孩子们做游戏的笑闹声。
人们在饥年理解了田鼠大妈的好,也体会了它的不容易。想到它被人们劫走了储蓄的粮食,它的孩子们被草原苍狼和饥饿的人们追杀,它们该如何挨过白雪皑皑的冬天?
当还没有人生阅历的孩子们抱怨田鼠大妈时,大人们总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和田鼠大妈在一块地上过日子,分点儿食物给它们,不是应该的吗?”
而这句代代相传的嘱咐里,透出了多少人生的苍茫……
仓房里的家雀儿
山野里,收割后的田地间,总要立着许多仓房。那些用秧棵垒砌的建筑,陈放着秋天的籽实,储存着一整年的香气。
在村庄里,最美的香味儿该是果实的气息。麻雀是村庄里话最多的孩子。
黎明,它们小小的翅膀去迎接第一缕阳光,好像想借机把灰色翅膀染黄。
白天,它们想方设法接近谷仓,成群结队。它们蔑视看仓的风车和假人,一路调笑,嘚儿,嘚儿,经常像旋风一样飞掠。
麻雀们知道,它们和村庄里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大地上所有生物,都和它们一起生长。
最先被麻雀把眼睛啄出的稻草人,先是眼眶成了鸟儿的洞窟,很快它又在一个雪天折断了腰身。谷仓的气孔,也很快成为了麻雀们进出的大门。
看仓的人在雪地里巡逻,对飞翔在谷仓上空的麻雀视而不见。他手中的铜锣害怕惊吓了麻雀,从来就没有敲响。村庄里最有权威的那个人,也从来没有责怪过他的不作为,更没有责怪过麻雀的顽皮。
大声喧哗,在村庄上空飞翔,这些麻雀,多像村庄里被大人们惯坏了的淘气小人儿。
村庄里的人,从来不会去捕捉和伤害麻雀。老人们总是嘱咐那些年轻人说:“假如没有孩子叫,没有鸟儿飞翔,那村庄还是村庄吗?”
所以,在山区,人们亲切地叫麻雀为“家雀儿”。
没有了这些以村庄为家的“家雀”,山区就没有了飞翔的梦想,就没有了关于天空的想象,这样的村庄,得有多么空旷……
梦想是人类的特征。而麻雀们小小的翅膀,驮载了山野的灵魂。
柳林莺啼
山野上,围绕着村庄的,总会有一片柳林。
高高的白杨树多像村庄里挺拔的小伙子,而柳林像极了村庄里婀娜的姑娘。
柳林里的鸟儿,叫柳莺,啼叫声尖声细气。它们的翅膀娇小,绿中带黄,阳光照透羽翎,闪着莹光。
柳树总爱站在小河边,柳枝总爱垂在水里。浪花流经这里,是要熄灭笑声的。因为浪声一响,就会淹没柳莺的啼鸣。
村庄里再淘的男生也不会去用弹弓打柳莺。
柳莺是村庄里的女孩儿。
欺负女孩儿是要被村庄里的人嘲笑的。
那嘲笑又有戏谑的味道:“从小就欺负女孩儿,长大了谁敢给你做媳妇儿。”
柳莺就那么安静地、细细地叫着。
它们偶尔也会成群结伴去探望附近的村庄。那些纯朴的村庄,住着对女人最温和的男人。
而那些男人,像遍地的丘陵一樣宽厚与和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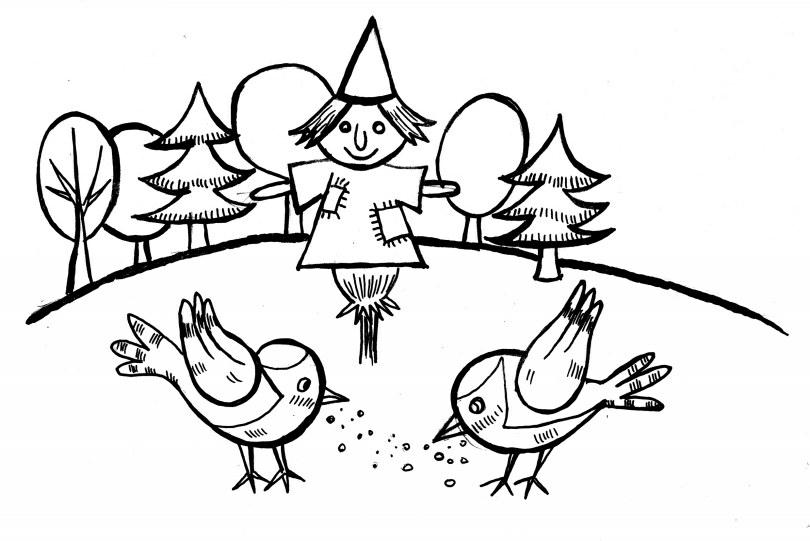
雪地上的火狐在冬天才像火一样红,仿佛要点燃冬天。
它们是机警的动物,春天在花丛中出没,夏天与繁茂融为一体,秋天像阳光一样斑驳。
冬天,山野最先被霜染黄。
阳光晒干植物的水分,放眼一望,处处枯黄。
野狐在此时出现,油亮亮的皮毛红光闪亮,阳光照在上面,仿佛照在梦上。
火狐的出现真就像梦一样。
它们是悄无声息的,蹑手蹑脚,机警的眼睛从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觉到危险,它们立刻会从你眼前消失,就像水渗入沙滩一样。
火狐在雪地里行走时才是最美的。
初雪,大地白得太不真实。天的蓝有白的雪衬托,越发纯净透澈。
但是,天气太冷冽了。
火狐就在这时在雪地里出现,像一团火,高抬的大尾巴像火舌。
虽然它没有点燃雪地,但燃烧了窗子后面观看的眼睛。它让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是美好的事物,更让孩子们相信了,这个世界即使如此寒冷,也存在生动的小精灵……
花媳妇儿喜鹊
村庄里最被善待的鸟儿,是喜鹊。
喜鹊长相可爱,黑白分明,人们都叫它们“花媳妇儿”。它们爱在高处做窝,爱在谁家房前屋后的树上扎营。它们是欢乐的鸟儿,每一声叫都像欢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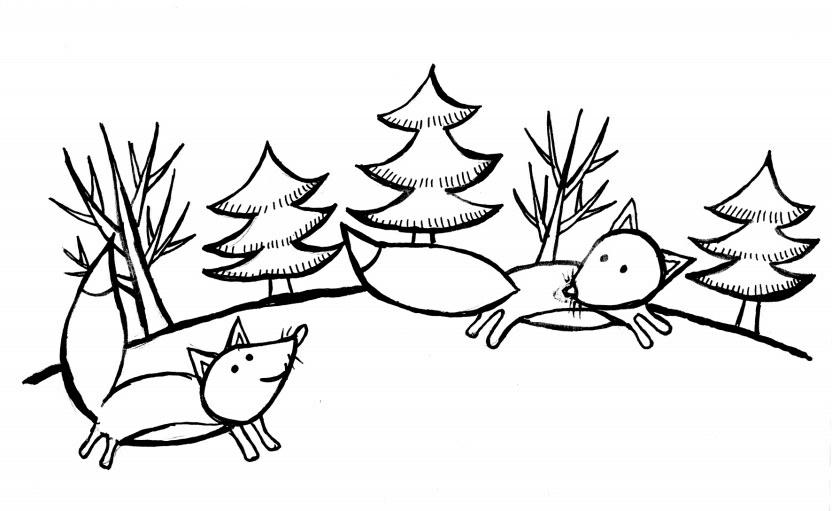
如果谁家娶媳妇儿,办喜事,它们赶来庆祝,一天到晚叫个不停,叫得喜悦的人们心情更好,便更喜欢这些喜庆的鸟儿。
喜鹊还是山村最好的建筑师。它们高高在上地筑窠,从远处衔来第一根树枝开始,往返上千次,费时几个月,完成这项复杂的工程。
它们的小窝结构合理,稳固扎实。从此睡在里面,无论刮风下雨,都能沉淀自己的梦想。
喜鹊们还像村庄里的居民一样热爱家乡。它们围绕家园觅食,生儿育女,在窝边歌唱。喜悦的日子,会招集来众多的伙伴儿,欢聚一堂。
因为有了喜悦的叫声,村庄里再郁闷的日子都透进了光亮。
人们赞美喜鹊的歌谣也在村庄里回荡。
胖小子,小胖子儿
门前种树勤浇水儿
树上住着花媳妇儿
长大娶个花媳妇儿
选自《少年文艺》2020年第5期
老臣,儿童文学作家,著有《远山风景》《女儿的河流》《漂过女儿河》《眼睛的寓言》等,出版“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收入多种文集选集及大中小学教材。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