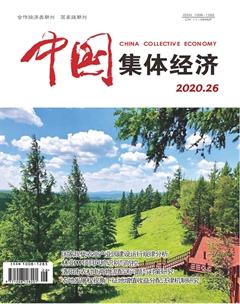个人信息权的规范构造
郭小伟 孔硕
摘要: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领域,现有三部较为成熟的个人信息权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但其对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上仍存在规定不明确、不完善之处,规范形式有待商榷。在明确个人信息权与其各项具体内容是权能体系的基础之上,从个人信息权的支配权能、请求权能、收益权能、救济权能四个方面对个人信息权的具体权能进行规范构造,并就如何在即将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更为合适的相关规则提出建议。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能;规范构造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现行制定法层面除《民法总则》第111条首次明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态度,但在私法层面上仍缺乏完整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体系规范,并且没有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及救济方式,不利于民法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这导致了实践的极大困惑,使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在实行层面上陷入困境。鉴于此,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背景下,为更好地保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由学者们负责起草的三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建议稿都明确规定了涉及个人信息权地内容的条款:
周汉华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下称“周汉华版“)分别从政府机关和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两个方面规定了信息主体获得个人信息的权利以及更正与停止使用权,分别在第16条、第28条、第49条和第50条。
齐爱民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学者建议稿)》(下称“齐爱民版”)在第二章专章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及其内容,从第11条到第19条分别规定了个人信息权、信息决定权、信息保密权、信息访问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可携权、信息封锁权、信息删除权、被遗忘权。
张新宝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下称“张新宝版”)在第13条“个人参与原则”提到了“知情权、同意权、查询权、更正权、拒绝权、删除权”,并在第四章“信息业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明确规定了“信息主体查询权、信息主体更正权、信息主体删除权”;第五章“政务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明确规定了“信息主体查询权、信息主体更正权、信息主体停止处理权”。
从形式上比较三部建议稿,“周汉华版”和“张新宝版”对个人信息权具体内容的规定分类不够清晰且不完整,“齐爱民版“虽然将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专章规定,但也存在与建议稿内其他章节规定大量重复的弊病。由此可以发现,在承认个人信息应受保护的前提下,三部建议稿在个人信息权的具体权力内容上有较为明显的分歧。本文拟以分歧为基点,结合归纳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侵害个人信息的典型情形,构建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探寻三部专家建议稿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并就如何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更为合适的相关规则提出建议。
二、个人信息权是权利体系抑或权能体系
上述三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建议稿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权利内容的性质是具体权利或仅为个人信息权的权能,换言之,个人信息权是权利体系还是权能体系?权能,可理解为权利之能,具体说就是指权利具体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一项权利包含多个权能,一项权利是由一束权能构成的。
总体上来看对于权利内容的体系安排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概括性权利——一般权利和具体权利”模式,可类比的典型范例,如人格权及其下位的一般人格权和各项具体人格权。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明确规定了10项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和3项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具体人格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第二种模式是“具体权利——权能”模式,可类比的典型范例,如债权及其包括的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债权保护请求权、处分四种权能。
权利和权能不是机械的包含关系,而是有机的组成及作用关系。对于权利与权能的区分,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提出了一个包括四种相关性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
权利(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无权利(no right)
权能(power)—责任(liability) 豁免(immunity)—无权能(disability)
霍菲尔德所使用的“权利”主要是指可以要求他人如何行为,“义务”则是响应他人的要求权而必须实施的行为。“权能”意指“法律上的能力(legal ability)”,即可以单方施加控制以改变既定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的能力,“责任”则是对“权能”的承受,即必须接受对方所做的改变。
据此推断出权利与权能的区分标准。第一,单方控制性。如果完全处于主体的控制之下,则为权能。如果仅为主体可以要求他人做的,则为权利;第二,必须承受性。如果他人必须承受这种改变或者创设,则为权能。如果只须响应要求,则为权利;第三,一次价值性。改变既定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后就失去原有价值的,则为权能。换言之,权能一般不可以转让,其不能够独立成权,转让后的权能对转让后的主体没有任何的独立价值。
以这三项区别为标准,可以推知三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建议稿中规定的权利内容是权能,理由如下。
第一,单方控制性,它们处于信息主体的完全控制之下。以信息决定权为例,信息决定权是将个人信息是否被收集、处理与利用以及以何种方式、目的、范围收集、处理与利用完全直接控制并支配。且以信息主体的个人权利来制约违法信息处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单方控制性的要求也是提高个人权利保护效率的应有之意。
第二,必须承受性。在信息主体行使具体权利内容后,相对方必须承受这种改变或者创设。以信息删除權为例,在信息主体提出删除个人信息后,相对方必须删除。
第三,一次价值性。信息主体行使具体权利内容后等后将不能再次请求或者再次行使没有任何意义。以获得个人信息的权利为例,在信息主体要求相对方提供个人信息后,再次请求获得相同的个人信息将再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周汉华版”、“齐爱民版”、“张新宝版”专家建议稿中,“齐爱民版”将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专章规定,“周汉华版”、“张新宝版” 并没有明确地使用 “知情权”或 “同意权”等表述,更多的是以原则的方式列出。实际上,上述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要么是实现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形式,要么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手段。它们是个人信息权的内涵与外延,是依附于个人信息权而存在的,不同于肖像权等摆脱人格权仍能独立存在之权,因此它们没有资格作为单独的权利存在。综上,个人信息权是权能体系。
三、个人信息权权能的规范构造
个人信息权的权能构建关系到信息主體的民法保护,因此其具体展开必须明确、合理,才能对个人信息权的侵权起到相应的救济作用。本文认为个人信息权的权能包括支配权能、请求权能、收益权能和救济权能。
(一)个人信息权支配权能的规范构造
“周汉华版”中“更正与停止使用权”中的“停止使用权”属支配权能的范畴,“齐爱民版”第二章对个人信息权作了专章规定,属于支配权能的只有第12条规定的信息决定权,“张新宝版”中的多次涉及的“同意”和“拒绝”属于支配权能。本文认为,个人信息权的支配权能是信息决定权,即个人信息权人得以直接控制与支配其个人信息,并决定其个人信息是否被收集、处理与利用以及以何种方式、目的、范围收集、处理与利用的权能。实际上,信息决定权足以涵盖信息同意权与信息拒绝权,无需将同意权和删除权单独列出。
(二)个人信息权请求权能的规范构造
整体上来看,对支配权和请求权的规定比重不适当且请求权能中的部分权能有重复。本文认为,个人信息权的请求权能包括信息更正权、信息可携权、信息知情权、信息封锁权、信息保密权。“齐爱民版”提到的“访问权”以及“张新宝版”中的查询权实际上都可被知情权所涵盖。对于删除权,被遗忘权,不作为单独权能提出。因为个人信息电子化后,特别在网络环境下,被删除、被遗忘的信息通常有备份,在技术上可被恢复,彻底清除目前不具备技术可行性。信息主体甚至无从知悉这些信息被哪些主体存储于及存储过何处,也不知其泄露来源和散布方向。即便在能够找到的服务器上作了删除,向搜索引擎确认身份后要求其采取筛除和屏蔽措施,也无法保证这些信息真的被彻底遗忘而不传播。网络空间没有严密的围墙和坚实的堡垒,依靠围堵封锁或删除清理并无可操作性,一项无从实现的权能没有存在意义。
(三)个人信息权收益权能的规范构造
个人信息收益权能是指信息主体具有的在法律上得以证立的,在信息收集人或控制人基于商业目的收集、加工、利用及传输其个人信息时,有权收取或获得利益的能力。“周汉华版”、“齐爱民版”、“张新宝版”专家建议稿均未提到收益权能。信息的流通使得信息财产性渐渐凸显,加之“定制化”经济的发展使得产品精准投放与个人信息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信息权以收益权能,以保障信息主体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价值的实现。
(四)个人信息权救济权能的规范构造
“周汉华版”只规定了侵犯个人信息权后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并未明确信息主体的直接救济权能。“齐爱民版”第40条规定了“损害赔偿”和第41条分别规定了“精神方损害赔偿”,第42条规定了“共同侵权责任”,第43条规定了“其他法律责任”。“齐爱民版”第40条也是从侵权人的角度进行规定,第41条和第42条明确规定了信息主体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共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张新宝版”将救济专章规定,第88条规定了信息主体向侵权的信息业者请求救济的途径,包括“与信息业者协商;请求个人信息保护组织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信息业者所在行业协会投诉;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根据与信息业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新宝版”对救济权能的规定足够详细,构成了信息主体救济权能的体系。
四、结论
在三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草案的基础上,个人信息权的权能可构造为个人信息支配权能、个人信息请求权能与个人信息收益权能与个人信息权的救济权能。个人信息权四种权能具体作用的表现形式即为信息决定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可携权、信息知情权、信息封锁权、信息保密权、信息收益权、信息救济权等。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对信息主体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民法作为私法的任务与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对个人信息权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对即将到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科学的、明确的、规范的权能构造,才能适应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齐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学者建议稿[J].河北法学,2019(01).
[3]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J].清华法学,2018,12(05):143-158.
[4]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46.
[5]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ed. by David Campbell & Philip Thomas,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2001:12.
[6]鞠晔,凌学东.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问题及法律救济[J].河北法学,2016,34(11):52-60.
[7]陈振涛.个人信息权的权能构造及权项分析[J].福建法学,2017(01):59-66.
*基金项目: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研究”(S201911066004)。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