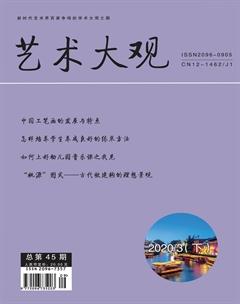从神话故事到影像叙事:哪吒形象之演变
魏毅
摘 要:神话故事是我国当下影视题材改编的重要来源,哪吒形象从西域佛教传入我国,并在唐宋时期开始有了具体的记载与描述,到明代的《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有了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刻画。其故事原型跌宕起伏,具有情节剧电影的叙事特征,为后世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灵感来源。《哪吒闹海》与《哪吒之魔童降世》都对原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与再现,完成了从神话故事到影像的再度创作。
关键词:神话故事;影像叙事;哪吒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09-00-02
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千年的神话典籍为电影故事的创作与拍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从先秦古籍中的《山海经》、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再到晋代的《抱朴子》、明代的《封神演义》中都记录了大量的古老神话和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影视剧的不断创作与改编,将之从文本描述到影像的再现,成为代代流传的精彩典故。2019年7月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通过对《封神演义》中哪吒故事原型的颠覆式改编,再度让哪吒这个神话形象得到了新的诠释与演绎。
一、哪吒形象溯源
在宋代的《五灯会元》中有关于哪吒剔肉还父的故事的叙述,在元代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有关于哪吒形象较为具体的描述,将哪吒与妖怪交战时形容为“三头飐飐”“六臂辉辉”,这时期哪吒三头六臂的外形特征并没有在电影作品中出现。今天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主要来源于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许仲琳的《封神演义》。
《西游记》中对哪吒与孙悟空的交手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一时期的哪吒已经从《五灯会元》中的三头六臂的形象逐渐转化为人的外形特征,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在《封神演义》中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到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这三个章节具体讲述了哪吒出世、杀死巡海夜叉李艮,抽去龙太子敖丙龙筋,大战东海龙王敖光、到误杀碧云童子、最后剖腹剔骨还父、托梦母亲建立行宫,再到后来的父子反目、莲花化身、被元觉洞燃灯道人罩入玲珑塔里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这些情节的描述集中展现了明清小说家们丰富多彩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直接为后世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
二、从文本到影像中的“哪吒”
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中将叙事虚构作品的三个要素概括为故事、本文和叙述。而《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原型正是具备了这样三个基本要素,即用紧凑的结构、展开生动的叙述、讲述了精彩的故事。依照米特里对电影叙事的划分,李显杰将电影分为情节剧电影与非情节剧电影。“米特里所说的悲剧形式和小说形式,实际上是指电影叙事中的情节性结构模式,即传统电影模式,以波德威尔论述的‘好莱坞经典电影为典型代表”。[1]《封神演义》正符合情节剧电影的结构模式。把平凡的形态加以强化,展现出超常的生活形态,也更符合当今观众的审美趣味。在短短三章的叙述空间中将人物关系的变化进行压缩和突变。更讲述了哪吒诞生、剔骨还父、托梦母亲修筑行宫、起死回生这几个大起大落的人物行动线,塑造了父亲李靖、太乙真人、东海龙王敖光、龙太子敖丙、石矶娘娘、文殊广法天尊、燃灯道人等各具特色的风格化人物。因此,在以情节取胜的《封神演义》的版本中,几乎全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元素。“情节剧往往突出人物的本质,让善或恶集中于一身,使人物成为风格化形象。”[1]这是当今大部分以哪吒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大量取材自《封神演义》的重要原因。
三、从顽童逆子到正义小英雄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与2019年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是最为关注的两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保留了《封神演义》中哪吒传奇出生,不过将原著的“肉球”变为一朵粉红莲花,花瓣层层脱落,哪吒赤身蜷坐花蕊。与原著中的形象做了更为接近人性化的加工和美化。
《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因为天热难耐,下海洗澡,震动龙宫而引发巡海夜叉李艮的质问从而产生了矛盾。虽然二人大打出手的原因是李艮动手在前,但哪吒先扰乱东海,面对夜叉出言不逊,似乎也难逃挑衅之嫌。《哪吒闹海》中则直接将这一情节改编为龙王敖丙派夜叉捉走小孩,哪吒严厉质问而产生的矛盾。将原著中的正邪对立设置得更加鲜明集中。电影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长中保留了原著《封神演义》中宝德门独斗敖光、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等情节,略去了石矶娘娘为徒儿复仇、燃灯道人金塔收服哪吒、父子反目成仇等情节。为观众呈现出的是一个有情有义、惩恶扬善的小英雄。
四、“略神得形”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陈吉德的《影视编剧的艺术》中将影视作品对原著的改编分为:形神兼备、得神略形、略神得形和形神皆略四种情况。其中,“形式指原著的人物和故事,神是指原作的主题和意蕴”。[2]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遵循了原著的人物基本行动线索,却将人物的内在品质做出了脱离原作框架的重新演绎与再现。为时隔40年后的动画电影巨作《哪吒之魔童降世》提供更为可行的改编思路,可谓是改编中的“略神得形”。
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较之1979年的《哪吒闹海》,无论从人物形象、情节安排还是场景建构,主题意蕴都做了对原著故事的消解与重构。
在人物设置上,申公豹本在原著中第十二回到第十四回描写哪吒的章节中并没有出现,在影片中成了最大的反派,而师父太乙真人打破原著中仙风道骨、淡然稳重的做派。变成一个酗酒成性、大大咧咧的糊涂老头。从声音设计上,一口地道的川普也再次颠覆了人们对固有形象的认知,将修炼成仙、道法高深的神仙形象加入了更立体生动的人性化塑造。“‘神属于天地宇宙之造化,不是一般人力可以达到的;‘仙则是人经过后天刻苦修炼,经过虔诚追求而达到的境界”。[3]可见无论是作为“神”还是“仙”的形象,影片刻画的太乙真人都与原著大相径庭。
对于李靖、殷夫人的刻画都加入人物的精神内核,在原著中,殷夫人虽也表现出对哪吒的关心,但影片中加入了她陪子玩耍,为子设宴等重要情节。父亲李靖在原著中本与儿子哪吒变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影片中却俨然变成一个替子受罪,悉心教子,为子舍命的慈父形象。这一改编,让观众观看时迅速找到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维系,更为接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此外,夜叉的出场也较原著有所推后。影片中的夜叉不再是原著中奉命巡海的李艮,而是一个善于隐身、丑陋滑稽的海夜叉,跟原著中导致哪吒大闹东海的关键情节点并无关联。敖丙的出场帅气逼人、冷峻飘逸,是背负着振兴龙族使命的希望所在,也早不再是原著中蛮横骄纵被抽去龙筋东海三太子。至于原著中的石矶娘娘、燃灯道人等形象更是无迹可寻,删去了对主题无关紧要的人物。[4]
在情節安排与矛盾设置中,影片将原著中哪吒与敖光的矛盾弱化,将陈塘关百姓对哪吒魔丸身世的偏见与恐慌不断升级强化。将个人与群体、个人内心冲突的矛盾上升为该片主要矛盾,将原著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消解。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寻找自我认同、他人肯定、反抗宿命的铁骨小英雄。无疑更有利于观众在他人与自我的对立关系中找到自我成长与完善的认知共鸣。
影片的场景建构也可谓是颠覆原著的一大亮点,首先舍去了哪吒与敖光单独打斗的宝德门,取而代之的是浓墨重彩渲染的奇幻场景——“山河社稷图”,里面水柱冲天与满池荷花交相辉映,经过精心细致的调色处理,展现出了一个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至美仙境。而原著中东海龙王的水晶宫殿变成了一座湿冷黑暗、缠满铁链的阴森地牢。更添加了李靖救子心切去拜见元始天尊的“空虚之门”。而这正体现出他的愿舍命救子的决心。影片最后的生日宴陈塘关大战的情节中,哪吒与敖丙合体对抗天劫咒。在一片刀光火影、电闪雷鸣中二人联手作战、将影片情节推向高潮,升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主题。[5]
综上所述,《哪吒之魔童降世》对神话故事《封神演义》的再现,是人物、情节、场景、主题价值观的一次大胆解构与重塑。这种改编方式可以归结为张觉明在《实用电影编剧》中提到的“取材式改编”,即原著只是为改编提供一种素材,改编者在次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重构、组合和再创作。也让哪吒这个源于古代神话故事的传统形象彰显出了符合当下时代价值观的新的生命特征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李显杰.电影叙事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2]陈吉德.影视编剧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6.
[3]刘春阳,兰南.神话形象漫谈 动画作品中的神话人物[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4]张觉明.实用电影编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5]付方彦.哪吒形象流变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