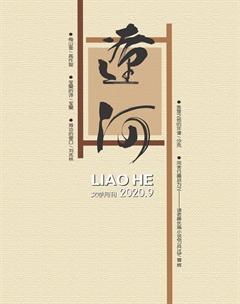赛华佗
余悦妍
1996年的夏天,我在南方某个小镇一家电子厂打工。那时候,我遇到过很多事情,但在流逝的岁月河流里,很多事,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淡薄,但“赛华佗”永远历久弥新。
一个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腿上有虫子在爬。白天工作太累,我不想起来,便随手把虫子一甩,又迷迷糊糊继续睡。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右腿痛,抬起一看,发现右腿上肿起个鸡蛋大小的包,硬硬的,一碰就痛。我急得想哭。
我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打工妹,工资不高,舍不得去看医生。两天后,肿包更大了,而且愈发疼痛。我实在忍受不了,下班后,匆忙赶到镇上医院去看医生。我站在医院大门口,看看包里羞涩的钞票,徘徊了好久,还是转身离开了。
但腿上的伤口痛得我无法忍受,不得不寻寻觅觅,反复比较,终于寻到一个私人小诊所。这小诊所室内外装潢得古朴典雅,像中医诊所。我想,可能中医会便宜些,就试探着走进去。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一看他就是本地人。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华。
华医生仔细检查了我腿上的肿包,说:“好在来得及时,你的皮肤过敏,再不医治后果会更严重。”说完,他拿来一张膏药。我也没注意到正面印的是些什么字,只看到反面画着一只黑色癞蛤蟆。这个图像让我感到有点儿恶心。
我有点儿担心地问:“华医生,癞蛤蟆药能治这个吗?”
“我系边个啊(我是哪一个)?我是赛华佗!”华医生笑着用半粤语半普通话得意地说,然后很肯定的保证,“药到病除,保证!”
你姓华就是“赛华佗”?那我姓李,我岂不是“赛李白”!他的保证,令我不安。我有点儿后悔到这里来就医。可是已经来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苦着脸让他贴膏药,他又开了打点滴的药方,交给他老婆去配药。
他老婆扎着低马尾辫,衣着普通,像农村妇女。我隐隐担心,她会配药吗?万一配错了怎么办?在等他老婆配药的空隙时间里,我听到华医生给后来看病的病人吹嘘他自己:“我系边个啊?赛华佗!保证你药到病除!”
我对他越来越反感。可我仍不死心,仔细地观察着他。病人刚好看完。他拿出一本又大又厚的中医药书,认真地看,封面上印着华佗。
我决定试试他的底细,就无话找话说:“华医生,您喜欢看中医书吗?”
“我本来就是中医嘛!”
“看起来您的中医医术一定不错!”
“那是,”他笑着说,“你知道我系边个吗?”
我好奇地问:“您是?”
“我系赛华佗!”
我对他是真无语了。但是,不觉又多观察了他几眼。微胖的宽脸膛,大眼睛极有神,嘴唇上一撇短胡须很显眼,怎么看也不像个稳重的医生。我心里更不安了。
他开了三天打点滴的药,不贵,才几十元。但是,打完今天的针,明天我决定不来打针了。回到厂后,我越想越觉得那华医生是个骗子。第二天,我没去打针。第三天,痛感让我咬咬牙,去镇上找了家最大的正规医院。挂号后,主治医生看也不看我的肿包,只问了一些情况,开了一张很长的药方。
我轻声问:“医生,大概需要多少钱?”
“不多,”医生平静地说,“650元。”
我一惊,我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多元呀!我试探着说:“药方能给我吗?我想去外面药店买药。”
“不行!这个药方只能在本医院买药打针。”
我想了想,说:“麻烦您帮我看看肿包!看看有没有变严重,好吗?”
他犹豫了一下,只好帮我揭开癞蛤蟆膏药的牛筋纸。奇迹出现了:我的肿包已经流脓了!我知道,这是康复的迹象。我掩饰住惊喜,对医生说带的钱不够,然后匆匆离开了医院。
回到宿舍,我打来一盆热水,把毛巾淋湿,对肿包一边挤压一边清洗,直到黄脓全部挤出。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来到了华医生的中医诊所。华医生一见我,很生气地说:“你总算来了!这两天怎么不来打针换药呢?”
我低声说:“不好意思,这两天忙。”
他老婆大声责备我:“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再忙也要先治好病呀!你就不怕这条腿废了?”
他们这半粤语半普通话的责备,竟让我像听到乡音般亲切。我连连点头,感激地说:“谢谢你们!”
挂上点滴后,华医生踱过来,又侃调起来:“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是我們中医之本,谢什么?”
我松了口气,连连点头。又忍不住笑着说:“华医生,您是谁啊?”
他怔了怔,疑惑地问:“我系边个?”
我满心诚恳地说:“我相信了,您真的是赛华佗!”
他听了,神情即刻肃穆起来,说:“我知道你们外来工不容易,所以,对于我有把握医治的病,我就用我是‘赛华佗来安慰你们安心医治,免得你们失去最佳医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