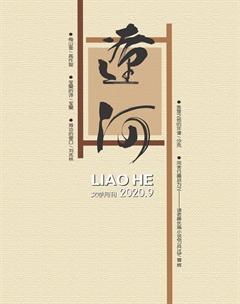我和爷爷的故事
徐鸣幽
小时候,我印象中一直和爷爷住,直到上初中才离开那个温馨而又略显寒酸的家。
之所以总和爷爷住,是因为我家孩子多,爸妈照顾不过来,加之奶奶去世早,我长得虎头虎脑,很招人喜爱,又是大孙子,爷爷也乐意带着我。
爷爷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在生产队的时候,爷爷赶牛犁地、耙地、收割、打场、栽树、种菜、捻麻绳、脱坯盖房,样样没有他不会干的。
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在爷爷的带领下完成的。那时我才刚刚记事,在我们村里住、经常逗我玩、给我好吃的的两个上海知青姐姐小叶和小朱要调往十多里外的水牛湖村,正是爷爷赶着生产队的牛车送她们俩去的。她们对我这个小屁孩多有不舍,非嚷着爷爷带我一起去。赶车的爷爷一言不发,只顾自己抽着旱烟袋,任我们在他后面疯。我家的小黑狗也通人气,不紧不慢地跟在车的后面,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它对朋友的心意。一路上,小叶和小朱姐姐有说有笑,跟我说着话儿,似乎很开心。但在最后离别时,她们却紧紧地抱着我掉下了眼泪,那一幕,真真切切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里,至今忘怀不了。
为了多挣工分,那时的爷爷是身兼两职的。白天,他和其他社员一样干生产队分配的各种农活儿,晚上则为生产队喂牲口,很是辛苦。听爷爷讲,家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人不得外财不发,马不吃夜草不肥。意思是喂牲口必须在夜里下功夫,要分不同时段给它们添加饲料,否则就无法保证它们膘肥体壮、就不能给生产队好好出力干活儿。所以,每天晚上爷爷都要起来好几次,给牲口添草加料。为了便于掌握牲口们的情况,同时也保护好牲口不被偷,爷爷只能睡在牲口棚内,我这个小跟屁虫自然也就沾了光,打小就开始享受免费的公房待遇了。
和爷爷一起赶集,是我最乐意做的事情。爷爷每年都会养十多只老母鸡,这些母鸡的职责则是下蛋。这可是爷爷顶顶稀罕的宝贝,它们平均一天能让爷爷收获十余枚蛋,除了每天煮两枚拌蒜泥当菜吃或蒸鸡蛋羹改善一下伙食,爷爷平均一周时间还可以剩下大约五十枚鸡蛋用来卖钱。那时候我们农村的大集是每逢农历单、双日子在不同的乡镇开放,如小李集、插花镇初一,那程湖集和冉庙街则是初二开。这样我和爷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单、双日子到不同的集市去卖鸡蛋。这些鸡蛋主要是卖给要去送中媒的人家,那时的农村人很少有人会买了自己吃。送中媒是我们家乡的一种习俗,女孩出嫁后生了孩子,作为娘家人,在孩子满月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这些亲戚就会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买一筐鸡蛋和一挂猪心肺,自己家再请人炸些油条串起来,一并送给生孩子的出嫁女孩,以显示娘家的人大方和熱情。正是因为总有这些热情又大方的娘家人在,我和爷爷的鸡蛋总也不愁卖。那时候卖鸡蛋是论个的,稍小些的七八分钱一个,稍大些的或红皮的则要贵上一两分钱。买的人和卖的人总是会讲价,只要差不多,爷爷就会痛快出手,拿了钱立刻带我去“潇洒”一番。先是给我买块熟的猪头肉,或是香瓜、菜瓜、麻花、凉粉、烧饼等好吃的,然后再给自己买上一小捆差不多的烟叶。等这些都完成,爷爷又会带我去一个更为热闹的地方——书场。说书的人口若悬河,似乎无所不知,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前五百年、后五百月,在说书人那里就如口吐莲花、呼风唤雨。在那里,我知道了黑老包、刘罗锅、秦琼、罗成、七剑三侠十五义、夏候老剑客、五鼠闹东京、打登州、破孟州、倒反延安等等一干人和诸多事,眼界顿开。
生产队的时候,我家日子过得很清苦。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到两年的功夫,立马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化,不仅能吃饱了,更吃得好了,白面馍可以天天吃,顿顿还有菜。第三年,我们家还盖起了五间大瓦房,把爷爷激动得不得了,割肉、打酒、杀鸡,十多个菜的席面硬是连吃了两天、又连请了两场露天电影。不光亲戚朋友,我们村最大的官——大队书记都亲自参加,爷爷真是有面子!喝酒时爷爷特意让我坐在他旁边,开始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他的酒场秘诀。自打得了爷爷的真传后,我这些年在酒场上还真的少有败绩。
爷爷是侍弄土地的好把式,更是一个慈祥的长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小时候都爱吃瓜,总买着吃钱花不起,爷爷就想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自己种,爷爷每年都会刻意留出一亩来地用来种瓜。春天开始下种,到小麦黄黄的时候就可以吃到瓜了。为了让我们尽可量多吃几天,一直等到秋凉时,爷爷才肯将瓜地拉秧。爷爷种的瓜品种很多,有西瓜、小瓜,小瓜又分香瓜和菜瓜。菜瓜打小就能吃,而香瓜必须要熟了以后才能吃,否则会苦得不行。菜瓜基本是酥瓜和艮瓜两种,香瓜里有十道青、十道黄、面瓜等十余个品种,味道各有千秋。我家的瓜除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随便吃以外,我的那些儿时玩伴们也能享受同等待遇,敞开肚皮吃,管够。其实,那些瓜自家人和朋友们是吃不了的,爷爷每年还能额外卖些钱来补贴家用。儿时的夏天,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一转眼,爷爷离世已经有三十五年的光景了,我离开家乡也已整整三十年。每每回老家,我都会给爷爷上坟,给爷爷磕几个头。那时,爷爷的形象又会在我脑海中一次次鲜活起来,永远是那般和蔼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