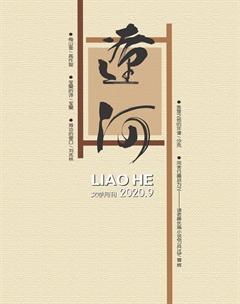四两命
万重山
不知道从哪个朝代起,闽南人把命运当作一种东西,一种可以以斤两称的东西,称出来的结果是四两命最“OK”。本地话:“人有千斤力,不值四两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一个人纵然有浑身本事,也比不过四两命好。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三两或七两八两?我查啊查,据说,就是一种“称命法”称出来的,其余无从考证。我吃饱了饭撑着,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啊找,希望与一个四两命的人不期而遇,我倒要看看这种人究竟长得啥样?是不是像刘备那样有着双耳垂肩、双手过膝般的异相?
有一天,这样的人,居然被我撞上了……呵呵,不多不少,四两刚好。
一
认识这个“贵人”,是在一次酒宴上。
酒量好,健谈,是一回事儿。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不一样。看第一眼,就有一股冲击力,造成视觉支离破碎的冲击力。他穿天蓝色的短袖迷彩服,上面的油污和灰尘的斑迹像盔甲那般厚,袖口有两三处像被烟头烫破的细小的洞,看起来很碍眼;左边的上衣口袋里插了两支笔:一支红色的,一支黑色的。这样的着装,要是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足为奇,但现在当是一大奇观。何方神圣?我心里不解,又不好当面直问。
待众人坐定,本次聚会最大的官——县劳动局龚副科长(我们尊称他为龚科)开始一一介绍来宾,当介绍到他时,龚科说,你们猜猜看,这位是干什么的?我心中猜测,可能是村干部,文书一类的吧。但看到他印堂宽大圆润,有一层油腻的反光,转念一想,这种职业,会不会折煞他?当今天下,大隐小隐颇多,藏龙卧虎,不可造次。
龚科见众人有说是教师的——经常批改作业,有说是财会人员的——账来账往,还有说是市管人员的——管市场的……都在他胸前的那两支笔上作文章。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瞄了他那魁梧的体态,突然举手喊道,杀猪的!红笔一勾——杀!黑笔一挑——过!大伙儿哄然大笑。
龚科叫他站起身,他便把椅子拉开,就地后退一步,挺胸收腹,“啪”地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大门保安一级的军礼,目光炯炯地向我们巡视了一周。大家看到他这种架势,都有点受宠若惊,掌声噼噼啪啪像打雷般响起。
龚科笑得嘴巴咧到了耳边,拍着他的肩膀,叫他坐下。这位是我以前的同事——安塘乡政府办公室的老黄……哦,明白了,比我猜的高了一个级别——人家是公社干部,管着村里呢。
酒,是润滑剂;酒,是话匣子。你看,几杯酒下肚之后,原本陌生的变得熟络了,原本木讷的变得活跃了。大伙儿兄弟长兄弟短地吆喝开了,你敬我,我劝你,酒杯敲出了一片欢乐的交响乐。
我见他一直不动筷子,光喝酒,不吃菜,有人敬他,喝;没人敬他,他自个儿喝。起初,我以为人家刚上桌有这个习惯,就像拳击赛之前的热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动作。但喝了半天,他还是老样子。我忍不住劝道,老黄,您能不能吃点菜、喝点汤?我的话还没说完,他伸出大手一挡,把我的话堵在喉咙口,瞬间又自个儿灌下一杯。
他喝酒从来不吃饭喝汤的,有时就几粒花生仁可以干两瓶“米酒头”。龚科插话道。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说,他难不成是一位穿着长衫喝酒的人?
不,他没有长衫可穿,他是穿着褪色迷彩服喝酒的人。
我不是孔乙己,我是老黄,笔名老君。他以为笔名一出口立马会赢得满堂崇拜的尖哨声,至少该有一两次稀疏的鼓掌,但对不起——真没有。他的话犹如一声响屁瞬间就被喧嚣湮灭了。他有点意外,想必整桌都是俗人。此时,酒桌上的气氛刚好,发言权基本上是你一言我一语平分的,但随着这家伙的神喝猛灌,整桌的发言权开始倾斜。他逐渐夺取了主动权,他的声音又大,有嗡嗡的回响,弄得我的耳鼓很受伤。
我给您们讲……他突然大吼这么一句,大伙儿顿时静下来,听他讲什么。我给您们讲,我如果在京城继续待下去,今日你们不可能跟我坐在一起,更别提喝什么酒了。大家愣怔了一会儿,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变故,竟然沦落到与我们这些草根同喝小酒的地步。他放开嗓子说,八几年,我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五台山采访,就是那个康熙小皇帝当和尚的地方……(哦,请原谅,他可能八成醉了,其实那个传说是指康熙他爹)……有一个得道高僧给我算了一卦。大家眼露好奇。说你怎么啦?讲来听听。那高僧说啊,我这个人四两命,一生“若无登坛拜相,便是民间贵人”。
太好啦,太好啦!可把您盼到了。我心中窃喜,终于撞到了一个——四两命,且如此零距离地承接他的唾沫感受他的能量场。我万分激动,左瞧右瞧,发现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刘备啊。
二
他說差一点儿“登坛拜相”,这我理解,自古以来这种人上人的职数毕竟有限,而觊觎这个位置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与“四两命”相匹配的则是他的滔滔不绝,一开始我几乎要献上膝盖:四两命的人,真的就是不同凡响——拜相不成,自然过渡成了贵人。
他说与一个副省部级领导关系如何铁,那领导还赠他一幅墨宝:“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为此,他把两个孪生儿子一个名永日一个名流年;他的某发小是上市公司老总;他的某结拜兄弟是中将……从他的嘴中一连蹦出十几二十几个大人物,令我这种井底之蛙,脑洞大开。
此人不可小觑!不容轻薄!在座的多数人像我一样开始正襟危坐,堆起满脸的谀笑和恭敬。他的朋友、他的见识、他的能量我辈岂能望其项背?他又呱呱呱讲起了一大串跟他交往过密的名人,他们的活动轨迹、绯闻轶事,我们的认知瞬间被提升到上流社会的高度了。但他的话实在太多了,霸占发言权的时间也太长了,座中有人跳出来开始发泄不满,说,人的一生,关键不在于你认识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仿佛被点中了穴位,他唾沫横飞的嘴巴未能闭下来,端着酒杯的手也僵住了。有那么几分钟时间,一直保持着这种下不来台的造型。
接下去的形势急转直下,对他很不利,也对“四两命”造成了负面影响。
龚科站起来压了压他的肩膀,说,我们黄协君……
什么?什么“皇协军”?这个名词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现过,指那些协助日本人的汉奸武装人员。这个时候再出现,多少有些媚日和搞笑的成分。众人不解,纷纷问道。
巧合而已,他姓黄,草头黄,不是皇帝的皇,名协君,不是军人的军,是君子的君。他的工作是临时——的。“的”音被龚科拉长了四五秒钟。他是社办人员。说白了,他是农民,是乡政府办公室聘请的写材料的临时工……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不可能吧,瞧这仁兄有那么多条天线,还啥的——临时工?
我在安塘乡待过,骗你们干什么?
那他说在北京某报社工作是咋回事?
那是实习,也不是正式的,也是临时的。
仿佛上当受骗一般,有人低低骂了一句,为了刚才白白浪费的表情而忿忿不平。
龚科见他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便放下酒杯,站着把话说完。他的命确实好啊,不多不少就四两!他前半生靠老爸,后半生靠老婆……
怎么回事?一个大老爷们还靠女人?
他老爹把他拉扯大,培养他读完大学,又掏出棺材本帮他盖了一座毛坯房,给他娶了媳妇。成家后则全靠他老婆养家糊口。噢,对了,在座的可能不认识我那弟妹,她姓连,名招惠。年纪嘛,也就三十出头,比协君少十二岁,两人同属羊,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既很会赚钱,又有贵妃之貌,一顾倾全村,再顾倾全镇……哇塞哇塞……老牛吃嫩草啊……龚科还没说完,座中开始有人蠢蠢欲动,掩不住羡慕嫉妒恨的神色。
最后龚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呀,讲得唧唧响,但实际“无半撇”。意思是半撇都写不来了,还能干什么?
这家伙被揭了老底,脸上挂不住,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在那里。树大招风,言多必失,他为刚才的夸夸其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伟大光辉的形象一下子跌落云端,他的“四两命”马上变得一文不值。与他低层窘迫的处境相比,大伙儿眼光一碰,随意轻松地捡回了满满的自信和幸福感。刚才大伙儿是仰望他的,现在变成俯瞰了,开始轮番抨击他,同情、揶揄、讽刺、打击,伴随着啧啧声,劈头盖脸地向他泼去。
还住毛坯房啊?怎么住?天啊……
他老婆太好了,有贵妃之貌是吧?又会赚钱养家是吧?不知道赚的是什么钱?哈哈哈!
大家纷纷放下酒杯,酒,不喝了。他成了酒桌的中心、主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与他结伴而来的同事童民勇突然插了几句,就像在他奄奄一息的当口又捅了他致命的一刀。协君师(我们这边称某人为“师”,多半有戏谑、轻蔑的成分。) 很是节俭,缺衣少食的。他常年都穿迷彩服,你们看,这件的领口都破成这样了。民勇走到他身后,把他的衣领翻给我们看——后脑勺下的脖颈部分因经常摩擦已破烂如絮。民勇又俯身到他座位下脱下他的一只皮鞋,高举在我们面前,你们再看看,他穿的皮鞋都像啥样了?像生癣似的脱皮了!
啊?真的假的?拿过来我看看……大家好像击鼓传花一般挨个儿递着看。包厢里面静了下来,一阵沉默之后,个个摇头叹息,个个一脸凝重,继而又是惊叹、感叹、喟叹,之后一堆批评、怜悯之词又铺天盖地地砸向他。
龚科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说,这样吧,我在市区有一套房子租给八九个大学生,他们这几天毕业回去了,扔下了几床被子和一大堆衣服。你如果不嫌弃,可以挑几件回去。龚科又扯了扯协君师的迷彩服说,我敢保证,那里的每一件都比你身上这件好。
三
黄协君死活不肯跟我上车。我说,龚科叫我来载你,他特地从县城赶到市区去等候了,说好的,你不能失信呀。
不去,不去!我死劲儿地拽他的胳膊,但他的双手像鹰爪般紧紧地抓住门框。他家的门框是木制的,门框和墙的衔接处临时用碎石头塞紧固定,缝隙可以插入手指头。我担心,再一用力门框会被顺带拔出来“哐啷”落地的,只得作罢。
我气喘吁吁地用手机跟龚科报告了这边的变故,他大发雷霆,大有扶不起阿斗的痛惜。我还不死心,企图动用龚科的权威,再压压他或许会使他态度软下来。我说,要不我叫他听听,您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吧。龚科大吼一声,几乎把我的耳膜震裂了。做个屁,死憨啊!手机随即就掐断了,进入“嘟嘟嘟”的忙音。
我感到很没面子,龚科好像连我这个经办人员也骂上了。
那次,我在他家坐了很长时间。我高度怀疑他的四两命要么掺水分要么造假。
他的家,是二层的楼房,但内外墙都没粉刷,地板也没有铺砖,仅用泥沙夯实,属典型的“裸房”。依他家的经济状况,估计能建到毛坯房,已是“力尾”(家里的积蓄已花光了,甚至还要举债)。
我们这边待客之道,就是泡茶。他踮起脚尖,从裸露的砖头墙壁上钉着的几个铁钉挂件中解下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是散装的带梗的茶叶。他边跟我谈话,边双手熟练地摘着茶梗,不一会儿就择了一泡茶葉。茶桌,是没有的。哦,他将一张支开的“三合板”桌子上面的碗筷扫到一边,腾出一小片空间,权当茶桌了。尔后又从墙角边的地上端起茶具,我看到那上面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污垢,我的茶欲被吓跑了。桌子周围环绕几张木制椅子,他拉出一张,我的重量压下去,有嘎吱的抗议声,使我不敢乱动。他说,椅子是民勇搬家时转送的。
四
一来二去的,我和黄协君就成了好朋友。
他颠覆了我对四两命的认知——并非一定要大富大贵。你看他日子过得极简,却天天有烧酒伺候,还花一笔小钱自己泡制各种药酒,什么杨梅酒、橄榄酒、木瓜酒、土龙酒、野蜂酒、蛇酒……摆在他那破房子的墙角四周,充分体现出厝主有雄厚的实力进行酒资源的战略储备。这期间他文思泉涌,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布在网络上。我记得他的诗歌中有这么一句:雄鸡不唱,天也白!多么霸气啊。哪像我们这些酸文人,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这不是四两命,难道是三两八吗?
一天傍晚,我的手机响了,是龚科打来的。他说,协君师出了车祸,进了县医院。他说,我人在外地,你能不能现在就赶过去看望他。车祸?人怎么样了?我吃了一惊。具体我不清楚,龚科说,你快去看看他吧,万一他死了也有个朋友让他见上最后一面。
我一听,赶紧放下碗筷。我想,这家伙可能身无分文,便把家里大约五六千元的现金倒出来装进两个裤袋里,往医院赶。在县医院的急诊科里,他已经躺在手术床上,苍白的白炽灯下,照着他——满面血痕,一身迷彩服也已血迹斑斑。见他血人似的躺着,我一阵心酸:四两命,这下会不会真没命了?
或许是看招惠年轻漂亮,老实可欺,或许是他鳏居时间太长,相处了一段之后,这老头就不老实了,开始言语淫秽动手动脚的。她再三警告,警告无效。这栋独幢别墅占地近三亩,即使她喊破喉咙,估计也只有那条看门狗听见。那次他突然從背后抱住她,还伸手乱摸,被她接连劈了几巴掌,老头却死不放手……
后来,这老头的女儿发现老爹钱花得快,每月给他两三千元的零花钱还喊不够,追问再三,老头说丢了。怎么老丢钱?!嫌疑就落在她身上。女儿留了个心眼,抓到了把柄,骂招惠狐狸精,吸血鬼,叫她立即滚蛋。老头砸碗摔盆,说没有招惠,他活不了。还拖着瘸腿,一步一顿地“走”到三孔桥上,威胁说,不留招惠,你们等着收尸!顺,即是孝。儿女们无奈,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由他胡来。过了一段时间,老头竟然被招惠带年轻了,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上显春光,一扫原来无精打采的邋遢模样,儿女们暗暗称奇。
俗话说:鸡蛋密密也有缝。一天,与老头同一个村庄的同事卢亚尘劝协君,快叫你老婆别干那种活了。
卢亚尘以为自己一片好心等着领赏呢,没想到迎头被啐了一口唾沫:你瞎说!我老婆岂是那种贱人?!卢亚尘还没反应过来,黄协君的茶杯又砸过来了,卢亚尘来不及躲闪,终究为好管闲事付出了血的代价。
那晚,我们可怜的朋友黄协君一个人喝猛了,喝得酩酊大醉,伏在那张既当茶桌又当饭桌的“三合板”上嚎啕大哭,哭得昏天暗地,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永日、流年俩兄弟吓得够呛。
招惠踩着自行车回来时,整个村庄已经黑灯瞎火的,加上已是隆冬,风如刀片一阵一阵刮过,簌簌作响的落叶把她裹在黑幕之中。
她到门口就听到男人悲怆的哭声,这很反常。
她的胸口有点堵,却强颜欢笑把俩兄弟拉进房间,打理他们睡下,安慰道,不怕呃,你爸只是发酒疯,哭过后就好了……话未尽,她急忙别过脸,捂住嘴巴和鼻子,不让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的酸楚……
六
大约一年后,我带了几个舞文弄墨的朋友去了一趟协君家。他家已装修完毕,门是铝合金的,光鲜得照见人影。家具是红木的,餐桌也换成了旋转的。可以说,鸟枪换炮,焕然一新了。他叫了外卖,点了几盘菜招待我们,要我们喜欢喝什么药酒自己开。喝到尽兴处,他双手往两边一压,把嘈杂和喧嚷压下去了,大着嗓门说,我给您们讲……那高僧说啊,我这个人四两命,一生“若无登坛拜相,便是民间贵人”……
我哈哈大笑,因用力过猛,把眼泪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