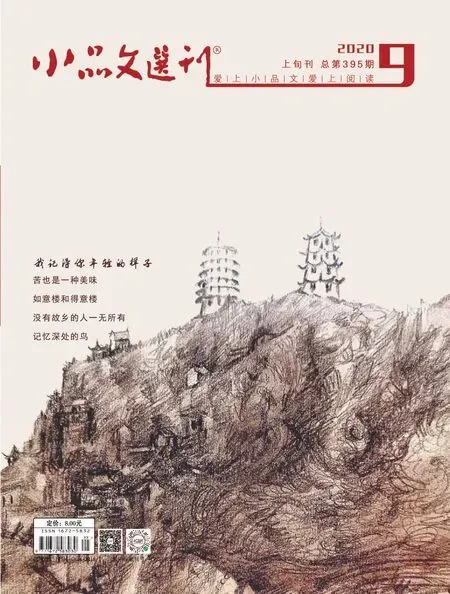遍地花香
石钟山

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我参军到边防某雷达团,后又到雷达站工作了一年。我工作的雷达站地处北部边陲,听老兵说,雷达站离边境线只有几十华里,记得从团部到雷达站时,老兵开了两天的车,起早贪黑的,才把我和满车的供给送到雷达站。
我们这个雷达站肩负着战备任务,有五六十号人,算是一个大站了。因地处偏远,周围几十里杳无人烟,平时我们休息时也没什么好去处。不知是哪个老兵在离雷达站十几里路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山沟,说是山其实就是草原上的土坡形成的褶皱。每年的七八月份这里都开满了黄花,金灿灿的一地,扯地连天的样子。这些黄花簇拥着,在不经意的风中摇摆着,发出阵阵袭人的香气。从那时开始,每到七八月份这条黄花沟便成了我们唯一的去处。从雷达站出来向东走上一个多小时,便是那条令人神往的黄花沟了。后来有人说,这些黄花可以做成黄花菜,城里的饭店一份加些肉片的黄花菜价格不菲。有好事者采了一些回来,交给炊事员去料理,不知是炊事员水平差,还是大锅菜不好炒,做出来的黄花菜味道的确不怎么样。但这时已有老兵探亲把黄花菜带回家里,品尝过,据说和饭店的味道并无二致。
也就是从那以后,有假期的老兵再去黄花沟时,便多了项采摘黄花菜的任务,士兵们相互帮忙,很快便摘了可观的一片。采好的花并不马上带走,而是摊在草地上,待一周后这些花干了,才小心地收起,仔细地留存起来。下第一场雪之后,便有老兵陆续回家休假,带走那些已经干掉的黄花,不久之后,老兵们又会带着黄花菜的故事回来。然后我们望着漫天的飞雪,等待着来年的春暖花开,还有那个关于黄花的美丽传说。
看黄花、采黄花一年只有一个季节,更多的时候,我们最好的陪伴是连队订的两份报纸,一份《人民日报》,还有一份《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 全连只有一份,放在连部办公室里,用书报夹装订起来。《解放军报》 订到班,我们宿舍就有一份。因为我们雷达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些报纸和我们的信件都是团部运送给养车捎来的,大约一月来一次。我们看到的报纸,也大抵是一个月前的了。读报纸时,明知是一个月前的,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新闻,报纸上的人和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我们班七八个人,一份《解放军报》不知在我们手里要传递多少回,也不知看了多少遍,原本坚挺的纸张已经变皱发黄,再也发不出纸的声音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这份报纸仍然是我们最好的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读着报纸上那些文章,感觉我们这里冷清孤寂,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一个角落。我们经常站在某处望着远方发呆,有时也讨论着《解放军报》所反映的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
直到一个月后,又有送给养的车来,我们已有了新的报纸,清脆的纸张声音在我们宿舍里传阅,就像一首美妙动听的音乐。有报纸相伴的日子,兵们的梦都是繁华的。记得有个新兵姓黄,正在学习新闻写作,所有的旧报纸都被他收集了,厚厚的一叠放在床下,珍宝一样地呵护着。有一天,一个老兵吸自卷的烟,卷烟纸没了,便顺手撕下报纸的一角卷烟吸了,被黄新兵发现了,两人大吵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黄新兵发那么大的火,脸红脖子粗的,差点哭出来,后来又跑到连部告了老兵一状。在晚点名时,指导员站在队列前又重申了一次报纸的重要性,还不点名地批评了那个不爱惜报纸的老兵。弄得老兵很没面子,磨叨了好一阵子。
黄新兵果然在写作上有了起色,他写了许多关于雷达站的新闻和生活趣事,陆续发表在兵种报上。他后来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兵,再后来又考上军校,毕业后又成了名新闻干事,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又经历了许多大小单位,从基层到机关,每天总会有《解放军报》 相伴,报纸都是当天出版的,散发着油墨气息,但我总想起在雷达站的那些日夜。一份报纸在兵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情景,还有那个姓黄的新兵,在夜半时分,把一张报纸放到被窝里,打着手电研究学习的情形。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再想读《解放军报》 时,打开手机,点开《解放军报》 客户端,报纸上的内容随时随地都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不知为什么,我还会想起若干年前的雷达站,孤独的时候站在某一处,眺望着远方,想象着报纸反映出的火热军营,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黄花,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便伴随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