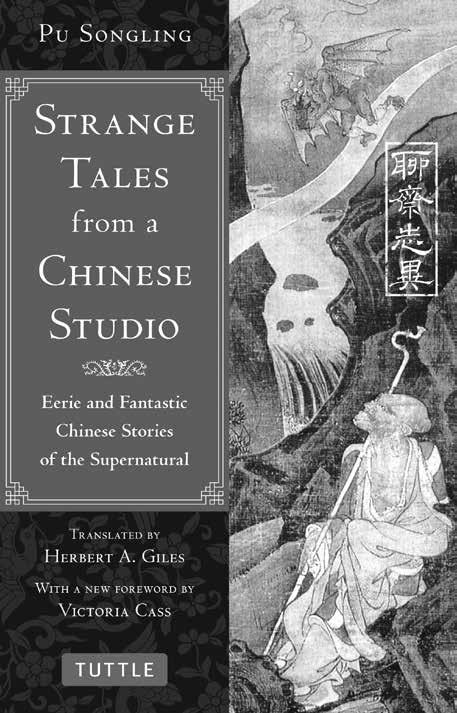卡夫卡创作的成熟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邵泽鹏

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初入小说世界,就将中国文化纳入了笔下。以其现存小说中创作最早的作品,初稿大概创作于1903年—1904年冬天的小说《一次战斗纪实》为例,这部与中国文化具有明显关联的小说,既描写了典型的东方人形象,也描写了以中国轿子以及皮影为原型的担架、黄色棉纸剪影。但此时卡夫卡涉及中国文化的描写,仅仅是摹写中国人、物的外形,直到1912年之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才真正融入卡夫卡的小说。从此,卡夫卡的中国描写也就由形似转为神似,同时,其“卡夫卡式”的小说风格也走向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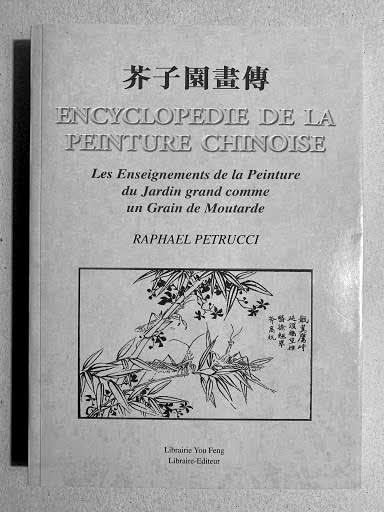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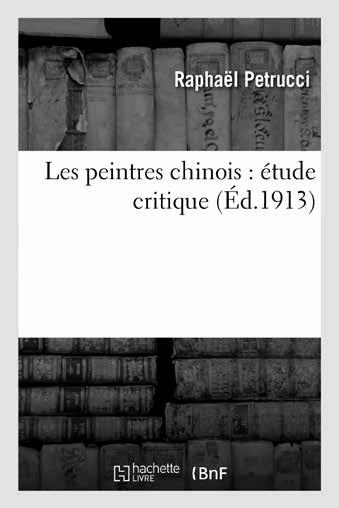
中国文化对于卡夫卡的影响在这一年从肤浅走向深刻,既是出于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1912年是一个新的起点——由封建帝国走向共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政治上的变革加速了中国文化的外传。例如,意大利汉学家佩初兹正是在这一年将《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一翻译成法文,并对其作注释评述,分三期(第1期到第3期)刊载于由法国汉学家考狄、沙畹主編的著名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第十三卷。佩初兹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引入到对《芥子园画传》的阐释中,表现出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同年,佩初兹凭借《中国绘画》(Les Peintres Chinois)一书获得儒莲奖。早期的西方汉学多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历史,在中国器物史、考据学,以及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却忽视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中国绘画》等作品的问世,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精神提供了帮助。早就在描写中国的卡夫卡直到这一阶段才真正开始领略中国文化精神并将其融入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卡夫卡而言,1912年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当年夏天,他与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同游德国魏玛。回到布拉格后,8月13日,在布罗德家,卡夫卡认识了一度成为其恋人,并与其两次订婚的菲莉斯·鲍威尔。9月15日,卡夫卡的妹妹瓦莉与人订婚。12月,布罗德与人订婚。在文学创作方面,9月22日夜到23日,卡夫卡一口气写完短篇小说《判决》。12月,他写出短篇小说名作《变形记》。这一年,卡夫卡开始筹备出版他的第一本小册子《观察》,12月10日—11日,该书的第一本样本通过邮局寄到了卡夫卡手中,接着他就将它寄给了已经成为他女朋友的菲莉斯。同年,卡夫卡还开始了长篇小说《美国》的创作……在这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还有一件事对卡夫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他从此开始深入接触中国文化。
在卡夫卡留下的书信日记中,下列时间均提到了中国:1912年7月5日、7月9日、11月24日、12月4日至5日,1913年1月13日至14日、1月16日、1月19日、3月11日至12日,1916年5月,1920年11月12日,1923年11月等,涉及中国的诗歌、小说、哲学、绘画、服饰等多个方面。
1912年7月5日,在参观过德国文豪歌德的房间后,卡夫卡于日记中提到,“歌德的房间。……有许多中国式的东西。”这是卡夫卡首次把“中国”一词写在纸上。从“中国”一词最频繁出现在卡夫卡笔下的时间段——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推断,他从无意中接触中国事物,转为有意识地记录、理解中国文化,与其1912年夏天的德国之行应该有关。首先,在参观歌德故居时,歌德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给卡夫卡留下很深的印象。其次,此时德国汉学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黄金时期,流行于德国的汉学热,感染了卡夫卡。1909年6月,汉堡殖民学院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设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其后,曾以外交官身份在中国生活13年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接受邀请,来到汉堡殖民学院,创立“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912年,《中国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1892—1910)的作者、荷兰汉学家高延在柏林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到20世纪20年代之时,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法国的欧洲汉学研究中心。此外,1912年中国政治体制的大变革,无疑进一步激发了当时德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卡夫卡在德国旅行途中,想必感受到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其后在布罗德家认识的菲莉斯,则为卡夫卡提供了一个较为完美的探讨中国文化的对象,长期工作生活在当时德国汉学研究重镇柏林的菲莉斯,也许不了解中国文化,但她对中国文化起码怀抱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否则卡夫卡也不会一直跟她谈及。

从此,一生从未到过中国的卡夫卡,对中国的了解,由茶叶、瓷器、轿子等早已进入欧洲人日常生活的中国物品,开始转向文学、哲学、艺术等更深入的层次。也即由物质文化层次的了解,转向对精神文化层次的了解。
参观过歌德房间中的中国风物品后没几天,卡夫卡就有了一个了解中国风俗的机会。在7月9日的日记中,卡夫卡这样写道:“昨天晚上有关衣服的演讲。中国女子把脚变成畸形,就为了有一个大屁股。”中国女子裹脚的习俗之所以引起卡夫卡的关注,并被他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奇风异俗满足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这也符合西方人对于东方女性“东方美”的想象——畸形的小脚、大屁股、柔弱的腰肢,依附于男性。如果说此时卡夫卡将中国写进日记,仅仅是忠实地记录下生活的点滴,或者说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观察生活,那么几个月之后,当卡夫卡再次将中国写进书信日记,就已经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较深理解。1912年11月24日,在写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提到了清朝诗人袁枚(袁子才)的《寒夜》一诗:“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在引出这首诗之前,卡夫卡特意向菲莉斯解释:“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诗,有必要说明一下富裕的中国人就寝前都用香料熏房子。”在据传为北宋诗人黄庭坚所撰的《香十德》中,这样形容香的用途: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在香的这十种品德中,能觉睡眠应当算是焚香最基本的文化属性。卡夫卡提及《寒夜》,是为了向菲莉斯证明,在世界上,包括在中国,“开夜车”都是男人的专利,以规劝菲莉斯不要再彻夜不眠地给自己写信,好好睡觉。这一点,在1912年12月4日至5日夜,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另一封信中也有提及,“与中国相反,这里是男人想夺走女友的灯。”由此可以推断,卡夫卡既了解该诗的文化韵味,应当也了解焚香可以促进睡眠这一文化属性。在这封信中,卡夫卡还提到了中国文学中的学者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对学者的讽刺和嘲讽共存。”尽管不能确定都有哪些中国文学作品让卡夫卡得出这一结论,但马丁·布贝尔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1911年),也即《聊斋志异》的德译本肯定是这些书中的一本。1913年1月16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另一封信中称,“据我所知,这些故事精妙绝伦”。

古老而又迷人的中国文化激发了卡夫卡的创作热情,丰富了卡夫卡的作品内涵。这一点,从卡夫卡受《聊斋志异》影响而创作的《变形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这一短篇小说被视为关于现代西方人异化的寓言,但其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中某些故事的相似,以及其中国化的创作手法,都说明了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产物。自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问世以来,变形一直是西方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之所以能够在卡夫卡的手中发展至顶峰,恐怕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融入。
从1912年7月到1913年3月,是卡夫卡于日记书信中提到中国的次数最多的一段时间,其文学创作也从此进入了一个较为旺盛、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关联。通过分析卡夫卡前后两个阶段的作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12年,是“卡夫卡式”创作风格真正形成的一年,也即卡夫卡创作成熟的一年,“卡夫卡式”创作风格中,蕴含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等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简而言之,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灌注,促进了卡夫卡作品独特气质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