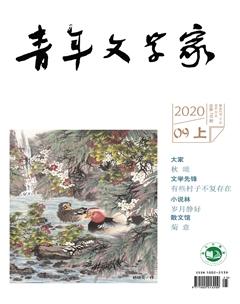弦弦掩抑声声思
张新法
龙应台说:“真正的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我想,教师亦然。
暑假过后,学校没有安排我跟班走,我教过的班级也打乱了,按成绩重新分了班。为了抢时间,八、九年级的孩子们提前开始了军训。八月的校园,像个大蒸笼,炽热的气浪把校园里的行人一扫而光。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发呆。灰白的墙壁上,一台旧空调,始终坚守,捍卫着办公室里的薄凉。状如哈巴狗的小闹钟,挥舞着一柄刀头舐血的利剑,将我原本焦灼的心一遍遍搅碎。我得看看孩子们!我拉开门,一脚迈了出去,汗水瞬间把浅蓝色衬衣裱在后背上。
这是一所农村中学,弥漫着天高皇帝远一般的清幽。三两株小叶杨像被开水焯了一下,叶片绵绵地耷拉着脑袋。我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穿过一个阒幽的读书长廊,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木屋尽头,一转弯,就能看到操场了。孩子们一袭迷彩,一个班站成一个方块,迈着矫健的步伐,呐喊着,前进着,像翻涌的稻田,更像滚动的浪涛。孔融曾在《论盛孝章书》感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我五十之年,忽焉成“目光短浅”之人,五步之遥,孩子们的脸,看似一个平面,少了些鲜艳和峻拔。我迎上前去,脑子里映出一个奇怪的画面:一望無际的田畦之上,一泓秋水映着碧绿的秧苗,悠悠地拨动着苗的茎、裸露的根须。
这个方队里一定没有我的学生,缺少豪宕之气!我把失望抛给背影,快步向宿舍走去。办公室到宿舍是没有路的,这个操场是唯一的通道。天上的阳光刺激得让我几乎睁不开眼。这时,背后传来两声嗤嗤的笑声,继而是窃窃私语。这调皮的笑声,太熟悉了!
顾盼间,我忽然发现,有一个方阵正在我前面不远处集结,我停下脚步。几十个孩子集结完毕,就向我正步走来。他们离我只有三米远的时候,领队的教官声嘶力竭地喊:“立定!全体都有,向前看,立正!一,二——老师好!”一如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这群孩子时,听到的那一声亲切地呼喊。我眼睛一酸,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我想,所谓爱,就是该放手时,还想执子之手吧。中午,我坐在办公桌前,细数着时光的碎片,一张张笑脸,被我从泪滴里捞出来……
“报告!”一个很轻的声音,把我起伏的波澜摁住。“昕!”门开处,是我原来所教班级的历史课代表,一个文静的女孩,她怯怯地站在门口,轻轻地喊了一声老师。在我面前,她本来想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却一侧身,低下了头。
我使出惯有的伎俩,说了一句老外都听不懂的外语,把她逗乐。她告诉我,想借几张报纸把寝室窗户糊上。我满口允诺,顾不上撩袍端带,翻箱倒柜寻了半天,竟然一张报纸都没找到。她一直安静地跟在我后面,看着我上蹿下跳。仿佛之前每当轮到我上课,她就会提前跑来,帮我拿教具、教材一样。
正在这时,教务处门口进来三个男生,每人抱着一沓发剩下的新书,问我放哪儿。“快放地上吧!”看他们抱着一块石头一样压弯了腰,我忙说。
他们放下书,相视对望一眼,又蹲下身去,挨着墙一本一本重新码了一遍。我站在他们身后,细细地看着孩子们,像等着春暖花开。整理好书,他们起身客客气气跟我打声招呼,昕也跟着他们一块走了。偌大的教务处,剩下孤单的我和墙角多余的书。忽然,三个男生中那个瘦高个男生,又快步转回来,走到我面前低声问:“老师,您真的不教我们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迟疑了一会,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想听您讲课……”
这时,他勇敢地盯着我,好像要从我出逃的目光里找到答案。我努力地点点头……
春去春回,再过几天,这些孩子们就要毕业了,唯愿这些与青春相遇的文字,枕着落日的惆怅,在春华秋实的尽头,与孩子们一起收获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