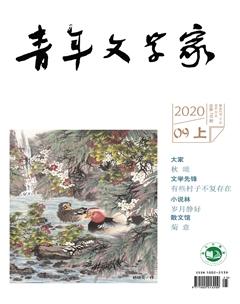人鱼未了情
禹茜茜
顺治元年,扬州城西郊长塘村有位渔翁叫昼溪,道是渔翁,实则还年轻。梦中常有一位鱼仙与他约会,他钟情于她,拒了数十桩姻缘,尚未成家,蹉跎至此。昼溪温润如玉,饱读诗书,喜清静,垂钓时,腹稿连连,一草一木皆诗情。
临行前,每每瞧见门前础石湿润了,连带青苔也更青了,昼溪便懂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道理。披上绿蓑青笠,杵在清许塘边,向他心河的鱼仙叨叨几句,随即踏上孤舟,随波逐流。一双枯手与一杆瘦竿,与鱼对诗,念起儿时故友,生了月落屋梁的情思。
故友旭曾邀他返折京城,昼溪不愿同旭一起赚来路不明的钱,即便能凭此驰骋热闹的街市,邀美人赏月,又作何如?心不安,理不得。他宁可清贫,不作浊富。
昼溪申旦达夕,与辰星共舞,同日月共处,落落穆穆,待鱼儿上钩时,他僵直的“腐身”顿时花天锦地,似一幅被泼墨挥毫的篆隶,鸾翔凤翥,颜筋柳骨。谁在书写他的人生?是青山,是碧水,也是他的村庄,他的桨声。
月下小酌,弯刀片开竹签上肥硕的鱼身,嗅着“哔剥”的串串烤鱼香,撒上雪白椒盐,滴上手工香榨油,三五孩童绕膝围坐,昼溪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南海鲛人”的传说……故事讲完了,他傻了眼,眼前仅有三五只蟾蜍,鄙夷地绕开他而已。
他清寂的背影嚼着鱼脊,用残缺的门牙撕开一缕缕白丝,好似残月之镰割开他蓑衣上一根根黄草。鱼肉怎么没那么香呢?他不禁生出疑问。被月影贪噬了么?即便渔翁睹影知竿,还是用心腹鱼钩向水下世界抛下了一串串问号。
农历九月初七,是他四十岁的生辰,他依旧独身钓鱼,良久,鱼竿沉了起来,他清寂的身影又驶向花天锦地的热闹,时而弯腰,时而跳跃,孤舟不稳,吃进了不少的水,他奋力一搏,竟钓上了一只妙龄美人鱼。人鱼美如画卷里飞身而出的鱼仙,半空中瑟瑟发抖着。
“竟是梦中人鱼!二十年了,年年幽梦此景,今梦圆生辰……”他怦然心动,更心怜,不忍让美人鱼离开清许塘,干渴而死,便用眼神,用心魂“拥紧”她,放走了她。
有太多不舍,心碎,看着波澜犹存的水面,只一个眼神,却似相识千年。
他亦清醒:他爱的并非垂钓,而是钓走那些清寂的漫漫岁月。
昼溪不知,他上岸后,那玉软花柔的人鱼也跟上了岸,鱼尾幻作一双纤纤玉腿,莹润的瞳眸,环顾着江南清丽而迥异的世界。
她原是闽南红砖古厝老宅的大宅院中长大的大小姐,在偌大的大宅院里,鱼龙漫衍,尘世间的风云诡谲,时时考验着她的家族。她懂得,为人应玉洁松贞,而非鱼悬甘饵;似璞玉纯洁,而不可贪于甘饵,为逐利而丧生,得不偿失。
家乡人民历经了一场渔阳鼙鼓,兵灾祸乱。她想,各方各尽其能,鱼跃鸢飞,不甚好吗?
她生得沉鱼落雁,被敌方将领垂涎,为了能让她幸免于难,母亲给她服下了高人赐予的药方,喝完可幻作人鱼,潜海游向他乡,自此隐匿人间。她依稀记得,母亲在亡刀祸临前,给了她一个新的名字:鸳洛。
此刻,鸳洛倚在昼溪的闲庭院落里,看着晾晒整齐的鱼干,一帖帖玉佩琼琚的诗文,一曲曲玉人吹箫的传奇,音画歌诗,抚慰疗养着她困顿的心灵,让她淡忘喋血屠刀,有了重生的勇气。
昼溪拿着玉箫走出屋门,撞见了倚门听曲的鸳洛,他们四目相交。眼前這位吹气如兰,隽永清丽的女子,从梦画中一笔一墨涓涓淌出,陌生而熟悉,剪秋双瞳里只剩下安宁、舒适,无欲无求的岁月静好。
鸳洛惊惶地退却两步,逃出仿佛要锁住她的眼神,转而望向庭外的鱼干,怯道:“你,你会吃我吗?”
风过,月落,一簇蒲公英不经意地贴到她粉面上,一种花瓣落雪的温柔,寄住他的心涧。昼溪不守君子之道,贴面轻吹过去,望着飞远的蒲公英,附耳接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