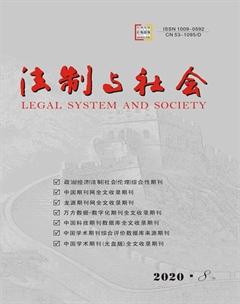离婚诉讼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之探究
关键词 判不离冷静期 财产保全效力 法律疏漏
作者简介:谢冰,福建至圣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8.177
离婚诉讼难免或多或少出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共有财产的分割争执,而那些受不了夫妻感情业已破裂,又有不能掌控夫妻共有财产煎熬的原告,一般都会进行财产保全。可实践中对第一次起诉离婚,只要被告不同意,有的法院便会以不符合《婚姻法》法定离婚条件为由,驳回原告离婚请求,给双方一次可能和好机会。缘此独特的判不离,原告若欲再诉离婚,那依《民事诉讼法》规定,则需六个月(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则需一年)的冷静期间隔。但对此冷静期所涉财产保全裁定效力是继续有效还是应然失效的评价,往往关联着当事人重大的现实财产利益与安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既缺失法律上针对性的明文规范,亦缺乏切实有力的救济典范,以致形成一个实务处理中似是而非的疑难症结。基于此,本文从民事诉讼维度,探究否定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之谬误,显然具有积极促进司法公正的现实意义。
一、终局终审既判是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评价的前提
司法本身职责要求任何司法作为,都要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相适应,具体到离婚诉讼判不离情况,不言而喻极其特殊,那对其财产保全效力的认定也要相应特殊,方为两端持平,即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评价,司法应当且必须关顾到这一不是当事人意愿,而是司法强制干预不离的特殊中止属性的特殊情况,鉴此对其财产保全效力倘若否定延续,那可能造成将来案件终局既判执行不能的危险,实际上根本无法排除。因此,在针对性明文依据疏漏且现实认知争议莫衷一是的朦胧之中,厘清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评估的前提是终局终审既判之法律常识,势必有益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延续与否的释疑解惑。
1.众所周知,财产保全为强制执行服务,实施执行的前提是裁判生效,裁判生效的前提是既判力有效,而既判力则始于法院确定终局判决所判断的当事人之间诉争事实状态或权利状态存在的特定时点[1]。换言之,终局终审、财产保全效力、未来执行, 三者关联密切,未来执行是财产保全效力的上层建筑,终局终审是财产保全效力的评价基础。可研究判不离,仅涉夫妻感情方面暂时搁置,并无夫妻共同财产事宜。也就说,离婚诉讼三环节之一的共同财产已经法律保全,且在保全裁定的有效期限之内,作为实体的纠纷最终如何裁判、财产保全目的能否实现,均属尚未确定状态,缘此终局终审的前提条件客观欠缺, 那无论在实务中,还是法律上,都推不出判不离生效而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必然终结的结论。
2.判断是否终局终审,法律上是通过“一事不再理”原则加以检查、鉴别,若能再诉,那就不是终局终审。照此标准不难看到《民事诉讼法》项下裁判,并非全部都是终局终审,如判不离式的离婚诉求单项驳回,与案结审终的诉求驳回,尽管有着相似的既判力,但相似不是相等,前者结案并未终局了结诉讼事项,仍是非常独特的临时过渡属性,后者则系普通的实质性终局,两者裁判之异质不言自明。为此,混淆且只抓住裁判生效既判力一点,而忽视具体裁判中存在特殊与普通的划分,终局终审与非终局终审的差异,就显然偏颇。
3.判不离所衍生出的冷静期,乃诉讼操作层面上的一项特别程序安排,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认知其既判之所以属性离婚诉讼中止的关键:
其一,特殊性,为法律强行干预,暂时冻结原告诉权行使的特定期限,是民事诉讼暂停特定时间以观后效的中止机制。
其二,过渡性,系等待解冻诉权的过渡阶段,并非案件终局审结。
其三,法定性,是种特事特办产物,保留原告再诉权利,赋予“一事不再理”法则适用的例外。
4.财产保全的重大作用就是控制保全的财产,以利案件执行。可判不离的显著特点一如前述,仅为离婚暂停,在冷静期中诉讼纠纷实际尚未达到终局终审裁判程度,那案件何来执行与否的明确?既然执行如何尚属待定,那又何来财产保全效力却因此先予法定解除的道理?
5.基于判不离尚未案结事了,致其既判之本质并非终止,因此,终局终审驳回诉讼请求的既判生效规则与其明显不相适宜,故以判不离式驳回离婚诉求生效视同已经事了案结,强推财产保全解除,无疑在把财产保全引向一个没有执行未来的歧路,这不但令离婚诉讼的财产保全价值与意义顿失,并且重创婚姻财产诉讼体系。
简言之,终局终审是财产保全效力评价的基石,而判不离案件的既判力欠缺终局终审的前提性配置,那就明显谈不到财产保全效力法定强制解除问题。况乎,一审期限法定六个月或再延长六个月,仍有可能时间上短于财产保全持续期间,此特色已然揭示财产保全效力在裁定期限届满或终局终结既判生效前可以独立生存,也即财产保全期限的完整形态的客观论述,就是既可依附于审判程序而跟审判的终局终审重叠,又可脱离审判期间且独自渡过申请执行期限空隙,跟执行程序融合完成财产执行使命。对此考评,倘若无感或无视,那势必形成冷静期离婚诉求只是冻结中止,而财产保全效力却被法律半途强制终结的闹剧。
二、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延续具有应然的正当性
由原告立场而言,对冷静期设置的直接定位,就是在诉讼特定时间里进行一次拯救婚姻家庭的试验,而非排斥离婚财产保全的效力。故追逐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就是希望离婚避免“人财两失”,将来被告倘若耍赖或拖延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义务,可以透过强制执行,兑现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再者,离婚纠纷财产保全所调整的是一种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关系,判不离只是审理上的一个逗号并不是句号,即案悬半空而实体未曾裁判的冷静期,虽有既判之名,但不存在生效裁判权益的实现能够通过其他方式给予保障或不再面临损害风险,进而失去继续保全意义的情形,那诉讼保全之防止财产损害任务就并未达成,那保全效力应然接续到法定保全期限届满为止的解读,就更好地排除了保全财产可能会被被告单方变动与处分的忧患与现实威胁,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
由被告立场而言,在诉讼博弈中趋利避害,乘机逃废或减少财产分割,也属人之常情。况且驳回离婚诉求判决既然生效,那其财产保全就失去案件的依存,保全措施自然就要解除。此论似是而非,主要缺陷有三。第一,于审理期限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财产保全效力管治的时间不会少于审理期限加上执行申请期限的总和,而且互相并無缠绕或必须无缝对接问题,也即财产保全与审理裁判之间的期限长短不一,其中尽管存在一些时段上交集,但相互关系特殊——既关联又分立。故仅简单地以判不离生效时点为界,机械作为划定财产保全效力截止终点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第二,于终裁标准上。审理裁判结束不等于财产保全结束,将法律设计婚姻纠纷冷静期的良苦用心视同终局终审裁判,犯了未把“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判断结案与否的基准标尺之错误,如此自然衍生审理中止与终止一刀切的荒谬;第三,于再诉权利上。倘若支持判不离属性就是终裁审结,那原告便不可逆地被排斥再诉,但事实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七项明确规定冷静期时间届满,原告享有再诉权利。这样岂不自相矛盾?
再者,对标实务,支撑案件“驳回诉求,终局审结,财产保全当然终结”的套路,机械使用于名了实未了的判不离案件之流行理由有二:第一,冷静期届满再诉,其案号是新的,不是原审案号,那就属于另一案件,所以既然案件判不离生效,那财产保全就应当解除。这乍听蛮有理,可窥究其实质与莫须有类似,因为二审被发回重审并不少见,那案号也不相同,难道据此也能成其财产保全解除的依据?第二,冷静期解保后,尽管被告对保全对象之财产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等擅变处分,屡见不鲜,但在法律上并不会缘此抹杀其夫妻共有财产属性和单方处分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在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理论上,仍可事后追偿救济。不过瑕疵就是理论与实际不相适应,即从实务上,常常好端端归属夫妻共有的财产实体消失,剩下一纸判决之教训,已经充分佐证其不仅诉累且增加难度。足见,否定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自然延续合理且应当的思维,十分苍白无力。
诚然,现实里不可否认冷静期中夫妻,有的就此琴瑟合鸣,但更多却因此更加仇雎郁闷,互信匮乏愈发严重,基此如若保全效力半途废止,那其讼争财产岂不失去切实保障?再者,原告作为夫妻共有财产人,相较而言就是财产权益的危机方,同时,被告往往掌握财产主导权,擅自处分财产,逃避分割的动机相对强烈,而这倘不予以遏制,定然增大将来既判财产难以实际取得可能性,且亦无端増添法院执行难的数量,更实际变成了一种对原告离婚的极限施压和惩罚,成为原告的无妄之灾。为此,支持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连续,既彰法律正义又兼顾执行保险之功效。 也即在财产保全期限尚未届满,诉讼事项裁判又属性中止而非终局了结情形下,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延续的正当性不言而喻。
三、冷静期强制解除财产保全之危害
关联解除财产保全的主体,依法是原告、被告、法院,也即解除保全途径分别三种,一是原告撤回;二是被告担保下的解除;三是法院依职权干预解除。为此,通过阐述其解除保全权利行使的正常循序与利弊,便可助益审视强制解除冷静期财产保全的危害性:
1.首当其冲是对原告切实利益保护与平衡,甚至财产保全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均成一个严重纷扰与危机。其实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既是法律赋予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由当事人自己处分的体现,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法院就不得拒绝。况且,财产保全普遍是以提供赔偿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损失之担保为前置。为此,结合前述冷静期财产保全效力应然延续的正当性,作为申请人如果不申请解保,那便不宜在财产保全期限届满前给予解除,是基本法律素养。否则,案件未终结,财产保全先行解除,这岂不给被告留下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可乘之机?同时,法律对于保全解除后财产变动处分又没有允准归属新情况、新理由,可以不受冷静期限制再诉再保全而救济保障诉争财产安全,这岂不实质压制原告财产权益保护?
2.对被告来讲,解除保全的管道始终畅通,正常可在提供担保或自动履行义务下申请法院解保。因此,冷静期内除非和解,否则凡要急于解保的,既使美名考虑财产保全影响不良,那在如今找保险公司担保普遍化且保费相较不高环境下,令其釆取兼顾双方冷静期利益保护与诚信,实行提供符合“等值且有利于执行条件”的反担保下解保,应成臻为适当与合理化解危害的举措。再择取被告财产处置过错的防患与救济之客观成效差强人意的角度,考证反担保下解保,也是一个双赢与解决双方利益争夺困境的最实在、最有效办法。否则,无担保任意解除保全,不仅明显庇护被告,而且令财产保全申请变成无用之功,那岂不损害司法公正与信赖?
3.法院强制解保形式分为依被告要求或行使公权二种,且此间具体操作并无明文规范,争议尖锐,现在纵然对之搁置争议,转而正向分析其积极干预,也难以逃脱越界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嫌疑。因为,强制保全解除依法是建立在案件终局终审基石之上的,而判不离乃系未经审理终局,所保全财产权属未经明确,且客观不能排除保全解除后爆发损害夫妻共有财产的可能。缘此,若是被告申请解保,那在司法尚未建构解保这一重要诉讼活动的听证机制下,为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那在冷静期特殊性下,至少应该听取原告对解保的意见。若原告明确反对且无放弃再诉权利表示,而被告又坚持解除财保,那从操作层面,就诚如前述需要被告提供反担保条件之下方予解保,这样的谨慎、折中,对双方争执利益的保护,无疑均会趋于理性与无害,不然,恐会导致剥夺或边缘化原告权益保障的弊端。换言之,在过错损害责任由申请保全方承担无虞下,法院解保活动,理应恪守中立,奉行不告不理,只有当事人申请之后,才能出手审查解保的正当性、必要性,也即在保全无错,原告无撤回保全申请下,法院于冷静期中主动解保或否认财产保全效力,完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和必要,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