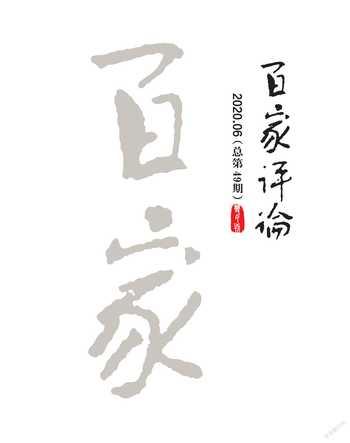改革开放时代的女性生命史与姐妹情深
蒋建梅
内容提要:《你的姓名》是旧海棠为姐姐写的“史诗”。在姐姐离世十多年后,旧海棠以“哀而不伤”的文风,呈现了姐姐30岁的生命史以及痛失姐姐后的无尽哀思,再现了民间传统习俗信仰与现代观念碰撞冲突下姐姐多重身份的裂隙与破碎感,凸现了血缘姐妹互爱互助、从乡村走向城市经历的精神成长。小说的女性身份困境与血缘姐妹情感书写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旧海棠 《你的姓名》 女性身份 姐妹深情
人间逆旅,寿数各有天命,聚散亦自有定数。失去亲人,生者哭天抢地;华年永别者,更令至亲痛彻心扉。文心玲珑者,往往将情深付诸文字,长歌当哭以慰哀恸。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里有两首悼念逝去亲人的诗,一为悼念父母,为清人方玉润称为“千古孝思绝作”的《诗经·小雅·蓼莪》,抒發“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憾痛之情,二为悼念亡妻(主题有争议,此处取其一)的《诗经·邶风·绿衣》,写物是人非的痛失之情。生死离别在人间永不落幕,孝思与悼亡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绵延成文学大观。除此两类最瞩目的痛失悼念之外,也有悼念其他亲属的感人佳作,如韩愈悼念侄儿十二郎、苏轼悼念堂妹小二娘的祭文均感人至深。在两千多年里的各类悼念文章中,因手足情深被同辈悼念的文章,颇为罕见,以致于苏轼悼念堂妹的深情被林语堂理解为痛惜难忘的“初恋”。在女性写作不太可见的古代社会,女性常因母亲和妻子身份被悼念。女性悼念亡姐的深情文字,几乎未见。在戴锦华所言的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女性主体视角下的姐妹深情书写成为了可能,旧海棠在姐姐于2007年故去之后,为纪念姐姐曾写过动人的组诗《给你的信》,因为诗歌容量有限不能呈现太多生活细节,时机成熟时,旧海棠遂将姐姐一生中重要的细节呈现于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你的姓名》①。
《你的姓名》描绘了镶嵌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乡村与城市文明冲突共生中一位70后女性30年的生命史,呈现了一对70后乡村姐妹的互爱互助、立足城市走向成长的手足情深的生命经验。可以说,《你的姓名》是旧海棠为亡姐写的一部史诗。“史诗”本指口传文学时代讲述人类童年时期的神话传说,或人类重大事件的叙事长诗。在现代印刷媒介发达后,“史诗”文体逐渐消失,用诗意的方式表达历史变迁中的精神图景与族群或个体命运的“史诗性”成为集体文化记忆与美学追求。旧海棠自言:“《你的姓名》起初是按非虚构来写的,主要想写姐姐从出生到病逝,写到七万字时,觉得处理不了现实中的一些关系,后来改成了小说,随之纳入了更多的人物和更长的时空进来,这就是现在这个小说版本的《你的姓名》。但不管是非虚构还是小说,都是我由纪念姐姐而起并献给姐姐的一部文学作品。”②因为和姐姐有过很多相处,所以失去之痛就特别深沉:“人与人的情感建立来自付出与交往。交往得越多,记住的情节越多,回忆也越多,回忆多了自然想念。”③“我”用对姐姐的回忆与念想建构了姐姐的生命史、姐妹情深,凸显了女性写作对于女性身份思考、女性情感展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一、传统与现代观念碰撞时代姐姐的身份困境
从乡村到城市的女性作家对身份认同似乎都比较敏感。70后女作家盛可以擅长书写乡村出身的底层女性在城市的残酷生存中遭遇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困惑。④同为深圳作家的旧海棠《你的姓名》延续了女性身份困惑主题,她敏感地意识到了姐姐从生到死都一直伴随着“寄居者”的身份。姐姐于1977年出生于大王庄,父亲在改革开放后带着她回到父亲的出生地、祖籍所在地大张庄承包田地,就现代法律而言,姐姐无疑是大张庄的合法人口,但就传统民俗而言,她是随父亲在大张庄继爷爷门户里出生的孩子,于张庄而言是夹杂外来身份的寄居者。姐姐从小就知道自己“寄居者”的尴尬身份,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姐姐童年时期就敏感地懂得“她要很懂事才行,要给爸爸妈妈挣面子。”故姐姐特别自律,勤快熟练地操持家务、照管弟弟和“我”,努力学习,力争出人头地。
在遇到爱情之后,姐姐违背了父亲对自己学医以后回馈家庭的设想与期望,因为对从医不合适也并不热爱,姐姐放弃了珠海体制内的医护人员身份,带着姐夫写给她的情书从珠海出走到了深圳,姐姐随姐夫作为外来者寄居在深圳郊区,“赋闲”在出租屋里的小家三年,此时从事没有薪水的家务劳动的姐姐在父亲看来,没有获得送她读书的父母期望的、现代教育赋予女性的社会职业和经济独立,具有双重寄居意味。姐姐终究对自己现代意义的长女责任有承担意识,于2003年开始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勤勉创业。少有资本积累以后,姐姐和姐夫趁产业转移觅得商机到苏州创办公司。不巧天命有违,公司刚有起色,姐姐产前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花费巨大,家庭财政遭遇重大危机,会变通的姐夫利用媒体的力量,以姐姐的“寄居者”身份为基础争取社会慈善力量的经济援助,“打工者”、“白血病患者”、“勇敢的母亲”等身份标签,让姐姐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捐助、同情与敬佩,姐夫几乎掏干家底陪姐姐去北京治疗,还得到热肠的北京人“洪大哥”在网络论坛发起的援助。为了能康复承担起自己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责任,姐姐承受了治疗时各种难忍的苦痛,终因医学无力回天憾然离世。网友洪大哥还自发组织一直关注姐姐的网友为姐姐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网络虚拟社区的力量似乎消弭了地域对人们身份的区隔与限制,姐姐在死后的“哀荣”中也似乎脱离了传统观念中男权社会的附属身份。但其实并非如此,姐姐的身份建构此时尚未结束,肉身消失后她依然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和姐姐存在,并且继续处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冲突与裂隙之中。
姐姐身份的困境暴露了这个新旧混杂的时代各种力量对于女性个体身份建构的复杂角力。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出嫁曰“归”,出嫁后女性的身份被丈夫的身份建构。姐姐安葬时,“我”们家并未脱离此传统观念,认为姐姐已经结婚并生了女儿,可依照安徽当地传统民俗葬入姐夫家的祖坟,但姐夫家族却以中间还隔着两代活人为由,拒绝了“我”家依照传统习俗的合理要求,为此两家起了争端,最后因“我”家人少又是在异乡而落败。姐姐仍葬入姐夫家族原来安排的祖坟附近的坟坑。姐姐坟墓的位置反映了生育了女儿的姐姐在传统男权社会的文化习俗信仰之下的身份尴尬,嫁入夫家的姐姐并没有得到应有之“归”,依然是一个寄居者。作者写到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老家传统的丧葬风俗与祭祀习俗已在逐渐与时俱进发生缓慢改变,但风俗信仰的改变不能突飞猛进,尚需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与现代生活方式弥合,这大概是虽已立足深圳但对于故乡的传统丧葬习俗仍然认同的作者内心为姐姐之死一直憾痛郁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姐姐的人生轨迹曾辗转多地,虽然坟墓根据传统安在夫家乡村,但姐姐的户口还留在原生家庭户口本的第三页,这是现代社会的性别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女性在社会中可自由流动从事各种职业的前提才有的现象,根据血缘关系和现代法律,姐姐作为女儿和姐姐、大张庄的合法村民的身份依然是毫无疑义的存在。故在姐姐去世后,村里面临拆迁补偿时,“我”据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依法为姐姐成功争取到补偿款。姐姐的身份权力在国家法律保障的户口簿里得到了应有的确认。但整体来看,“寄居者”姐姐的身份是令人困惑与破碎的,仍处在传统民间习俗信仰与国家法律权力的矛盾裂隙之中。
二、姐妹情深互助互爱的精神成长
70后学院派作家付秀莹《他乡》呈现了乡村出身的女性凭借教育、才华与不懈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精神成长的生命经验。翟小梨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新世纪作家书写人性以及探索和把握时代精神的叙事能力,也为当下新女性形象的成长书写和伦理观的重构做出了应答。⑤在此向度的女性写作背景下,舊海棠《你的姓名》除了写姐姐的身份困惑之外,也写出了乡村出身的姐妹如何互助互爱、走向城市、经历成长。作为当代文学批评资源的“姐妹情谊”本是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指作为男权社会的压迫者的女性互解互爱互助,“相互关心与支持”“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⑦不少文学批评者多用以阐释非血缘的女性同盟情谊,指出它的美好,亦指出它的脆弱。⑧本土已有的文学实践多表现非血缘的女性同盟情谊,表现血缘姐妹亲情的互爱互助并不多见,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姨妈姐妹。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书写血缘姐妹情深互助互爱成长的小说尚无长篇佳作。故旧海棠写就的血缘姐妹深情无疑具有展示现代社会女性情感世界某个侧面的独特文学意义。
姐姐有非常自觉的姐姐身份意识。比“我”大两岁半的姐姐自五六岁起就自觉承担了照顾“我”的任务,经常为保护弟弟和“我”挨了母亲不少气头上的打。姐姐还因心疼“我”找别人评理挨过别人的打,以致于“头皮耳朵上方有指甲盖大小的白皮字一直不长头发。”当然,“我”也不是一味被姐姐保护,“我”凭着天生的大胆和“土著身份”,在村里帮姐姐泼辣骂退那些以寄居者为名欺负姐姐者,在学校里剽悍地保护成绩好表现好、但胆小怕虫怕蛇被别人嫉妒整蛊的姐姐。“我”因成绩不好初中辍学后,在县城打工,姐姐在省城读中专,“我”去看姐姐时,非常节省的姐姐从生活费中硬挤出钱来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双皮鞋。后来16岁的“我”曾将在潮州菜园打工挣得每月200元的工资钱省下来,寄给了姐姐500元做生活费。姐姐病重需钱时,还在还房贷的“我”先后两次尽力筹钱,第二次要筹十二万,老公责怪姐夫不卖公司时,“我”一时情急却情切说出:“我们总不能不救我姐”、“我们是姐妹,他是一个外人。”“我”放下深圳家中的舒适生活,为姐姐辗转苏州、北京、安徽,甚至有一段时间还不得不把幼小的孩子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一直安慰因病要做生死未卜的剖腹产手术的姐姐、孤独住在重症室的姐姐,对姐姐说以前姐妹俩经常用以逗乐对方的“雷好啊,靓女,我好中意你嘅”,“我”借粤语“中意你”传达了对姐姐郑重如一的爱,也意味着传统文化中成长不善于直白说“爱”的姐妹,常借嬉笑的粤语传达内心对彼此的庄严深厚的血缘姐妹之爱。作者写了姐夫2009年再婚后的凉薄,也写了自己十多年里对姐姐无尽的悼念,由此印证了她在为姐姐治病时把血缘姐妹亲情置于夫妻情之上的合理性。
有主见的姐姐知道自己要什么,放弃了体制内的从医工作,为爱去了深圳,当今社会人们已意识到只承认社会职业的收入而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典型的性别偏见与歧视。但当时姐姐冒着这样的偏见压力在深圳生活了三年,后来为更好的生活以及承担家庭责任,在时机成熟时姐姐在家人的支持下两度创业,期间天生体质较弱的姐姐吃苦耐劳,很有拼劲。“我”认识到姐姐是“我”的指路人,她对于“我”的职业规划、能顺利在深圳立足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姐姐没有南下之前,到了广东的“我”一直从事底层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如在菜园打工,在酒店做服务员。姐姐在深圳立足后,她让“我”辞掉珠海的服务员工作到深圳从事与先前所学的裁缝技术相关的商场服装导购工作,奠定了“我”以后主管品牌服装市场推广事业的基础,同时她又鼓励“我”去学会计拿到了会计证。虽然“我”后来并未以此为业,但对于“我”在深圳顺利立足,甚至以后成家立业而言,这一项技能显然更增自信与底气。
姐姐去世后,她的成长其实并未结束,而是在“我”替代她的身份成长中完成了未完成的成长。在弟弟车祸事件中的追责、赔偿、就医、康复过程中,老家村里大锋家欺负“我”家势弱侵占“我”家宅基地等系列事件中,只有乡村经验不能应付城市生活、年老弱势被村里人欺负的父母只能依赖“我”,“我”不仅出力帮助父母,还屡次出头依法为家里力争各项权益。每次为家里出头时我都意识到“这应该是姐姐去处理的问题,如今落到我头上了我该怎么做”,“我”替代姐姐的长女位置为家庭担当重任,“我”在历事中成长。姐姐生前引导了“我”如何立足城市的成长;姐姐死后,“我”接替姐姐在家庭中的位置,完成了现代社会家庭中一个顶梁柱般的长女身份的成长与蜕变。“我”无比痛惜地领悟到,“我”和姐姐无论生死都是情感与精神可分不可离的血缘共同体。
三、结语
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人世无常只因天道昭然。旧海棠曾在《遇见穆先生》创作谈中说到姐姐的死:“一个人突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一件残暴的事情,她突然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了。”为了减缓这天地不仁的“残暴”带来的憾痛,用文字留下姐姐的世界,旧海棠写下这部“哀而不伤”的《你的名字》,延续了她以往小说以极其温和的方式叙述非常惨痛的事件的风格。她说,这是因为童年生活的北方平原田野天高地阔、历经世事的她已人到中年。我能理解。我写这篇评论,是因为我被《你的姓名》所感动,正如旧海棠读徐则臣散文集《到世界去》所说:“因为心灵在肉身里,外界的干预始终是外界的,所有进入心灵需得心灵的自然接受。”作为同样在时代大潮中从乡村辗转到城市里立足的70后女性,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能呼应共鸣的部分,这让我喜欢这部看似平淡却深情暗涌的小说。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女性一个前所未有的开阔世界和无数机遇,但女性的解放仍远未完成。因此,女性的不断言说具有揭示自身生存境遇、指向更好未来的重要意义。立足于文学史的维度上,我想尽力挖掘出我能理解到的、这部小说对于呈现血缘姐妹的深情、女性身份困境与女性精神成长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
注释:
①旧海棠:《你的姓名》,《〈收获〉长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夏卷,第128-279页。
②旧海棠:《〈你的姓名〉创作谈:有限的生活,无限的细节》,《收获》微信专稿,8月10日。
③旧海棠:《你的姓名》,《〈收获〉长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夏卷,第172页。
④刘涛:《青年作家研究——70后六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
⑤张丽军、刘兰慧:《新世纪“娜拉”形象的重构——论付秀莹新作〈他乡〉》,《百家评论》,2019年第6期。
⑥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 39页。
⑦冯慧敏:《王安忆〈天香〉中的姐妹情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第7期。
⑧龚自强:《姐妹情谊与男权世界的辩证——简论电影〈七月与安生〉》,《艺术评论》,2016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影视中的生育主题研究”(17YJAZH0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