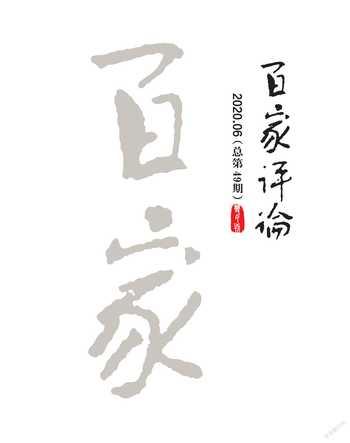叙述方式设定与隐秘精神世界透视
王春林
内容提要:读完黑孩的这一部《惠比寿花园广场》,我们即可以断言说,这部作品思想艺术方面最突出的一个成就,就是对于韩子煊这一人物形象那种现代病态人格的深度揭示。同时,我们固然在以类似于叙述者的眼光理解看待渣男韩子煊,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在以隐含作者的视角理解看待着叙述者“我”。更进一步说,那样一种与流浪猫“惠比寿”紧密相关的精神救赎情怀,也主要是通过潜在的隐含作者而充分凸显出来的。
关键词:黑孩 《惠比寿花园广场》 韩子煊 隐秘精神世界
对于从未踏足过日本土地的我来说,面对黑孩的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载《收获》杂志2019年第6期),首先关注的就是何为“惠比寿花园广场”,以及黑孩到底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一种小说命名方式。因为黑孩的这一长篇小说涉及到了诸多真实人物与地名,所以,我就去查阅百度。由百度可知:“惠比寿花园广场是集购物、餐饮、办公、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它的前身是札幌(sapporo)啤酒工厂。” 更具体来说,“除了百货商店、葡萄酒店、西点屋等购物设施以外,还有电影院、美术馆、各种餐厅和咖啡馆等,可以尽情享受。惠比寿花园广场塔的38、39层是展望餐馆街,是东京都内著名的赏夜景处。”对于这一名闻遐迩的去处,黑孩在小说中借助于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女主人公“我”也即黑孩自己(这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的叙述者“我”,到底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作家黑孩自己,其实也是饶有趣味的一个话题。一方面,从文本中所刻意营造出的若干带有明显纪实性特点的人物与细节,比如“我”与作家谢冰心、汪曾祺他们的交往历程、比如“我”曾经创作过一部名叫《父亲和他的情人》的短篇小说集、比如“我”很早就在与前夫离婚后移居日本等等这样一些情节来判断,这个“我”当是黑孩自己无疑。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小说本质上乃是一种依凭于想象和虚构的叙事文体来加以考量,那么,这位深度介入到了故事之中的“我”,却又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被看作是作家黑孩。也因此,一个合乎艺术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应该被理解为带有突出自传性意味的人物形象。然而,除了以上这一点之外,黑孩所设计采用的第一人称这种叙事方式,恐怕也还与一种小说文体现代性的悄然建构紧密相关。虽然或有不同的例外存在,但从总体上来说,第一人称“我”的登场亮相,一方面,突出地传达着现代人生存层面上精神的漂泊与孤独,另一方面,却也明显意味着强化后的个人主体拥有了单独与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外部世界隐然对峙的悍然力量,一种现代性品质的具备,乃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的眼睛做出了相应的描述:“某一个夏日,我曾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溜达过。广场上最高的大楼,仿佛是由一大片一大片蓝色的玻璃建成的。玻璃上映着好多移动着的人的影子,很容易令我错觉空气中有一股海洋的气息。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栏杆、窗框,街道的标示牌的基调,是金黄色的和墨绿色的。无所事事的我,带着空阔沉静的心情,觉得自己正走在欧洲的某一条街道上。”阅读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就不难发现,同样是那个惠比寿花园广场,与百度中没有丝毫温度可言的说明性文字相比较,小说中的文字很明显地打上了“我”的主体烙印。无论是从惠比寿花园广场的高楼玻璃联想到“一股海洋的气息”,抑或还是仿佛“正走在欧洲的某一条街道上”如此一种错觉的生成,其中主体性烙印的存在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一方面,因为惠比寿花园广场乃是日本东京一个标志性的所在,另一方面,更主要地还是因为这一场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缘故,所以,虽然只是第一次置身于惠比寿花园广场,但“我”却暗下决心:“什么时候有了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搬到惠比寿来。”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时候“我”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距能够居住在惠比寿这一地方却都还相当遥远。尽管自打离开中国移民日本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算短(根据小说中透露的若干信息来推断,“我”离开中国准备前往日本的时间应该是1991年年末与第一任丈夫大宇离婚之后不久,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二次见到了女作家冰心老人:“我告诉冰心,我刚刚离婚,有一所日本的大学欢迎我去留学,但是我还在犹豫。”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曾经有机会见到作家汪曾祺并求序。汪曾祺在序言中写到:“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由此即不难断定,“我”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是在1992年的时候。但等到作品所主要讲述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时间却已经是接近二十年之后的2010年前后了:“我跑到电视机前。电视里的播音员正在说沪昆铁路的名字。2010年5月22日下午16时42分,K859次旅客列车由上海出发开往桂林。次日凌晨2时10分,运行中的K859次旅客列车,在沪昆铁路江西省抚东市孝岗镇河坊村附近,撞上塌方土石发生脱轨事故。该事故造成乘客死亡十九人,伤十七人,其中重伤十一人。” K859次旅客列车脱轨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与韩子煊的故事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由以上分析即可推断,故事发生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基本生存状态却仍然相当糟糕。不仅仍然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且仅有的一个名叫维翔的情人,也还已经引起了他太太的强烈怀疑。那个被藏下专门领来找“我”看手相的李太太,正是“我”的情人维翔的妻子。幸亏被“我”及时警觉到,方才识破真相:“我十分警惕,知道两个女人找借口骗我来看手相,目的是为了审判我。”然而,“我”虽然因为自身的警觉躲过了一劫,但与维翔之间本就脆弱的情感联系却也更其脆弱了。萍水相逢的韩子煊,之所以能够很快地乘虚而入,应该与这种脆弱紧密相关:“维翔没到机场送我,我就觉得那个卖月饼的女人是占了我上风了。我心理上出了问题,好像一只受了伤的流浪猫,到处寻找安慰。”正因为“我”不仅情感上很受伤,而且也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那个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主动与“我”搭腔的“朝鲜族人”韩子煊方才有机会进入到“我”的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尤其不能忽視的一点是,韩子煊所亮出的居住地名正是“我”无比向往的惠比寿。当“我”询问韩子煊的居住地时,韩子煊给出的答案竟然是出乎预料的惠比寿:“韩子煊说了一个令我吃惊的地名。东京的人,都知道惠比寿是有钱人才能居住的地方。”事实上,也正是由此方才引出了“我”一番关于自己第一次造访惠比寿花园广场时的回忆。究其根本,正因为“我”一开始就对于惠比寿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所以,韩子煊那不无炫耀之意的自我表白,方才迅即引发了“我”自己一番“不怀好意”的联想:“而这个叫韩子煊的男人,好像圣诞夜醒来后枕边的一个礼物。也许我可以给维翔打电话,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会晚几天回东京,并且告诉他,我已经不需要他到机场来接我。”由此可见,在“我”与韩子煊之间绝对不能够以正常视之的一段畸形情感关系中,作为现代欲望象征的惠比寿花园广场,所实际承担的正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媒介角色。如果没有惠比寿作为强劲原始推动力的存在,“我”与韩子煊肯定不会那么快就搅和到一起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惠比寿花园广场在小说中也还一直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大约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所以黑孩才会极富艺术智慧地采用了这样一个看似比较特别的小说标题。
事实上,借助于“我”这样一位深度介入到故事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作家黑孩的主旨乃是要在深度揭示其内在精神奥秘的基础上成功地刻画塑造出韩子煊这样一位格外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正如同白先勇在一部专门讨论《红楼梦》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元素:“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①读完黑孩的这一部《惠比寿花园广场》,我们即可以断言说,这部作品思想艺术方面最突出的一个成就,就是对于韩子煊这一人物形象那种现代病态人格的深度揭示。具体来说,关于韩子煊其人的现代病态人格,恐怕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
其一,他长期以近乎于“讹诈”的无赖方式居住在惠比壽花园广场。我们都知道,在“我”携同韩子煊一起入住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时候,面对着每个月多达十九万八千元的高额房租,“我”曾经明确表达过退缩之意:“我很为难,犹豫了片刻,坦白地说:‘可是,按照这个房租来算的话,我至多只能出三分之一。’”但尽管如此,韩子煊却仍然执意要把这个房租看起来颇有些昂贵的房子租下来。到最后,房子虽然租了下来,但有两个细节却引起了“我”的些许疑心。一个是当管理公寓房的老太太拿来契约书的时候,韩子煊曾经一度想要让“我”去签约:“不知道为什么,韩子煊让我在契约书上签约,我摇头,表示我不能签约。韩子煊耸了耸肩,意思是他来签约。所以租房子的名义人是韩子煊。”另一个则是,面对着需要首付的八十万元,韩子煊拿给“我”一张八十万元的支票,强调说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但他那躲躲闪闪的言词之间的潜台词,很显然是不希望“我”真的去将其兑换成现金。到后来,等到“韩子煊知道我提取了现金以后,看上去心情非常坏,他的脸泛黄,是那种疲倦后的菜色,整个人就像一块洗过后没有熨烫的衬衫,支不起架子来。”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即使如此,稍后,韩子煊还是和“我”达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协议:“说两个人同居后,房费由他来交,我负责衣食和煤气水电费。”面对韩子煊这个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提议,“我”唯有一声不作,因为依照这个协议执行下来,“韩子煊的负担明显比我的负担大”。然而,只有等到“我”后来从房东太太吉田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方才彻底明白韩子煊为什么要主动提出由他自己来承担看起来颇为高额的房费:“吉田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虽然半年已经过去了。除了最早支付的八十万,韩子煊再也没有付过一分钱的房钱。”紧接着,吉田继续发问道:“韩子煊这个人,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有钱呢?他看上去忙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去中国。每次我跟他提房费的事,他都说从中国回来就会有钱,还说有了钱就会付房费,结果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次房费都没有付。”面对着如此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在倍感吃惊的同时,也向吉田提出了她在赶不走韩子煊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断然采取打官司的方式向他索要房费的疑问。对此,吉田给出的回答是:“我赢了有什么用?只要韩子煊不说他不还钱,只要他有还钱的意思,只要他说他没有钱但是他愿意每月还一千元的话,法律拿他也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不在乎韩子煊还不还钱,能不能还上钱。法律只在乎韩子煊有没有还钱的意思。还有从上诉到裁判,你知道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而我已经是个老人,我的身体是这个样子。”实际的情形是,年已六十多岁的吉田老太太,有着长期关节疼痛的毛病。也因此,她才会三番五次地经常征用韩子煊来为她按摩,以求得病情的暂时缓解。这其中,一种彼此交换意味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就这样,虽然时不时地需要付出为吉田老太太按摩的些微代价,但从总体上来说,韩子煊其实是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以一种近乎“讹诈”的无赖方式居住在了惠比寿花园广场。一直到男女双方情感破裂之后,都丝毫未见他有可能主动搬出惠比寿花园广场的迹象。
其二,韩子煊长期扮演着一个四处招摇诈骗的国际掮客形象。应该说,作为韩子煊的同居女友,“我”对他最早的怀疑来自于“亚洲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后一次失败的画展:“虽然画一幅都没有卖掉,只是白白花掉了十几万画廊的租金,韩子煊看上去一点儿都不丧气。”当“我”情不自禁地追问他,画一幅都卖不出去,怎么样才能偿还来自于朋友处的借款的时候,韩子煊给出的回答,竟然是等到下一次画展把画卖出去之后。唯其因为下次画展还八字不见一撇,所以韩子煊的如此一种态度,才会让“我”顿然生疑。事实上,也正是在他们同居在惠比寿花园广场的过程中,“我”方才得以逐渐地了解并认识到,韩子煊其实是一位不断地游走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依靠招摇撞骗为生的国际掮客形象:“开始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虽然韩子煊会告诉我他去中国的日子,却不告知我他回日本的日子。韩子煊去中国了,韩子煊回来了。这样持续了几次,我由不习惯到习惯下来,一个人的时候,晚上我就去惠比寿花园广场。”“其实,原来我也以为韩子煊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跑来跑去是做生意,但是,慢慢我知道他是在骗人。其实,他不过是认识了几个中国人,根据中国人的职业,他随便立出一个项目,然后用这个项目骗日本人投资。钱骗到手,他立刻就去中国住高级宾馆,请客吃饭,唱卡拉OK。钱花光了他就回来了。”也因此,虽然只是与韩子煊接触了不长的时间,“我”妈妈就已经看穿了他这种不堪的老底:“无论韩子煊手里进多少钱,他的处境都无法改变。”到后来,从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真实那里,“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却原来,韩子煊的如此一种不堪状况,其实早在他与“我”结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真实向“我”询问“我爸爸,他现在的工作安定吗”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总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跑来跑去。”真实在强调韩子煊的如此一种境况“跟和妈妈离婚的时候一样”的同时,再度发问:“爸爸他,借有好多债。你知道吗?”在听到“我”的回答是“知道,我经常接一些电话,要我帮你爸爸还钱”之后,真实不由得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反应:“原来爸爸没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韩子煊,其实是一颗非常可怕的定时炸弹:“有时候会害怕,觉得你爸爸像定时炸弹,会把他自己和我一起炸了。”
更有甚者,即使已经到了如此一种不堪的地步,韩子煊也不仅不知悔改,反而还是在变本加厉地继续向深渊滑行。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他向“我”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贪婪索取上。其实,韩子煊对“我”的索取,在他试图推脱最早的八十万元房租的时候,就已经已经开始了。因为知道“我”身为一个作家有着稿费收入的缘故,在一起同居后的韩子煊,更是把贪婪的目光牢牢地盯上了这一笔钱:“好长时间以来,韩子煊一本正经跟我谈话的话,肯定就是投资的事。我拒绝给韩子煊投资,已经有过多少次了?不知道,可能是五次吧。”但韩子煊却根本就不知道,他如此一种充满算计色彩的行为,早已在不经意间严重冒犯了“我”的尊严:“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小心翼翼绕开的就是稿费。我一直无法将写作看成兴趣。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的生命,是我唯一的信仰。如果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去赚钱的话,我愿意以打工来赚钱,而不是用文学来赚钱。”正因为写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如此神圣,所以,韩子煊那种算计稿费的行为方才令“我”感觉特别不舒服。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已经遭到了“我”的多次严词拒绝,但恬不知耻的韩子煊却仍然在不择手段地试图有所索取。这一方面他的一个极端行为,就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扣押了“我”的护照与存折:“我今天整理资料,不小心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你的护照和你的存折。”“我是无意发现的,所以,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机会,就把它们收起来了。换句话说,我把你的护照和存折管理起来了。”实际上,对于早已贪婪成性的韩子煊来说,所谓的“管理”不过是“投资”的别一种客气的表达方式而已。正因为如此,对韩子煊的行为动机早已洞若观火的“我”才会骤然出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韩子煊貌似振振有词地对“我”大加指责:“你为什么不肯帮助我呢?难道你就眼看着我的人生滑下坡去,眼看着我的生活失去尊严和意义吗”的时候,“我”给出的是这样一种严厉的痛斥与回击:“尊严?你跟我谈你的脸?你擅自做出这种事,你缺乏常识。”“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感到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是你对我那点可怜的钱的期待。你不是想跟我在一起,你只是操心我的钱。”到最后,面对着已然接近于无赖的韩子煊,为了索回自己的护照与存折,“我”甚至不惜动用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我握着水果刀走近韩子煊,把水果刀举在离他的脖子很近的地方,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拜托你,请把我的护照和我的存折还给我。’”或者是韩子煊尚有一分天良残存,又或者是慑于水果刀的威力的缘故,在“我”的暴力面前,韩子煊终于乖乖就范,把护照和存折原封不动地物归原主。只有在真正地事过境迁之后,“我”方才不无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在充分认识到“韩子煊是一个自爆炸弹”之后的一时情急之下,或许真的会诉诸于暴力:“我累了。虽然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杀人。这时候,我突然感到恐怖,也许是第一次,我想我真的会杀人。”
其三,总是惶惶若丧家之犬的韩子煊,竟然有着某种可谓是牢不可破的政治情结。事实上,早在与韩子煊刚刚结识不久,一直自诩为“朝鲜族人”的韩子煊,就曾经对“我”坦承过自己的来历:“韩子煊告诉我他出生在韩国,由于他父亲的原因,十六岁的时候,不得不离开韩国。一离开就是几十年。有生之年恐怕都不会再回韩国。”更进一步说,之所以会是如此,与他父亲当年的不幸遭际紧密相关:“韩子煊告诉我,他的父亲因为拥护朝鲜而被韩国政府逮捕,他妈妈受他父亲牵连遭拷问,他妈妈怕拷问会牵连到他身上,即使不受拷问牵连,相信他在韩国也不会有好的前途,于是设法让他来到了日本。”关键问题还在于,正如同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韩子煊其实有着一种堪称屈辱的偷渡体验:“少年韩子煊也是藏在黑暗的船舱里,从大海漂到了日本岛。”一位年仅十六岁的懵懂少年,“一脸黑油”地藏在船舱底偷渡出境。如此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肯定会在韩子煊的内心深处刻下深深的烙印。也因此,虽然已经是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但韩子煊却一直难以说清自己的家国归属:“如今长大成人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但是,说自己是朝鲜族人,因为日本也有好多同类。”然而,或许也正因为是偷渡入境者的缘故,为了生存,聪明过人的韩子煊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套带有混世性质的生存能力与生存哲学。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在获得了多达一百位大学教授的支持后,得到了在日本“永住的在留资格”:“他的名字叫韩子煊,一百名大学教授在他准备好的愿书上,为韩子煊这三个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韓子煊自己不无炫耀色彩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我,虽然是偷渡来日本的,但是,因为我拥抱了一百名大学教授,所以拿到了永住的在留资格。”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韩子煊有着如此一番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所以这位长期生活在日本的“朝鲜族人”,内心里满是空荡荡的感受:“韩子煊说他的内心是空的,我能够理解。妈妈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但是妈妈是生活的最高意义。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当韩子煊跟我这样说起他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这个受苦受难的男人,有资格令我为他痛哭流涕。”一方面是因为的确长期远离着妈妈,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因为妈妈所牵系着的,其实是连韩子煊自己也根本就理不清楚的家国归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子煊毫无疑问应该被看作是一位无根的漂泊者。
关键还在于,韩子煊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存在,在这部《惠比寿花园广场》中,由韩子煊而进一步牵扯出的,是一个涉及到一个庞大生存群体的“在日朝鲜人”的问题。对于所谓“在日朝鲜人”,作家曾经借助于韩子煊之口,给出过相应的解释:“韩子煊解释说,加上‘在日’两个字,意味着这些人是特别永住者。与一般的永住者不同,特别永住者享有好多特权。”“他说,1945年日本战败,南朝鲜独立,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但是,一些前殖民地的土著还留在日本,这些人实际上成为‘弃民’。怎么办呢?日本政府只好给前殖民地的土著颁发特别在留许可。”这样一来,因为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缘故,自然也就形成了类似于“在日朝鲜人”这样一种事实上摇摆挣扎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生存群体。借用“我”的理解,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些前殖民地的人还留在日本,成了所谓背井离乡的难民。于是,日本政府也头痛,就给这些人颁发了特别永住许可。特别永住许可,并不是外国人居住日本的在留资格,而是指南北朝鲜和台湾的那些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的人。”一方面,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永住在留者,却一直以类似于公民的方式生活在日本这样的异国他乡,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其中某种尴尬与苦涩生存滋味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尽管黑孩在小说中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描摹展示这些“在日朝鲜人”的具体生存境况,但通过韩子煊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却也可以略微窥得其中一斑。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一点是,一贯自诩为“朝鲜族人”的韩子煊,却坚决要与这些“在日朝鲜人”划清界限。对此,身为韩子煊同居女友的“我”,倍觉困惑不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朝鲜人对立呢?我觉得,你跟这些特别永住者是同族,却憎恨他们。你的所谓‘朝鲜族人’的核心是什么呢?”对于女友的疑问,韩子煊尽管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从他对待一家在日韩国报纸主编白慧教的态度上,我们却也差不多可以搞明白其中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位总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电视名人”,白慧教的政治态度非常鲜明:“一贯都是批评朝鲜。”针对白慧教的如此一种政治姿态,韩子煊绝不认同。唯其如此,他才会不管不顾地当面予以斥责。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虽然韩子煊自己除了后来的短暂到访之外,并没有过在朝鲜的具体生活经历,但父亲当年那样一种亲朝鲜的政治立场,却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现实政治选择。也因此,在“我”的理解中,韩子煊绝对属于那种思想跟不上时代演进步伐的落伍者,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既往政治时代的一个活化石:“你十六岁不得不偷渡到日本,你觉得是白慧教的责任吗?世界每天都在往前走,好多事情都变了,你纠结你的过去,你的过去跟人家有关系吗?”更进一步说,“我觉得,虽然生活一如既往地向前走着,但韩子煊被什么拽住了大腿,向前走的时候要费很大的劲儿,所以,他不向前走了,只在原地踏步。我想,也许韩子煊累了。”
论述至此,一个需要我们加以思考的问题就是,韩子煊这种牢不可破的政治情结,与他那近乎于无赖的四处招摇撞骗的渣男品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无法简单地断言二者之间毫无联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韩子煊十六岁之后的所有人生,都与他的那次偷渡行为紧密相关。但在另一方面,说一位渣男必然会如同韩子煊这样具有一种奇特的偷渡经历,却更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也因此,一种最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结论就是,四处招摇撞骗的无赖渣男与难以彻底消解的政治情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韩子煊这一人物形象堪称丰富的人性复杂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韩子煊的渣男本性却并没有止步于以上数端,在同居过程中,“我”还进一步获悉了解到其他一些问题的存在。首先,是韩子煊面对女性时色狼本性的大暴露。这一点,其实最早突出地表现在和“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一次,韩子煊就主动提出要摸一摸“我”的屁股。当“我”询问他理由的时候,他做出的回应是:“我只是想抚摸一下你的屁股,想知道你的屁股是凉的,还是热的。”其实也不仅仅是美月,韩子煊日常生活中女伴的更换之频繁,我们可以从朴教授对“我”的谆谆告诫中得到某种强有力的证明:“朴教授说:‘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上个星期,韩子煊刚刚来过我家。不过,跟带你来时一模一样,这一次,他也带来了一个女人,好像刚刚从俄罗斯来日本不久,还不会说日语。’朴教授停顿了一会儿,‘其实,在你之前,韩子煊也曾经带了一个女人来,是蒙古出身的。’”惟其如此,朴教授才会进一步告诫“我”说:“他一贯如此,到处撒网抓鱼,到处钓鱼。他离开你,我反而高兴,知道你没有上钩,就是没有受到伤害。”以上种种,所充分证明的,正是韩子煊对于女性时一种过于贪婪、轻薄的色狼状态。
其次,是韩子煊那样一种知错不改的拒绝悔改态度。事实上,尽管韩子煊一再辜负“我”对他的美好期望,一再地暴露出自己的丑恶面目,但“我”却并没有对他彻底绝望,尤其是在了解到按照日本的法律,一个人竟然可以“自我破产”的时候,“我”也曾经希望韩子煊能够通过这种“自我破产”的方式改头换面地重新做人:“我以为我可以把韩子煊当成不重要的存在,彻底忽视他。我现在却像鼓足了勇气,对韩子煊伸出了我的手,想要他抓住。”但“我”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个“自我破产”的建议,到头来却遭到了韩子煊的坚决拒绝:“但是,自我破产就等于彻底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好多工作都没有资格做了。而且,官报一旦曝出实名实姓,那么,我连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会失去,因为没有人再会信任我,没有人会再希望我帮他们找机会了。再说了,我可是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在绝望中投奔到日本的朝鲜族人。”也因此,韩子煊才会咬牙切齿地近乎丧心病狂地表示:“去他妈的自我破产吧。”或许与“我”的作家身份有关,对于韩子煊如此一种带有明显“自暴自弃”意味的举动,“我”给出了某种具有一定深度的精神剖析:“我差不多知道韩子煊的心理了。在韩子煊看来,他宣布自我破产可能会带来更加残酷的现实。尤其韩子煊认为自己是一个朝鲜族人,所以不能在日本自我破产。但是,我不太理解韩子煊的心理。说真的,韩子煊强盗似地到处骗人家的钱,事实上,他在人格方面早已经是破产的了。”實际上,也只有在劝说韩子煊“自我破产”无果的情况下,“我”才进一步认识到韩子煊的邪恶本性以及他彻底的不可救药:“韩子煊和他身边的人,好像都被骗局和大笔的债拴着。骗局和大笔的债,像一根绳子拴在韩子煊和他身边的人的脖子上,正在慢慢地勒死他们,或者正在勒紧他们,而他们不惜一切地寻找着所有可以翻身的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便牢牢地抓住不肯松手。”很大程度上,也只有读到这段犀利剖析文字的时候,我们方才可以反过来理解在与“我”不到一年的交往同居过程中,韩子煊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他的一再要求“我”投资,抑或还是他对“我”护照和存折的悍然扣押行为,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已经看清了国际渣男韩子煊的真面目,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彻底诀别韩子煊:“对鱼的想象(主要是指自己无意间变成了为韩子煊所钓的“鱼”)令我很难过。我决定搬家,还决定带走惠比寿。”“一年里,这是我的第三次搬家。北京的时候,我亲自扔掉了我所有的东西。菊名的时候,我跟韩子煊两个人扔掉了我所有的东西。惠比寿这里,我搬走了,我知道韩子煊不可能住得长久,那么,我和韩子煊共同拥有过的东西,要韩子煊一个人来扔了。”然而,尽管“我”已经做了足够充分的精神与心理准备,但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我”的表现却依然还是比较失态:“穿过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时候,热潮涌过我的全身,血液膨胀得要撑破我的肉体。我对妈妈发誓,说再也不到惠比寿花园广场来了。走进车站的时候,我目不斜视。第一次,我觉得我将一种称为憧憬的东西,连根拔起了。”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可以明确地意识到小说标题“惠比寿花园广场”一种强烈的象征意味。却原来,惠比寿花园广场也可以被看作是“我”某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情结之所在。正如同叙述者“我”在叙述过程中所明确表示过的,即使当初“我”无意间巧遇的那个男人不是韩子煊,自己恐怕也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他搬到惠比寿花园广场来居住:“当初,我说碰巧遇到了韩子煊,如果我遇到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结果会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结果是相同的。”说实在话,真正惊到笔者的,正是“我”所给出的这一段话。却原来,对于“我”来说,惠比寿花园广场所象征的那样一种高品位的现代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某一位具体男性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惠比寿花园广场》这部长篇小说中,具有现代病态人格者并不仅仅只是渣男韩子煊一人。韩子煊之外,另一位现代病态人格的突出体现者,就是这位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深度介入到故事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小说中,叙述者“我”对自身病态人格问题的最早觉醒,是在“我”随同韩子煊一起来到朝鲜的时候。在朝鲜,因为对韩子煊心生不满的缘故,“我”于不经意间突然意识到,当年曾经致父亲于死地的忧郁症,其实也在自己身上有所遗传:“我总是觉得我身体里有另外的一个人,她与我的距离好像白天和黑夜的距离。而我知道,在这个地球上,白天和黑夜是同时存在的,打一个比喻,好像日本是白天的时候,美国却是黑夜。黑暗从我的感觉里退出之后,明快会覆盖我。这种反复好像会永远持续下去。”所谓的身体里有另外一个人,所寓指的,其实也就是“我”身上某种现代分裂人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我”对于韩子煊那种既有所厌恶但却又有所依赖的矛盾姿态,正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现代分裂人格的突出体现:“韩子煊教会我厌恶,厌恶他,厌恶我自身。我跟韩子煊在一起,用他骗来的钱在朝鲜旅游。在韩子煊的灵魂里,我看到了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我想把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从韩子煊那里切除掉。因为是这个原因,我正在用五官,用身体感受那种死了算了的难受。如果死是对生命的亵渎,我很愿意赎回我跟韩子煊的灵魂。”然而,还等不及“我”采取任何所谓“赎回我跟韩子煊的灵魂”的行动,“我”却很快就在房东太太吉田那里不仅了解到了韩子煊拒付房租的无赖行径,而且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阴暗面:“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时间静止并凝固了。”“我费了半天力气,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令我痛苦的起因。我一向把盗窃看成所有罪恶的原型,认为盗窃偷走的,是公平的权利,所以也是令人无法原谅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半年来,我跟韩子煊,竟然会白白地住在惠比寿的公寓。我认为,这跟抢房东太太的钱没什么区别。我跟韩子煊,跟所谓的强盗没有什么区别。”在意外地获悉韩子煊一直赖着房租不付的情况下,“我”一方面迅速地表示作为韩子煊的同居者,自己也有交房费的责任,但在另一方面,恐怕连她自己都会倍感失望的一点是,等到房东太太吉田表示,如同“我”这样一个女孩子,根本不可能付得起昂贵房费的时候,“我”却似乎一下子就心安理得了:“吉田说得这么具体,我也知道无奈和绝望是怎么回事儿了。我还搞不清我自己的立场,我在韩子煊这边,我也在吉田这边,我到底在哪边呢?对惠比寿花园广场的种种回忆冲击着我的脑海,里面翻腾着我最热切的向往。失意和失望,不可阻挡地涌到胸中,强烈地洗刷着我的心。”究其根本,“我”之所以会在韩子煊与房东太太吉田之间一时摇摆不定,还是自己内心中某种潜在的贪欲心理作祟的缘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潜在心理作祟的缘故,“我”才会近乎本能地站在本来毫无道理的韩子煊一边。
事实上,也只有借助于韩子煊这样一个镜像的存在,“我”方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身内在精神世界中的黑暗面。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妈妈来到日本之后。原本,“身居惠比寿花园广场这个事实,好像麻醉剂,麻醉了我身体的某一根重要的神经。”妈妈来到日本后,不仅一眼看透了“我”糟糕的生存状况,而且还委婉地提醒“我”一定要早做决断,早一点离开韩子煊这样一个恶魔式的渣男。妈妈的及时提醒,催促“我”作出更加深入的自省:“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与韩子煊的关系虽然已经裂纹丛生,尤其裂纹处生出很多的污浊,但是除了我们之间或许存在的那点儿恋情之外,搬家前,在菊名的那个缠绵而又激烈地夜晚,韩子煊已经浸透在我的骨、我的灵魂深处。我的情形是,虽然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觉得问心有愧,但作为与韩子煊同居的女人,良心上所感受到的责任尚没有达到极限。尤其吉田这个老太太,在她对我暴露了她的孤独之后,我的忏悔的心境便得到了拯救。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形容我人间失格。是的,就是人间失格,还要更甚!”就这样,借助于妈妈到来后的及时提醒,“我”再度陷入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批判与忏悔的心境之中:“还有,坦白地说吧,好不容易住到憧憬的惠比寿,惯有的醉醺醺的快感缠绕着我,结果形成了所谓恶性循环的怪异的三角圈。”尤其是那次酩酊大醉后与韩子煊的无耻交合过程,更是让“我”看到了自己精神丑恶的另一面:“虽然是喝酒喝醉了,仍然可以证明那个时候的我,是下流猥琐的。”说透了,“我跟韩子煊,原来竟好像亲生的骨与肉。我与韩子煊是两个人格欠缺的人。”很大程度上,“我”与韩子煊,是彼此互为镜像的两个人物形象。借助于彼此的互为镜像,映照出的,正是他们俩各自的人格欠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互为镜像,促使“我”心生悲凉:“一想起那个失控的夜晚,我就会感到悲凉,悲凉无法制止,无边无际地蔓延滋长着,这是对我的惩罚。住到惠比寿之后,我的内心有点儿不像人样了,受惩罚,是早晚会发生的事。”也因此,在充分地意识到,为了达到入住惠比寿花园广场的目标,自己竟然可以无所顾忌地选择追随任何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更是对严重人格欠缺的自己倍觉厌恶:“当我想象我牵着韩子煊的手,一起走在人生的那条看不见终点的小路时,我觉得很恐怖。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提升韩子煊,因为我跟韩子煊是一路货色,都人格欠缺。韩子煊靠给楼上的老太太按摩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而我靠韩子煊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我没有比韩子煊好到哪里去,甚至比韩子煊还要坏。或许我应该替韩子煊跪在老太太的面前感谢老太太。我不过是一只寄生虫。”原本我们都只认为渣男韩子煊所具备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现代病态人格,特别令人厌恶和反感。没想到,与韩子煊相比较,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竟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竟然也同样是一位人格欠缺者。说实在话,在一部带有明显自传性特点的长篇小说中,作家黑孩能够以如此一种方式展开内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作家具备某种非同寻常的写作勇气。究其根本,能够把审视的矛头从他者转向自我,能够展开足够深入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对于《惠比寿花园广场》内在思想艺术品格的进一步提升,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分析至此,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在这样一部以刻画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体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为什么要不惜花费很大的笔墨去关注那只被“我”命名为“惠比寿”的流浪猫,要去书写表现“我”和妈妈与这只流浪猫之间由疏到近的情感关系呢?流浪猫“惠比寿”的登场,已经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是伴随着妈妈的来到日本而出现的。这只猫的命名者,是“我”:“我给这只猫起了个名字,叫惠比寿。因为它出生在惠比寿公园,又在惠比寿公园与妈妈相遇。”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日本的七福神话中,惠比寿是所谓的“福神之首”。因为在妈妈的喂养过程中,与这只猫结下了深厚感情的缘故,“我”曾经告诉妈妈,自己会在妈妈回国后,把“惠比寿”接到家里来养。没想到,到后来,就在“我”试图把“惠比寿”带回家里的路途上,由于受到意外惊吓的缘故,“惠比寿”竟然一下子发飙,张嘴咬了“我”的手。咬了“我”倒也还罢了,关键还在于,回到家里后,“惠比寿”竟然在慌乱之间掉进了墙壁和浴缸的夹缝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得不动用消防署的工作人员想办法把“惠比寿”寻找并拯救出来了。就在这个寻找拯救的过程中,韩子煊和“我”之间发生了一场饶有意味的对话。韩子煊问道:“多少钱你都肯花?几百万你也肯花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韩子煊紧接着追问:“那么,几千万的话,你也肯花吗?”“我”的回答依然是“肯”。这场对话,一方面引发出了妈妈的一种自谴,另一方面却也让韩子煊倍感失落。却原来,在“我”的心目中,韩子煊竟然还没有一只流浪猫重要。而这,到后来,自然也就变成了他最终决定远离“我”的一个主要诱因所在。事实上,也正是在“我”对韩子煊感到彻底绝望的同时,在“我”这里感到无利可图的韩子煊,也在疏远着“我”,独自离家好久后都不曾回家。韩子煊根本无法料想到,自己的如此一种做法,竟然被“我”理解为“被遗弃”:“自我暗示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让我放松自己。至于韩子煊,我只剩下被他遗弃的想法了。到头来,人在绝望的时候,就会接受现实了。被遗弃是我决定离开韩子煊的最好的理由。一切如此简单。”“我”一向是一位优柔寡断的人,很多时候的行动都需要有某种外力的推动。尽管对韩子煊早已心怀不满,但却始终无法下定远离他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被遗弃”,恰好构成了促使“我”下定决心彻底离开渣男韩子煊的根本动力。
然而,与成为“我”下决心远离渣男韩子煊的诱因相比较,流浪猫“惠比寿”的重要性,其实更体现在一种精神救赎功能的昭示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就在妈妈因为“惠比寿”而自谴不已的时候,作家曾经写到:“我理解妈妈的心情。男人和空洞,都是事先想象不到的意外。归根到底,不好的不是妈妈,不是惠比寿,也不是我。”事实上,流浪猫“惠比寿”的设定,恐怕更多地还是要起到一种对比映衬的艺术作用。如果说妈妈和“我”对一只萍水相逢的流浪猫所采取的都是一种悉心呵护的态度的话,那么,对于同样是萍水相逢的韩子煊,到最后之所以会表现得特别决绝,那就是因为他那人格严重欠缺的无赖卑贱品性实在令人无法容忍的缘故。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更须注意到“惠比寿”这只流浪猫对一种精神救赎功能的昭示。一方面,妈妈,以及“我”在妈妈的精神感召下,对“惠比寿”这只流浪猫的悉心呵护,所昭示出的,固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救赎情怀,然而,在另一方面,虽然从故事情节的演进层面上看,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我”最终远离了渣男韩子煊,但从内在的精神理路上來看,作家所最终出示的终极态度,却依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悲悯意味的精神救赎。说到底,能够在饱受韩子煊的伤害之后,仍然能够写出一部《惠比寿花园广场》来,作家的如此一种书写行为本身,即意味着宽恕之后的精神救赎。
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情节设定层面上,黑孩的这部长篇小说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孔乙己》所采用的,也是一种深度介入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者“我”,乃是咸亨酒店一位卖酒的小伙计。一方面,身为叙述者的小伙计对孔乙己的态度有一种由起初的理解同情到后来的麻木冷酷的变化过程。“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样的一段冷冰冰的叙述话语,所透露出的,其实正是小伙计“我”骨子里的某种麻木冷酷。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叙述者“我”也即这位后来越变越势利的小伙计之后,也还有隐含作者存在着。对此,曾有论者做出过深入的分析:“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②尽管并非完全相同,但黑孩关于小说叙述方式的艺术设定,却也有类似的艺术效果。一方面,我们固然在以类似于叙述者的眼光理解看待渣男韩子煊,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在以隐含作者的视角理解看待着叙述者“我”。更进一步说,我们在前面所具体提及的,那样一种与流浪猫“惠比寿”紧密相关的精神救赎情怀,也主要是通过潜在的隐含作者而充分凸显出来的。
注释:
①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第192—193页。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5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