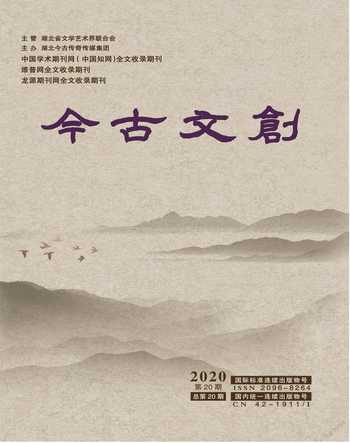文学治疗视域下莫迪亚诺的作品
【摘要】 文学具有文学治疗作用: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释放了压力,排遣忧愁;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作品给读者带来精神慰藉。莫迪亚诺早年生活惨淡,个人身份的疑惑深深影响其作品创造。二战结束后,集体失忆成为社会现象,重获和平的欧洲陷入精神危机。莫迪亚诺通过对身份、父母的追寻释放了内心压抑已久的痛苦与过去达成和解,达到了恢复心灵健康的作用。
【关键词】 文学治疗;记忆;身份;遗忘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30-03
文学能够满足我们五个需求:一是符号游戏的需要;二是幻想补偿的需要;三是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四是自我确证的需要;五是自我陶醉的需要。文学以语言作为承载,不仅帮助作家宣泄内心的愁绪,还以自己的文字感染大众,实现“文学治疗”的目的。
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博爱是人类本性,只要积极引导这种自然倾向,就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他将社会看作整体,而家庭在其中充当了“社会真正的要素,社会的细胞”不可或缺的角色,家庭是孕育博爱的摇篮。而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家庭关系淡漠,幼年经历坎坷:父母对其置之不理;弟弟吕迪突然去世成为无法弥补的痛处;个人身份迷茫都是构成作者内心创伤在其作品中展现。通过写作,莫迪亚诺找到过去和现在的平衡与过去和解。另一方面,莫迪亚诺身处二战结束后动荡年代,战后人们经历集体失忆症,但一味逃避并不能真正磨灭悲痛。莫迪亚诺在作品中承起作家责任直面过去抵抗遗忘,用文字治愈大众。
一、追寻身份,平息焦虑
我们身处社会,角色、地位就会如影随形。行动者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社会对角色有不同期望,社会由这样的行动者构成。人是群居动物,“个体形成群体乃至组织就像角色,地位一样,只要你是群体一员,就要背负起相应期待。”宗教作为影响深远的群体或者组织,为个体提供理解自身存在的支持。作为成员,我们会对群体忠诚,也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感”,“他们感”。
作为生活在法国的犹太人,莫迪亚诺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和犹太传统分离:从小生活在法国;母语是弗莱芒语。莫迪亚诺一直在法国人和犹太人两个身份间漂泊。虽然他出生时二战刚结束,“但纳粹宣传影响深远,公开的反犹主义仍然存在”,因此,他的母亲让他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送他去天主教会学校读书。
对于犹太人而言,他是天主教徒;对于天主教来说,他是异类,两方都不接纳他,他是没有身份的人,即使是土生土长也是异国他乡。同为犹太人的父亲没能帮助孩子进行自我身份构建,还让原有的疑惑更激烈:莫迪亚诺的父亲是犹太人,却在二战时期伪造证件用不同身份从事黑市走私,和德国警察勾结出卖同胞。父亲的秘密萦绕作家心头,甚至内化成他生命的整体在往后岁月里回响。
作家对身份的焦虑直接反映到作品人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作品中叙述者都为身份问题困扰。他们是作家的替身,替他說出身份迷茫、寻根、分担烦恼。在大部分作品中,主人公要么患上失忆症,不忆往昔;要么失踪,身份成谜。想要追寻记忆的叙述者不断找到线索,直到填补记忆空白。身份的失去与找寻成了作品核心主题。
莫迪亚诺处女作《星形广场》主题就是犹太人的身份迷失和归属。主人公拉法埃尔·什勒米洛维奇是一位犹太人,他的身份不断变换:反犹的犹太人;作家;编辑;顺从的儿子。主人公陷入了光怪陆离的幻觉和身份迷失当中。他拥有很多身份,但无论哪个身份都不能给他足够的归属感,但是这些身份就像标签一样贴在他身上撕不掉。他游离在这些身份之外,所以他总是在质疑,否定自己身份。23岁的莫迪亚诺锋芒毕露,不仅不爱自己,学不会与世界妥协,执着地追问“我是谁”,非要得出确切的答案。在作品当中体现了莫迪亚诺对于身份问题的迷思与哲思,莫迪亚诺将自己身份支离破碎,不能找到身份认同的绝望注入角色,所以,主人公也深陷身份认同危机的漩涡不能自拔。
写于《星形广场》十年后的《暗店街》虽然仍然是寻找身份的故事,但是结局却全然不同。叙述者是个得了失忆症的男人,私家侦探于特出于同情收留了他并给了他新的身份, 新的名字:居伊。“居伊”是法语单词“谁”的音译,如同他的名字,居伊一直为空白的前半生和丧失的身份所困,正如开篇所言:“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于是在于特退休之后,主人公决定寻找遗留在德占时期巴黎中,自己的真实身份。
全篇,叙述者都困于虚无的过去,在记忆的迷宫里跌跌撞撞,将他人身份认作自己。个人的过去已随历史掩埋,居伊也要逆流而上,试图在用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一个“我”。虽然最终谜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叙述者的过去开始明了清晰,不再是一片朦胧。
十年时间大浪淘沙,莫迪亚诺早就收敛了刺人的锋芒,追寻的路没有终结,但原本性格尖锐,颓唐不已的青年如今已经有了处事不惊的从容,在记忆中探索到的些许线索给了他太多慰藉。八十年代前,莫迪亚诺书写的主要内容是身份的追寻。从最开始的犹太人到无国籍者,流浪者;八十年代之后,他的作品主题更偏向于对记忆的挖掘收藏,对往昔的怀旧。在写作当中,莫迪亚诺找到了自己立足于世的恰当位置,不再单单执着于自己的犹太身份。
二、追寻父母,排遣遗憾
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和经历有关,所有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的所有需求,所有期望,都是曾经经历没有得到,所以现在渴望得到的。而其中,童年对我们性格、态度形成最为重要。在这阶段形成的性格,态度思维都会储存在潜意识里,后来整个人生都会受影响。而童年对作家而言更是意义重大,童庆炳先生曾说,“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懊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
正如莫迪亚诺在诺奖获奖演讲上说的,“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笔。我长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来,这让我想试图通过写小说来解决这些迷惑,希望写作和想象力能最终帮我把这些零散的线索都串起来。” 莫迪亚诺的童年和幸福二字牵扯不上关系。正是因此,莫迪亚诺的作品总是萦绕着淡淡的忧伤气息。一方面,这份经历给了莫迪亚诺无尽的写作灵感;但另一方面,过早的生活重压给他的心理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莫迪亚诺的父母绝对算不上称职:母亲作为演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常年不见踪影;父亲在战时昧着良心做黑市交易,勾结盖世太保,甚至出卖同胞。战后几十年都频频出行,逃避自己做过的丑事,对孩子更是漠不关心。我们总说家是温暖的港湾,是遮风挡雨的巢,但莫迪亚诺的父母并没有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家。正如莫迪亚诺在访谈中所说,“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从最开始寄养于祖父母,到辗转于三教九流的父母友人家中,莫迪亚诺的童年全都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经历,鲜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在莫迪亚诺作品中,现实和虚构并存,夹杂亲身经历,他从自己早年经历中来获取对文学创作养分,追溯成长历程,直面往日的痛处,探求父母“抛弃”自己的理由,也不乏对父母关爱的渴求。在其中作者完成了童年情结的表达。我们可以看见父母亲,或是类似角色在他作品中出现:《暗店街》中侦探于特扮演了父亲,在叙述者最窘迫的时候给他在巴黎生活下去的身份与工作。不问过去,全心全意相信他,像父亲支持孩子一样支持他的决定,并竭尽所能提供帮助。这样为孩子保驾护航的父亲角色大概是作者一直渴望的。“占领三部曲”《环城大道》中,父亲将十七岁的孩子推下地铁铁轨,试图杀死他,只因为孩子没了利用价值,还知道太多自己黑市交易细节。
十年后,身处动荡的“占领时期”,叙述者作为犹太人,没有合法证件,随时面临大搜查的威胁。但他仍决心寻找父亲,想了解父亲是否需要自己的帮助。然而父亲早忘记叙述者,父子相见不相认。即便如此,主人公仍然留在父亲身边,暗地里为他筹划。叙述者有时候也会对父亲无视自己而沮丧,决心放任父亲和流氓沆瀣一气,但总会心软,不仅不计前嫌地充当父亲的“守护天使”,还认为父亲将他推下铁轨情有可原:“父亲要杀掉或摆脱儿子,这完全是当前社会价值大混乱的表现”。他为父亲抛弃自己找好理由。《夜半撞车》中被父母抛弃的叙述者,面对他人母亲般的体贴、嘘寒问暖虽然感到局促,但更多是不自觉依赖。
现实中,莫迪亚诺与父母关系僵硬,但内心却渴望父母关怀。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追寻父母”主题是作者对父母的追问,也是作者想瓦解与父母隔阂的尝试。他试图再现父母的生活过往,追寻他们的足迹,从记忆中挖掘细枝末节来了解父母对自己不管不顾的原因。莫迪亚诺通过写作拼接记忆碎片,在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中完成了和父母、过去的和解,也从中攫取了现世生存的力量。不甚满意的童年可以随时间流逝渐趋平静,莫迪亚诺用写作的方式宽慰自己,虽然父母造成的伤害不会消失,但他已经能坦然面对,平静述说往事。
三、抵抗遗忘,再现记忆
时代是作品最深的烙印。莫迪亚诺出生时,二战刚刚结束。人们重获自由,但宁静并没有如期而至,百废俱兴背后掩映着精神危机。
“谋杀成为记忆,记忆变成美丽的枷锁。个体的记忆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二战之后,欧洲忙着重建美好新欧洲,创造了经济奇迹,曾经鲜活的痛苦随着时间流逝淡去。大家都假装失忆:二战的屈辱,颓势愈烈的国家实力。比起面对现实,大家更愿意活在虚妄的歌舞升平中。“在战后最初的岁月里……集体性失忆成了欧洲人的庇护所……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反省战争和沦陷的真实经历——即是没有时间悲伤。”
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中提出“共同价值内化”:被社会成员内化的价值准则上升为整体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反过来指导民众行为规范。是单位行动到社会行动,最终又影响到单位行动的过程。从微观到宏观,再返回微观视角。“社会结构的事实是超越个人,并对个人有制约力的行为或思维类型,它独立于个人之外,也强加在个人之上” 个人失忆上升为集体失忆,重提往事的人就是异类,会“受到惩罚,被视为精神不正常,被社会排斥。”在此社会环境下,对过去沉默成了大家的默契。活着的人只想往前看,回忆过去徒增现实的负担。就像莫迪亚诺在诺奖致辞中说,“当孩子问起当年的历史,他们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要不然就避而不答,好像能把那段黑暗的时光从记忆中抹去,还有就是隐瞒一些事情不让孩子知道。可是面对父母的沉默我们明白了一切,仿佛自己也亲历过。”战争结束了,但是带来的影响久久不散。甚至阴魂不散糾缠下一代人。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段历史都成了集体记忆中不见天日的部分。可想而知,曝光过往,打破幻觉与沉默,人们会陷入何等困境。
战后国家迅速重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孤独、苦闷、迷茫,以为不谈就可以忘掉过去,最终走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莫迪亚诺的写作则是在废墟中挖掘记忆的碎片抵抗遗忘,还原绝口不提的过去。2014年,莫迪亚诺获得诺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称“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
莫迪亚诺的小说通过寻找,调查,回忆,探索,将视野转回从前的岁月。《多拉·布吕代》主人公原型取自德占时期的真人。在1941年的寻人启事上,一对犹太父母寻找在学校失踪的十五岁女儿多拉。莫里亚诺搜集旧报纸时看到了这份启事,难以忘怀,他调查收集保存下来的信件,照片,地址,最终在1942年从巴黎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上发现了多拉的名字。现实和想象的结合让陌生的名字有了气息,“多拉”只是个名字,而二战期间的“多拉”何其多?她们都真实存在过,只是被故意遗忘了。
阅读莫迪亚诺的作品就是和他一同游弋于朦胧的过去,寻根究底。在他笔下,文中叙述者们对于过去的事物有特殊的 “收藏嗜好”:精确到街道门牌号的巴黎地址还有旧报纸上的信息。《暗店街》中被奉为圭臬的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是于特不可替代离不开的工具书。这本名录是过去五十年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无国籍老人在每张照片后面写上人物事件备注,小心翼翼收藏在饼干盒子里,这就是他前半生全部记忆了。《家谱》中叙述者总是反反复复说着那个时期自己读过的作家和作品名字。“我把所以这一切都记在了那个黑色记事本上”《夜的草》一书中,主人公的黑面记事本里写满笔记:人名,电话号码,约会日期,剪切的报纸上的小启事,事无巨细,就连剧院女演员在几分几秒说出哪句台词都要记录。为什么这样做,作者借由主人公之口,说出了原因,“我需要时间坐标,地铁站名,楼房的号码,狗的系谱,我担心那些人和事物眨眼之间就会躲开或者消失,起码应该保留一个他们存在过的证据。”这本笔记本里的文字是证明自己和他人真实存在,而非活在梦境中的铁证。
战争结束了,城市毁了,有些人就这样消失了,这让莫迪亚诺这一代人对记忆和遗忘特别敏感。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众人向前疾走,过去的记忆也在不断消失,反而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字母,坐标”,才是证明他们的存在,回答“我是谁”的最好答案。“对物的忠诚记忆,或许是对抗动荡人生,抵抗遗忘的一种绝佳办法。”
不同于普鲁斯特,写作于莫迪亚诺而言不止于追忆往事,更多的是借写作解过去困扰,用文学平息读者内心对于永远不得而知真相的焦虑,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假装遗忘并没有效用,莫迪亚诺背负着作家的使命,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同遗忘与被遗忘抗争,用文字与写作弥补空白,让褪去的言语重现,直面才是对伤痛最好的治疗。
参考文献:
[1]戴维·纽曼.欢迎光临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1-55.
[2]基恩·罗威.野蛮大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7.
[3]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7.
[4]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夜的草[M].合肥:黄山书社,2015:89.
[5]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环城大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7.
[6]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家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7.
[7]托尼 · 朱特.论欧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1.
[8]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J].社会学研究坛,2000,(3):55.
[9]袁箐虹.论莫迪亚诺作品中的“记忆拼图”[D].浙江大学,2017,15-16.
[10]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 1998,(6):84.
[11]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作者简介:
张佩维,女,汉族,重庆人,硕士研究生,电子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