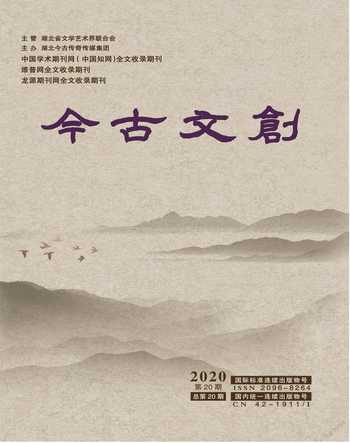《醒世姻缘传》服饰描写与泼妇形象塑造关系探析
【摘要】 从《醒世姻缘传》中的服饰描写入手,可以对“泼妇”这一作品中最具特色的群体进行探究,分析作者西周生是如何通过服饰描写塑造泼妇形象,揭示泼妇内心,展现泼妇之间关乎生存与利益的斗争。
【关键词】 服饰描写;泼妇形象;心理;妻妾斗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21-03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一部以描写前世今生两世姻缘为主线的世情小说,它通过主人公的家庭社会关系,串联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胡适曾称“我们自然会承认这本百万字的小说不单是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史料”[1]384。
在这部社会写生中,西周生对出场女性的服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绘,其中包括她们的首服、足服、所穿的衣服以及各种佩饰等。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服饰描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运用甚多,本文将分析小说中的泼妇形象,探究作者是如何通过服饰描写来塑造这一极具特色的女性群体。
一、服饰描写与泼妇形象的刻画
“泼”在《现代汉语小词典》里的释义为“蛮横不讲理”[2]426,马克梦在其著作中将“泼妇”解释为“把祸水泼向男人使其丢面子”的女人[3]57。计氏、薛素姐等人是《醒世姻缘传》中最具代表性的泼妇,她们都有强势蛮横的一面,但其形象特征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各有不同,服饰描写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塑造这类泼妇的形象,凸显人物性格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一)计氏
在晁家还未发达时,计氏的娘家在经济上给予了晁家很大的支持,被晁源当作宝的计氏完全有逞凶泼悍的资本,敢于对丈夫开口就骂,起手即打。只是随着晁家的暴富,计氏完全沦为了一个“失权者”的形象,小说中对她的服饰虽着墨不多,却很有代表性。第2回,计氏听说晁源带珍哥打围,第一反应就是珍哥虽是娼妓出身,既嫁给了晁源,就不该“穿了戎衣”和一群男人抛头露面。[4]13
计氏对晁源态度蛮横,很大程度是经济优势和晁源的纵容助长了她的气焰,她的内心仍然相对保守。对比珍哥的风光华服,被留在家中的计氏所着服饰却是“帕子裹头”,穿“羔皮里的段靴”“半臂和单叉裤子”[4]14,显得十分朴素,这与她家庭地位发生的变动有很大关系。前者打扮得甚是齐整,后者都不曾梳洗,珍哥受宠而计氏遭到冷落的现状一目了然。
小说第3回提到,被晁源厌弃的计氏在年节时清锅冷灶,父亲计老头劝她折了衣裳首饰过年,但她不愿听从,这处描写进一步深化了计氏的困窘处境。经济无法独立的古代妇女,失去了丈夫的宠爱,无人依靠,就连日常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但同时,一个泼悍而有气性,竭力维护自我尊严的女性形象也跃然纸上,只是计氏要维护的尊严,实际更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无情戕害。计氏被污蔑私通,自缢之前戴上首饰,缠好脚,穿上了新制的“银红锦裤”“两腰白绣绫裙”“月白绫机主腰”,以及“天蓝小袄”“银红绢袄”“月白缎衫”和“天蓝段大袖衫”[4]70,可谓是盛装打扮。
自宋代以来,理学家们对贞洁观过于推重,贞洁成为封建社会为女性制定的严苛道德要求,是对女性单方面禁锢的武器,为了维护父系血统的纯洁,女性必须自始至终对丈夫保持专一。总是轻鄙珍哥是“淫妇”的计氏,自然无法容忍自己背上私通的罪名,只能选择以死证节。对婚姻心灰意冷,而只能寻求道德的完善,这让计氏的死有一种荒唐之感,她维护尊严的途径,充斥着封建社会妇女的血与泪,是极为可悲的。
(二)薛素姐
小说对薛素姐服饰的描写也颇为细致,在展现素姐美貌的同时,令人深刻地体会到她的“表里不一”,妖娆美丽的容颜与她一颗好心被狐精换去,从此变得泼悍凶恶的性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薛素姐成亲时小说里有几段对她服饰的描写:“柳叶眉弯弯两道,杏子眼炯炯双眸。适短适长体段,不肥不瘦身材。彩罗袱下,烟笼一朵芙蓉;锦绣裙边,地涌两勾莲瓣。若使雄风不露,争夸洛浦明妃;如能英气终藏,尽道河洲淑女。”[4]351
就连得知了前世孽缘的狄婆子见了她,也暗自欢喜。身穿喜服的素姐看起来温柔雅致,娇媚妖娆,小说用了仙女、芙蓉、淑女等词来形容她,但就是这样一个美人,在新婚之日就开口骂人,婚后更是肆意殴打丈夫,辱骂公婆,與儒家传统中理想的淑女形象相去甚远。
除了表里不一的凶悍个性之外,薛素姐的妒性也格外强烈,第52回中她因狄希陈私藏汗巾和眠鞋而大发雷霆的情节就印证了这一点。汗巾与眠鞋都是女子的贴身之物,《红楼梦》中袭人与蒋玉菡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条汗巾,至于女性的鞋履,更是常常成为女性向男性表示爱慕的信物,林语堂曾指出男子喜爱女子的金莲,“歌咏之,崇拜之,盖把小脚看作恋爱的偶像”[5]152。
素姐见到狄希陈紧张汗巾与眠鞋的模样,自然猜到这是其他女子赠予之物,将狄希陈打得伤痕累累,甚至将他拴在床脚用针去扎。可见妒意会让泼妇变得更为凶悍暴虐,这是由于她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实在的威胁。
马克梦指出,在宗法制度之下,女性“仅仅是一种交换品,地位明显低于男人,泼妇便发泄对孔教虚伪面目的憎恨,用行动和呵斥来迫使男人彻底就范”[3]61,因而一旦丈夫与其他女人私通,泼妇就会感觉更为冤屈,行为更容易进一步走向极端。
二、服饰描写与泼妇心理的揭示
在《醒世姻缘传》中,阴盛阳衰是一种普遍现象,男性对美色和情欲的迷恋给予女性利用自身优势的机会,而他们懦弱的个性的又使泼妇们有机会对夫权进行打压。在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下,极不公平的两性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压抑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天性,一旦她们享受到将男性掌握在手中的快感,凶悍的个性被激发出来,就走上了极端乃至于变态。但女性毕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们被迫分享丈夫,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常常孤立无援,本质仍然是脆弱的,这在小说的服饰描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对男性的控制心理
正如前文所述,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操纵下,女性的地位过于低微,她们只有通过呵斥与逼迫丈夫,使丈夫在自己面前服服帖帖,才能够稍稍缓解自己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冤怒之心。女性所处的位置,受到的限制远远超过男性,于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泼妇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控制男性,保全自己的利益。
小说第63回,素姐误会狄希陈偷藏了从南京带回的顾绣衣裳,大发雷霆,不仅连番逼问,还对丈夫使了诸番刑罚。在莲花庵烧香时,看见了智姐衣裳的素姐就已经被激发出妒忌心,只是此时,她心中所含的仅仅是女性面对不属于自己的美丽服饰时产生的艳羡情绪。但当智姐假言衣裳是狄希陈托人捎回的,这种对美丽衣物的占有欲很快转化成对丈夫的愤恨,这种愤恨远远超越了刚开始的艳羡,甚至绝不仅仅是怀疑狄希陈将衣物赠予其他女子的嫉妒。薛素姐并不需要狄希陈去新买衣裳,指明必须要南京来的原物,这就说明她最无法接受的是隐瞒,是失去对丈夫的控制。
自从嫁入狄家,素姐打骂丈夫、顶撞姑婆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她早就习惯了对这个懦弱丈夫的掌控,狄希陈的隐瞒无疑是一种她无法得到完全的控制权、甚至会失去权力的信号,她将自己的凶悍行为称为“管教”,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惩罚丈夫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巩固。
小小一件顾绣衣裳对于富裕的狄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闹出的阵仗之大令人啧啧称奇,素姐必须借这套衣服发难,以确保自己仍能牢牢将丈夫控制在手心。如此一来,薛素姐凶悍泼辣、善妒凶恶的性格被塑造得淋漓尽致,顾绣衣裳事件揭示出的是薛素姐极为隐秘的内心,她对男性控制欲望之大,已然走向极端。
(二)揭示泼妇的脆弱心理
泼妇虽然凶悍,但在父权社会中,她们的行为始终被视为异端。她们会被维护父权秩序的人围攻,自身也依然依附在男性的权力之下,因而这种行为上的凶悍与内心的脆弱并不冲突,小说第3回的服饰细节描写就充分显示了这点。
珍哥在跪拜晁家先祖时,晁太公显灵时将她吓得被“白秋罗连裙”绊倒,“裹脚面高底红缎鞋”都摔了出去,她平日里向丈夫撒泼,对主母发难,这里只是看了晁源公公一眼就反应激烈,说明心中并不坦荡。西周生此处的描写颇为诙谐幽默,服饰细节突出了珍哥的狼狈,面对鬼神产生的畏惧之态,无疑揭示出她实质的脆弱与心虚。
小说第8回,珍哥见到计氏房中走出来的姑子,随口污蔑,肆意辱骂,而当计氏真正自缢死亡后,她就再也无法耍往日的威风,而是“拢了拢头,坎上个鬏髻,穿着领家常半新不旧的生纱衫子,拖拉着一条旧月白罗裙,拉拉着两只旧鞋” [4]426,一副风光不再,大势已去的模样。由于人的地位常常与穿戴相关,华丽体面的服饰正是珍哥在计氏面前、在丫头仆妇面前耀武扬威的战甲。然而逼死正妻将受到的惩罚使她再也无心服饰容貌的整理与修饰,作为悍妇的凶恶姿态也一扫而光。
由此可见,《醒世姻缘传》中女性泼悍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是丈夫的维护与纵容,她们本身并无任何权力,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资本,因而当丈夫这层庇佑受到威胁,有失效的可能性时,女性面对礼与法的脆弱就会显现出来。
三、服饰描写与家庭地位的争夺
在以“礼”治国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服饰也深受礼教制度影响,需要区分贵贱亲疏。明朝初期为了恢复礼制,防止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朱元璋致力于制定冠服制度。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饰制度逐渐失控,即使是下层社会的人们也喜好奢华。《醒世姻缘传》中妻妾地位的失序状况极其严重,因而泼妇在争夺家庭地位时,总是用尽各种泼悍手段,妾室只要受宠就能获得比正妻更優越的待遇,这一点同样通过对人物服饰形貌的描写表现了出来。
(一)妻妾之间的服饰对比
为了防止家庭混乱,人伦纲常失序,妻与妾地位的不同透过服饰的差异就能明显表现出来。陈宝良在他的《正侧之别: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一文中指出,“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只有正妻方可接受朝廷的封赠,成为诰命夫人,而妾则根本享受不到这种权利。这就已从根本上决定了妻妾之间服饰的差异。”[6]128
因而在《醒世姻缘传》中,计氏作为晁源的正妻,与妾室珍哥服饰的穿戴对比是很有意味的。小说第8回对计氏衣着的描写是“蓬松了头,上穿着一件旧天蓝纱衫,里边衬了一件小黄生绢衫,下面穿一条旧白软纱裙……”[4]67
珍哥作为妾室,地位本该远远不及计氏,但她拜见公婆时,穿的是“大红通袖衫儿”和“白绫顾绣连裙”,戴了满头珠翠首饰。很显然,由于晚明奢靡之风盛行,士商阶层服饰的僭越现象已十分普遍,于是在丈夫无底线的偏爱下,本只是为娱情而用的妾室,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明媒正娶的妻。
再来看薛素姐与童寄姐之间的服饰对比。薛素姐出嫁时所穿的婚服是“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童寄姐出嫁的穿着是“大红纻丝麒麟通袖袍儿,素光银带”,还盖着“文王百子锦袱”,被四人大轿迎娶进门,狄希陈援纳中书以后给她做的大衣霞帔更是明代作为正妻的诰命夫人才能享受的规格。童寄姐虽然是嫁给狄希陈做妾,但无论是结婚时的排场,还是婚后享受的待遇,都与素姐这个正妻不相上下。甚至素姐容貌被毁之后追来四川,受到狄希陈新组建家庭的一致对抗,她却因为寄姐替自己做衣裳而高兴不已,越发忘了那被打的羞辱,妻与妾的地位好似颠倒过来一般。
(二)服饰描写表现的妻妾斗争
古代的婚姻制度中,妾的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与婢相差无几,男性娶妻要求门当户对,需要妻子持家和延续香火,但纳妾主要还是贪图美色,受制于情欲,因而如前文所述,妾室的命运完全是由丈夫宠爱与否决定。正妻虽然在法律和礼制层面上都有绝对高于妾的地位,但在世俗生活中,丈夫很有可能贪恋美色冷落正妻,导致正妻对妾室的嫉妒,妾室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窥视正妻的位置,妻妾的斗争难以停止。
在《醒世姻缘传》中,男性常常会送衣裳饰物博取女性的欢心,如第6回晁源将珍哥安置在京中,年节时“自头上以至脚下”无一不备;第56回中狄希陈从京中回家,与素姐久别重逢,送了一大堆裙袄、首帕、宝石等物件放在素姐面前“进贡”。男性对女性身上强烈的性吸引力渴求不已,于是以华美的服饰去讨好她们,而这些衣饰对于女性来说,代表了金钱和丈夫的宠爱,与她们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必须要你争我夺。
小珍哥是晁源以八百两银子买得的美妾,晁源一直许诺要休弃计氏,扶她为正。珍哥对自己“姨娘”的身份十分不满,小说第8回她为了晁夫人捎给计氏的珠宝衣物撒泼不止,但她心中所愤恨的绝不仅是计氏所得的一点衣裳财物,而是这些物件所代表的公婆对计氏这个正妻的重视,她怨恨公婆肯定了计氏的地位,相比之下,珍哥拜见公婆所得的二钱拜钱就少得可怜。计氏去世后,晁家一个亲戚孔举人家办丧事,珍哥更是穿戴齐整,前呼后拥,打扮得如同神仙一样前去吊孝。珍哥如此讲究服饰与排场,也是希望借由服饰的光鲜彰显自己的地位,渴望得到正妻的待遇。事与愿违的是,孔举人的娘子对她的态度十分勉强冷淡,相反对穿戴不如珍哥的箫乡宦夫人礼遇有加,这等于将珍哥的自得与希望彻底踩碎。
由此可见,妾室虽然可以依靠丈夫的宠爱,获得比正妻更好的物质待遇,但实际的地位依旧无法受人认可,巨大的落差之下,嫉恨的情绪和凶悍的行为就更加难以避免。
四、结语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服饰描写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密不可分,透过服饰,读者能够分辨人物的地位,探析人物的性格以至于内心。《醒世姻缘传》中描写服饰的笔墨格外精巧,不单是对泼妇衣着饰品的简单描摹,通常还为了展示泼妇的性格气质,体现她们境遇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服饰成为了行文的线索,有助于推进情节的发展,甚至泼妇们嫉妒、行悍的导火索也常常与服饰有关。纵观全文,西周生以大量的服饰描寫,展现了明代中后期士民的世俗生活,塑造出一批别具特色的泼妇群像,同时还生动地呈现出晚明时期一幅“阴盛阳衰”的社会图景。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北京:外文出版社,193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美)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王维东,杨彩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
[6]陈宝良.正侧之别: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J].中国史研究,2008,(03).
作者简介:
李聪颖,女,汉族,江苏南通人,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