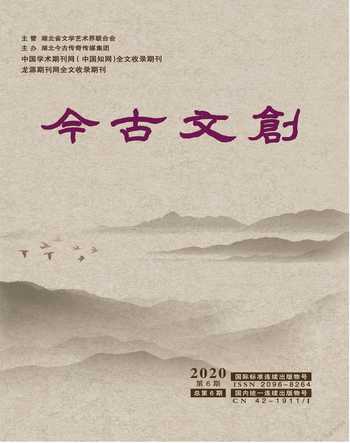《地下室手记》与《堕落》主人公形象之比较分析
【摘要】 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堕落》明显受到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的影响,包括在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地下室手记》和《堕落》主人公都缺乏传统的英雄品格、自我不稳定且精神分裂、困境之中自暴自弃式的反抗堕入了更深的深渊,他们属于反英雄人物形象,虽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却有很多相同之处,而又不完全相同,本文对两篇小说中的两个反英雄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地下室手记》;《堕落》;反英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6-0033-03
《地下室手记》(1864)和《堕落》(1956)分别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作家加缪最难懂的中篇小说,两篇小说问世以来,因其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形式的独特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和阐释,褒贬不一,具有很大的争议。两篇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也因为各自的独特个性成了经典的文学人物形象,引发了学术界不同的认识和思考。
“反英雄”一词出现之前,首先存在的是“英雄”一词,英雄可谓早已有之,人类出现之初,就有了英雄,例如,古希腊的神话英雄、中世纪的骑士英雄、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杀富济贫的草莽英雄等等,这些英雄代表了人类的勇气、力量和道德。人类需要英雄,人类创造英雄,人类也崇拜英雄。那么“反英雄”呢?“小说里应当有英雄,可这里却故意收集了反英雄的所有特点。”[1]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原文,据说,这也是“反英雄”一词在文学作品中的最早使用[2]。“反英雄”显然与英雄不同,而是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反英雄”不像传统英雄一样具有高贵的出身、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过人的胆识、英勇的气概、卓越的才能、开拓的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是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既没有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也缺乏崇高远大的目标,更不具备强大的意志和力量;他们经常性格孤僻、古怪、忧郁,或者精神分裂,甚至常常显得荒诞可笑;他们面对眼前的困难、困境,往往表现出屈从命运、怀疑自我、犹豫不决、胆小怕事、退缩不前的性格特征。但“反英雄”毕竟不是普通人,他们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诸如这类手记作者那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社会里不但可能,而且必然大有人在。我想在读者面前描绘消逝不久的那个时代中的一个人物。他是至今还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3]这“一代人”指的正是出生于俄国20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这一代知识分子40岁时,俄国正处于时代社会动荡、思想观念混乱之际,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至今还活着”的他们,与那个时代和社会一样,思想充满各种矛盾、情绪也常常悲观失望。生活在《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正是这“至今还活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也与这些知识分子同样思想矛盾、悲观失望,只不过他更加头脑聪明、思想敏锐、认识深刻,正是这些突出的特征,让他成了一个“反英雄”。
加缪曾说,《堕落》记录了那个时代纵横交错、繁复庞杂的思想,他在《堕落》的写作中提道:“的确这是一幅画像,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的画像。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全部缺点的总结。”[4]他还在1956年为《堕落》提出过一个标题叫《当代英雄》,从中可见小说主人公克拉芒斯的“英雄”性。克拉芒斯这幅“画像”,是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克拉芒斯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生于一戰前后,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50年代,他们同样40岁,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动摇了,爱和正义一时都好像不见了,处处可见的是暴力、杀戮、谎言、背叛。作为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克拉芒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态度,滋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进行了大胆的暴露和深刻的批判,他是“当代英雄”,但是一个“反英雄”。
从《地下室手记》和《堕落》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身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地下室人”和克拉芒斯两个反英雄竟如此相似。
一、与传统英雄相反的“反英雄”性格特征
一般来说,高贵的出身、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过人的胆识、英勇的气概、卓越的才能、开拓的精神等优秀品质,是传统的英雄品格。而“地下室人”和克拉芒斯则表现出相反的性格特征:自我怀疑、自卑不堪、懒惰自私、欺软怕硬、懦弱无能、卑鄙放荡、纵欲堕落、好虚荣、常撒谎、胆子小、私心重等等。
活到40岁了,“地下室人”一直住在城市的边缘,而且还是在一个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这样做的目的,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方便他躲开全人类,看起来他喜好孤独,但是人毕竟离不开社会,“地下室人”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只能通过地下室的缝隙,偷听着外边人们的那些谈话。他的生活杂乱不堪、没有头绪,一个人形单影只、毫无生气,常常沉迷于幻想中不可自拔。他是一个懒惰的人,还喜欢撒谎欺骗别人。他居然可以忍着牙疼,不去治疗,而是去体会疼痛带来的“乐趣”,这简直就是自我虐待。有时,他一人寂寞无聊,于是趁着夜色昏暗,偷偷跑到堕落腐化的场所,去干一些猥琐、卑鄙、下流的事情,但是他胆小怕事、虚荣心强,害怕被别人看见了说三道四、印象不好,所以总会费尽心机挑选“黑咕隆咚”之地出入。然而这些都是他自作多情,因为周围的人眼睛里压根儿就没出现过他的影子,他于别人而言,如同草芥,好似苍蝇,属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一类,他有时自己其实心里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长此以往,他也“承认自己是老鼠而不是人”,既然如此,他只能选择关起地下室的门,独自一人,痛苦地咀嚼着遭受的那些辱骂和嘲笑,就像感受牙痛一般。可是他自己也从不“正眼看人”,常常“侧目而视”,不“宽恕别人”,还给人下了定义,说人是“两条腿的、忘恩负义的生物”。他有自卑心理,总觉得周围人的眼睛投来的都是厌恶的光,他经常这样自我怀疑,于是自己心里都讨厌起自己来了。他有时脸皮也厚,没受到邀请就跑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自然遭受蔑视,碰了一鼻子灰,他心里虽不服气,但却懦弱无能,只能在自己憎恨的人面前“低下眼睛”,还带着“病态的恐惧”,阿谀逢迎地向对手妥协道歉,可是他也喜欢转移痛苦、欺负弱者,最终将自己心中的怨气发泄到更弱的人身上,无辜的妓女莉扎成了替罪羊。
克拉芒斯原是巴黎一律师,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畔,做起了“法官—忏悔者”的营生。他虚荣心强,喜欢自我欣赏,擅长自己夸自己、吹自己,说起话来就是“我呀,我呀,我……”滔滔不绝好似话痨,全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满嘴说的都是关于自己的利益,只有自己是最重要的,除了自己,其他一切他都觉得无所谓,他曾在集中营喝了一个垂死伙伴的救命之水,自私自利的特征在他身上一览无余。他不当“演员”简直可惜,因为她喜欢表演,甚至把表演当成了癖好,尤其喜欢在女人面前表演,因此,逢场作戏、玩弄女人就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为了勾引朋友之妻,他可以不择手段,与朋友提前断交,只为息事宁人,一旦得到她们,征服发泄一番后便抛弃了,他并不会就此收心,依然会跑去风花雪月之地继续他的放荡纵欲生活。他有很强的权利欲,喜欢掌控一切,在压迫别人、操控别人的过程中,他能够体验到幸福,他喜欢这种感觉。他虽然是个男人,但是胆子小、很懦弱,大街上遭人狠揍毒打却一点儿也不敢还手,他品行卑劣、欺软怕硬,喜欢蔑视他人,尤其是弱小伤残人士,比如,向盲人吐口水,算计着通过对推车放气的手段来欺侮残疾人,侮辱咒骂下苦的工人是肮脏的穷鬼,他甚至还荒唐卑鄙地钻进地铁打婴儿耳光。有一次,他走夜路,过桥时遇到女子落水,没施救没报警,转头离开。
二、自我不稳定且精神分裂
由于在异化的困境面前无法把握自我,加之人的本能要求与社会原则发生冲突时造成的矛盾分裂,反英雄总是处于精神分裂、性格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他们既是受害者或被凌辱的对象,又作为迫害者去欺凌别人;他们时而很高尚,时而又充满卑鄙的欲望;他们憎恨社会的丑恶,满怀抗争热情,却又缺乏勇气和胆量,逃避退让,苟且偷生;他们一半是斗士,一半是小丑,既是天使,又是野兽[5]。
我们先来看看“地下室人”的自我分裂。他一开始就自我贬低,说自己“有病”,或许想以可怜之姿换取同情之心,可是他的自尊心、虚荣心作祟,觉得这样很没有面子,别人会看不起他,于是又说自己“凶狠”,紧接着又自我辩解说自己其实并不是“好发狠”的人。他刚刚还夸赞地下室是个好地方,对他有好处,甚至高呼“地下室万岁”,但是他又担心别人耻笑他,于是乎,他又说自己没说实话,其实地下室并不好,并不是他渴望、期盼的,与他实际追求的事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转眼便发出了“让地下室见鬼去吧”的豪言壮语。可见,前后自相矛盾,恰似胡言乱语。自我不稳定、精神分裂的反常态状态,是反英雄“地下室人”的常态。对他来说,矛与盾、是与否、他与我这些相对的相反的因素,随时转换、变幻无常。以至于他自己有时都无法稳定地界定自己,“既不凶狠,也不善良,既非小人,也非君子,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爬虫。”[6]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却被人蔑视而得不到尊敬,他遭人鄙视也鄙视他人,但是他自己倒是习得了一套类似精神胜利法的本领,能够将屈辱、痛苦转化为快乐。他的意识与行动也会严重背离,可以意识到美,行动却做不到美,可以意识到反击,行动却身不由己转变成了阿谀逢迎胆小退缩,明明也同情她,行动却还是凌辱她。
而克拉芒斯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就显得比较明确,他说人有两副面孔,表里不一。他的实际行动也正是展示了他的这种看法。表面上,他的面孔是这样的:他为孤儿寡妇免费辩护,帮助盲人过马路,从不要穷人付律师费,“始终喜欢为路人咨询,为他们点燃香烟,推一把沉甸甸的货车,为‘抛锚’的汽车助力,买一份‘救世军’女郎手中的报纸或卖花老太太的一束鲜花。”[7]其实这些事都是他打心底里所不情愿的,之所以這样做,目的是为了哗众取宠满足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因此背地里,他的面孔又是这样的:欺负盲人,玩弄女人,蔑视他人,欺侮辱骂弱小伤残,面带微笑奴役他人等等。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的“谦虚”只是为了让自己“出风头”,连“自卑”都被他用来帮助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取胜”,“和平”只是他用来“打仗”的手段,“大公无私”也成了“满足私欲”的帮凶,而“德行”这样高尚的品质到他那里都被当成“欺压”他人的幌子,他是一个“转化”的“高手”。克拉芒斯就是这样一个“两面人”,他因过失受到良心的自我谴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可以算得上是受害的人,但是他为了逃脱自己遭受的痛苦而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转而又打着“忏悔”的旗号,对别人进行所谓的“审判”,这样,他自己又诡计多端地变成了进行迫害的人。
三、困境中自暴自弃式的反抗
“反英雄”也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然而反英雄与他们周边的一切是格格不入的、不协调的,他们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始终与周围的环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与之形成对抗关系,这使得他们常常身处困境之中受到伤害,成为牺牲品,但是反英雄并不会一直默默承受这一切痛苦和伤害,他们也想方设法竭力冲破牢笼,想呼吸新鲜空气,获得自由,可是他们选择的反抗方式是那样消极、极端、不择手段,注定不能成功,反而将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然而他们在主观上从没有屈服。“地下室人”和克拉芒斯正是这样的“反英雄”,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像“局外人”一样,有时甚至成为社会的公敌,于是他们进行自暴自弃式的反抗,结果只是堕入了更深的深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地下室手记》时说:“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8]“地下室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腐化和堕落,有尖锐的洞察,也萌生了反抗情绪,还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他自己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摆脱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因此用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标准反抗资本主义的文明自身,这样地放抗,本身就存在悖论。正如《地下室手记》中描写的那样,在受到军官、同事以及他的同学等人的蔑视和侮辱后,“地下室人”很想报复却又懦弱胆小,只能将所有的怨恨、痛苦,通过卑鄙、下流的方式,邪恶地、野蛮地强加到弱者身上,让无辜的妓女承受一切,他自己则猥琐地逃入黑暗阴湿的地下室,以为这样便完成了他的报复,抵抗了那个他极为不满、甚至厌恶的世界,可是这明明是逃避,是失败,是痛苦的转移,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是一种妥协式的反抗,如同助纣为虐。
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是大屠杀、大清洗、血腥、暴力、罪恶,遭受了战争的摧残,战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动摇了,社会缺乏爱和正义,暴力、谎言、背叛依然随处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知识分子腐朽堕落,克拉芒斯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控诉和批判。但是作为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并不能摆脱他所处的环境和他自己的命运,所以在认识到这一切包括自身的罪恶后,他精心策划了对抗方式,但这种方式是荒唐的,他以 “法官—忏悔者”的姿态,通过忏悔来审判别人。正如加缪所说:“《堕落》中的男主人公沉湎于精心设计的忏悔中,他来到阿姆斯特丹避难……他无法忍受被别人评判。因此,他急于作自我批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审判别人。他最终将审视自己的镜子对准别人。”[9]克拉芒斯逃亡在外,企图把自己犯的错以及自身的缺点,扩大至所有人身上,他想要的是所有人都与他一样“黑”,想以此逃避自己良心的不安,好一场精心设计的诡计,但或许出乎意料的是,以“堕落”反抗堕落的时代,反而将自己推向了更加可怕的深渊。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对加缪《堕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来看尤其明显。克拉芒斯与“地下室人”具有几乎相同的反英雄特征,他們都缺乏传统的英雄品格、自我不稳定且精神分裂、困境之中自暴自弃式的反抗堕入了更深的深渊。但是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他们也各具特点,“反英雄性”在克拉芒斯身上得到了发展,他的自我认识、反抗意识加强了。“地下室人”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感到难受和不适,一度陷入深刻反思不可自拔,至于他所进行的反抗,除揭露、批判之外,就是效仿他极其厌恶之人做卑劣下流之事,因而可以认为“地下室人”的反抗是一种无意识的,可称之为反抗的萌芽。相比于“地下室人”的反抗,克拉芒斯的反抗则更具有“反英雄性”,他更为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所以他的反抗更明确,于是他给所有人布下了一个罗网、一个陷阱,即“镜子游戏”,即使最终他自己也难逃罗网,但克拉芒斯的反抗更加主动、顽强、张扬、叛逆,无论反抗意识,还是反抗力度,都强于“地下室人”。
参考文献:
[1][3][6]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
[2]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2.
[4][9]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M].肖云上,陈良明等译.广西:漓江出版社,1999:614,615.
[5]参见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J].当代外国文学,1995,(1).
[7]加缪.堕落[M].丁世中译,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2.
作者简介:
张建祥(1985-),男,甘肃陇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职业教育、思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