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危机
罗宏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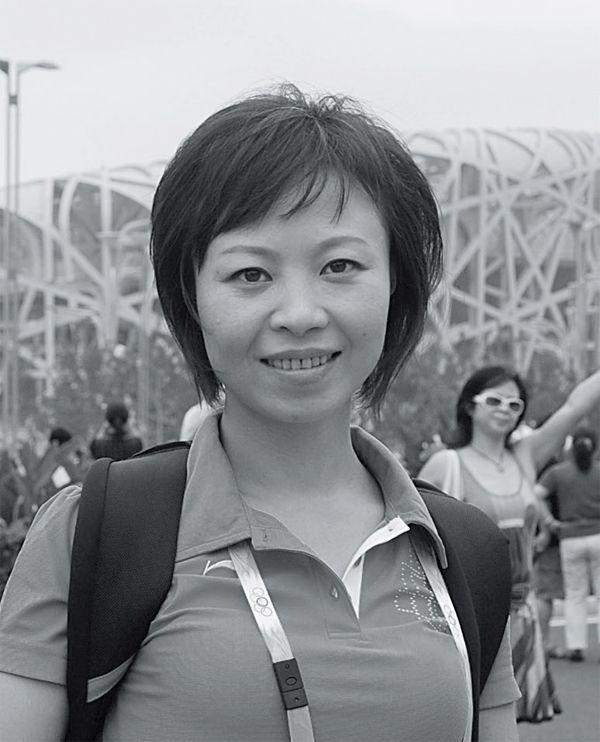
倘若没有疫情,7月的东京本该是全球体育精英及世界各地媒体人员汇聚,奥运标志缤纷街头,体育场馆观众云集,志愿者笑容洋溢,游客与市民熙熙攘攘……此时,这样的盛景只能存在于想象,或存放于对未来的希冀之中。现实的情状是,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之外,全球疫情仍旧波澜汹涌,拐点之日还遥遥无期。如此情势之下,东京奥运尽管已延后一年,其前景还是让人忧心忡忡。
国际奥委会120多年历史上首次以视频方式召开全会。其问,东京奥运会赛程正式公布;曾任日本首相的東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表示:奥运会不可能取消,东京奥组委有充分信心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对焦虑东京奥运前景的人们来说,明确而肯定的表态会安心不少,尤其对那些疫情之下苦苦坚持的运动员来说,更会是一剂安慰。
但疫情的未来走向仍是迷雾重重,国际政治的博弈也因疫情变得更加复杂。在这场说不清何时才可平息的狂风巨浪面前,尽管国际奥委会和它领导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称得上是一艘巨轮,但要平稳航行少受损伤也绝非易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组织对危机并不陌生,有几次已威胁到根本,甚而引发存亡之虞。
二战之后,奥运会的参赛人数和项目数量持续增加,不断膨胀的规模让举办奥运会的成本急剧上升,令东道主城市难堪重负。197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公民投票,反对为丹佛市举办4年后的冬奥会提供资金支持,致使丹佛不得不放弃先前费心费力争来的举办权。国际奥委会紧急寻找下家,先是找到了加拿大的惠斯勒,但被拒绝,最终,举办过1964年冬奥会、场地设施齐备的奥地利城市因斯布鲁克同意接办,这才解了燃眉之急。1976年的夏奥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该市因此债台高筑,后来过了很多年还债的日子。这一阶段,国际奥委会自身的财政状况也岌岌可危,其资产一度只剩下200万美元。花费巨大却缺乏挣钱渠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极大影响到申办意愿。1978年,当国际奥委会确定1984年夏奥会举办权时,只有一个城市申办。萨马兰奇1980年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大刀阔斧改革沿袭已久的模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引入商业开发并成功实现盈利,奥运会因此重现申办热潮。通过TOP计划、转播权出售、特许商品授权等方式,国际奥委会逐渐累积起巨大财富。
上世纪70年代的财政危机,以及90年代末盐湖城贿选丑闻引发的信任危机,终归都能够通过国际奥委会内部机制的改革“升级”化险为夷,而另一些危机却远非他们的努力能够化解。最典型的便是1976到1984年连续三届夏奥会发生的大规模政治抵制。
1970年,国际奥委会将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除名,禁止会员与南非的体育交往。但是,新西兰橄榄球队在1976年赴南非访问比赛,蒙特利尔奥组委邀请新西兰参加奥运会,引起非洲国家强烈不满,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抵制了那届奥运会。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第二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包括美国、中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在内的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抵制。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遭遇了以苏联为首的“报复性”抵制,18个国家缺席。接下来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抵制规模大大缩小,只有朝鲜和古巴两国,但另有5个国家因为资金等问题没有派出代表团。
如今,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大疫”与剑拔弩张的国际政治博弈叠加,其复杂性甚或超过冷战时期。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坦言体育和奥运会面临被政治化风险,并反思当年的政治抵制事件。未雨绸缪也好,话中有话也好,忧虑显而易见。危局之下,如何彰显奥林匹克运动促进沟通、弥合鸿沟、增进共识、推动团结等难以取代的特殊作用,考验着巴赫先生及其同事们的智慧。东京奥运会倘能如期且平稳举行,无疑就是最大成果。国际奥委会已备出多套方案,包括中国在内不少国家重启赛事的实践,也会给奥运赛事组织积攒下经验。尽管未来的300多天依然被不确定性所笼罩,人们还是有理由多一份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