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市井传奇
戴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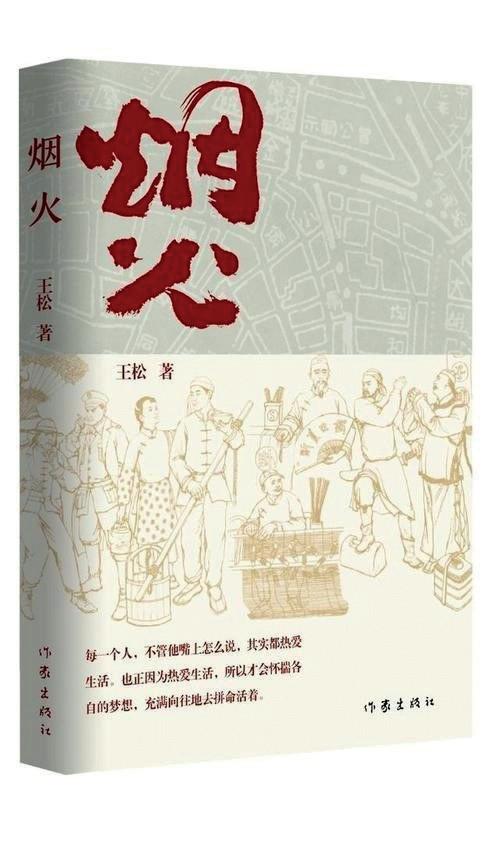
烟火作者: 王松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出版年: 2020-6
也许,作家都是属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比如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池莉的武汉、王安忆的上海。在地域写作中,“京味小说”和“海派文学”无疑是个中翘楚,且早已开枝散叶、蔚然成风。从《四世同堂》到《动物凶猛》,从《倾城之恋》到《繁花》,一个写尽四九城与大杂院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一个满是百乐门与城隍庙灯红酒绿却又充斥孤独卑微的爱恨纠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冯骥才为首的天津作家开始倡导“津味小说”,代表作品有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林希的《高买》等。而何谓“津味小说”,并不像前两者那样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陆码头无数,华洋五方杂处,百余年间随国脉兴衰风雨飘摇。可以说,天津最不缺的就是诸般人物和传奇故事,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学土壤亟待发掘。
在完成《烟火》之前,作为天津作家,著作等身的王松似乎并没有认真打量过自己的城市,创作的津味小说并不算多。王松非常善于讲故事,笔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尤其是在讲述另类的知青故事方面独具一格。姑且不论他几百万字的其他作品,仅就《双驴记》《葵花引》《红汞》《哭麦》等“后知青小说”的成就,就足以让他跻身当代作家的第一方队,他的这些作品改写了一个时代的“知青文学”。谈到这次《烟火》的创作契机,王松觉得每个作家写一部小说都有其宿命,什么时候写什么题材,这也是宿命。“大概是冥冥之中,或潜意识中的事,觉得该为这个城市写点什么了”。
王松是热爱天津的,尤其是弥漫在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不过他也直言,要写天津并不容易,因为天津的文化很难一言以蔽之,“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拼图”。很多人都会说天津是码头文化、殖民文化、漕运文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可再一细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对。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地方,一百个人看天津会有一百种看法,也有一百种说法,这就是天津真正的特质所在。而王松想要寻找的,却是那第一百零一种看法和说法。
在创作《烟火》的过程中,王松天天背着水和面包,跑遍了天津的大小博物馆和当年的老城北门外。在王松看来,作家是必须深入生活的,“看文字资料和照片,和看实物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跑博物馆,就是想看一看实物,比如当年的鞋帽店,门口挂的招幌儿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皂靴的形状;再比如当年柜台上用的算盘,足有两米多长,能几个人同时用。这些东西至今还带着当年的烟火气,只要你用心观察,便一定能感受得到。王松感受到了,不仅如此,他还想让读者同他一起感受到。王松的小说没有文人式的伤感和矫情,更多的是带有一个数学专业出身的作家所特有的爽利劲儿,叙事干脆利落,线索清晰,逻辑性强。而《烟火》却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读完使人眼前一亮,感觉这才是属于作者自己的题材。王松虽然在京津冀之间游走,根基还是在津门。天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是王松最为熟悉的。因此,他的笔一落到天津的街道上,就变得摇曳多姿、声情并茂起来。那个醉心于故事、讲究叙事速度、素以理性著称的王松,笔端也不免带了些许文人式的悲悯和伤感,故事情节的进展也跟着缓慢了下来。
小说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余年。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然而,《烟火》写的是天津,却从老城北门外一条叫“侯家后”的胡同展开的。“侯家后”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地处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三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俗语说,“先有侯家后,后有天津卫”。可以说,这里便是天津的历史文化缩影。侯家后“大胡同套着小胡同,宽街窄巷密密麻麻”,不仅仅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也很优越,靠水路连接着富庶的南方,也连接着浩瀚的海洋。小说的开端,引用了清代查曦的《登篆水楼》中的一句诗:“最见津门繁盛处,双桥雨水万家烟。”因为漕运的缘故,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诞生了许多老字号商铺,狗不理包子铺就从这里名扬天下。
严格来说,侯家后并不是一条胡同,而是一片不大的区域,书中的重头戏就发生在里面的“蜡头儿胡同”里。《烟火》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晚清末年至新世纪,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辛亥天津起义、“壬子兵变”、老西开教堂事件、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这些历史事件,在小说里并不是正面表现,而是作为背景来映衬小说中的人物,王松始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笔墨,尽量不让胡同之外的历史风云过于直接地卷到胡同里来。但在小说人物的命运背后,却始终映现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蜡头儿胡同”原本叫“海山胡同”,一条窄窄的胡同,却能够连着山、接着海,简直可以通达天下,这正是《烟火》所写出的天津城与天津人的宏大气魄。
王松具有编织故事的强大能力,他以高掌柜的狗不理包子铺为据点,人来人往之间,将侯家后的诸多店铺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学地理图景。胡同里住的大都是手艺人,有卖拔火罐儿的老瘪、卖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打帘子的马六儿、卖帽子的杨灯罩儿、绱鞋的老朱、拉胶皮的保三儿、玩石锁的刘大头、卖神祃儿的尚先生等。在王松的文字里,读者能看到老瘪卖的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知道拉胶皮光有一膀子力气还不够,鸡毛掸子也有好坏之分,打帘子还有各种讲究,从人人熟知的狗不理,到鞋帽铺、棺材铺、水铺,嘎巴菜、豆腐丝儿……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汇聚于此,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而这也正是老天津的魂魄所在。
如果说俗白、凝练、纯净是“京味小说”的特色,那么“津味小说”一定离不开曲艺文化的浸润,尤其是相声。王松曾写过许多相声小品,马三立及其弟子都用过他的本子,小说最令人称道之处,正在于作者将自己写相声的经验融入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口语化的叙事之中,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开拓,也展现了天津人的独特表达方式和生存智慧。而且小说加上序言共有六部分,标题分别是垫话儿、入头、肉里噱、瓤子、外插花、正底,用的都是相聲术语,这样一来,就使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相声的质地,干净利落,活泼俏皮,读来宛如欣赏一出连轴出演的相声,津津有味,叫好连连。
《烟火》的故事密度在长篇小说里是极其罕见的。在百余年的时间跨度里,百余位出场人物的故事在一条胡同里渐次展开,每一个人物都自成章节,都可以沿着时间的脉络探向另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角落。王松大量采取插叙与补叙的手法,在保证故事主线不受干扰、始终保持固有节奏娓娓道来的前提下,得到了很好的补益与充实。正因为这些穿插的故事和人物细节,小说的架构更加丰盈茂盛,时代和人文气息更为浓烈动人,作者的真实意图伏脉千里又并不刻意生硬。在这方面,王松似乎并不吝惜笔墨,小说的更多的“舍”,其实埋在了它的“不舍”之后。
读完掩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作者对这部小说命名的用意。“烟火”指向的当然是市井与民间,在王松看来,正是在嘈杂而丰厚的民间市井生活里,才埋藏着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民族最为重要的根本;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胡同”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重要的不仅是广阔空间里一时的风云变化,而是在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那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