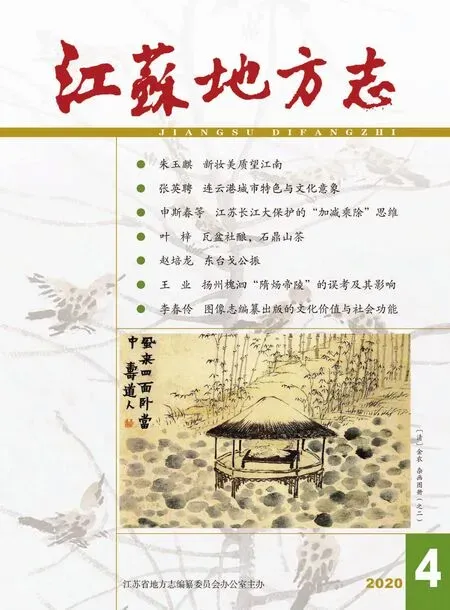图像志编纂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 李春伶
(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北京100717)
提 要:图像志是图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图像志(人物和地理)编纂出版实践,重点阐述图像志出现的背景、发展趋势、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认为,图像志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学术发展背景。图像志的编纂出版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记忆保存需求的基础上,还承担着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功能。当今方志编纂中应有意识地编纂图像志,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方志工作“活起来”。
如果说,以图像作为主要材料与呈现方式是美术、雕塑、工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艺术领域的基本方法,那么,以图像呈现族群和社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则是影视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图像史学,是以图像为主要史料与独特呈现方式,以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的新兴学问,是历史学人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与使用可视材料的新尝试。近20年来,图像史学在中国开始萌发,很快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1]作为图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像志正是通过对上述主要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地记载,从一种新的不同的视角还原再现地方历史,丰富、开拓中国地方志、社会史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这一新领域很有前景,大有可为。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在宋代方志体例定型之前,方志曾经历了从早期地记到图经的演变。所谓图经,就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又称图志、图记。宋代以后,志书逐渐演变成以文字记述为主、图像为辅的形态。进入近代社会后,图片影像资料大量出现,以图像记录历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近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图像资料的丰厚和史志图书编纂的需要,图片甚至可以从书中插图位置发展到单独辑册编纂出版的水平,以致以图像为主的图像志再度成为方志的新品类。图像志为什么出现?这类志书的编纂出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图像志的编纂出版具有哪些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笔者结合图像志的编纂出版实践进行分析。
一、图像志再度成为方志的新品类
方志编纂出版工作要发挥存史、资政和育人的社会功能,把最好的历史文化产品奉献给人民。近十几年来,以人物老照片和老旧地图为主题的图像志的出版悄然兴起,成为方志出版的一个新品类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品类的特点在于:(1)图像记录仅关乎某一特定地区特有人物或地理的变迁;(2)摄影、印刷等技术的发明与传播在图像志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人物照片为主题的,如李润波主编的《平谷老照片——一个时代的记忆》(科学出版社,2018年)。该书作为北京市平谷区第一部人物图像志,乡土气息浓厚。作者从5000幅左右的收藏品中甄选了800幅老照片,记录了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平谷人的生活变迁,为读者留存一份关于北京乡村生活的凝重厚实的集体记忆。该书采用8开画册的装帧设计风格,以图为主,辅以文字。按照片的主题和拍摄年代,该书共分镁光初闪、岁月留痕、怀旧经典、风采当年和校园记忆五个部分,从不同侧面重构了平谷社会各界参与创造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岁月痕迹。翻开图书,映入眼帘的是农民、工人、干部、教师、学生、孩子、老人,或田间,或工地,或讲台;或院内,或室内;或学习,或琢磨,或劳作;或端坐,或站立;或华服,或便服;或集体,或个人;或全家,或三五好友,或与爱人;或蹙眉,或微笑;或得意,或失意……都在镁光闪现的一瞬间留下永恒的历史记忆。以地图为主题的,如孙逊、钟翀主编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该书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以丰富的上海历史地图资源受到学界的关注。该书编纂历时五年,汇集了与上海相关的古代舆图与近现代地图217种(上起于1504年,下迄于1949年),跨越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大体展现了上海城市古旧地图的全貌。该书的217种地图中主图196种、附图21种,包括地图分图,以及封套、地图背面的各种地图附件等图像资料,计近400幅,图像资源可谓丰厚。该书是大8开(对折4开)的精印之作,间或有大比例尺的拉页大图三折于其中,每每打开折页,除给读者以整体的强烈视觉冲击外,还给读者某种程度上探宝的感觉。该书印制装帧非常讲究,精装彩印,裸背锁线,带函套。加之该书内容资源独特珍稀,汇集了近5个世纪以来的上海城市地图资源,全面反映了此类地图的演化脉络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堪称城市地图集中的经典之作。
二、图像志编纂出版的背景与发展趋势
图像志作为一类志书,再度成为方志的新品类与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过程紧密相关,与摄影技术、地图测绘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传播密切相关。
(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变迁
图像志编纂出版的大背景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转型。18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的推动下全球进入工业文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胁迫下先后开放了70多个通商口岸。据曾国藩的记载,以英、法、美、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2],建立了由沿海到内地、由口岸城市到乡村集市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他们一方面从中国攫取廉价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连接原材料与市场的、以口岸城市为网络节点的贸易网络已经形成。在商品贸易的带动下,摄影术、照相机、测绘技术、印刷机器、实测地图以及相关书籍等得以在中国进行交流和传播。中国口岸城市首先出现了照相馆、摄影师、地图出版社、地图编绘人员和相关学术团体等,开始了照片和地图的制作与传播。

《平谷老照片——一个时代的记忆》
1949年以来,中国继续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轨道上前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规模和速度上也明显加大、加快,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49.28%[3]。这个恢宏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留存的文化遗产经过精炼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图像志的编纂出版由此发轫。一方面巨大体量的社会转型与工业文明发展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城市快速扩张、旧城改造升级、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事业持续升温,城市古旧地图的整理与利用也逐渐进入相关研究者的视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多地已相继出版城市古旧地图集和人物图集。
(二)摄影技术的发明与传播
作为“百闻不如一见”的表现形式,图像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以区域或机构特有的地图、人物图像作为图书的主要内容,有别于纯文字记述的地方志书。中国传统志书虽然很早就有各类舆图并插有人物画像,但这类遗存规模和制图技术水平局限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状况。19世纪30年代末,法国人路易·雅克·芒戴·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首次成功发明实用摄影术,该技术的迅速推广使照片成为有别于文字的另一种历史信息记录、储存、传递的载体,各种题材的图像史料得以大量留存。
摄影技术传到中国后得到了快速的传播。目前看到的,在中国最早拍摄的照片大约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Teren Bennett)撰写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和《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三本书。在三部摄影史著作中,贝内特对1840年以后几十位中国摄影师和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和他们拍摄的照片进行了考证,考证史料涉及当时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烟台、香港和澳门等城市。19世纪50年代,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出现照相馆,仝冰雪著《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采用丰富的图像史料记载了中国早期照相馆发展的历史。[4]具体到北京市平谷地区,20世纪20年代末,平谷人郝国基开办了第一家照相馆,从那时起这家照相馆给平谷人民拍摄的照片有40万件以上。[5]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摄影方式逐渐被数码照相机淘汰,照相馆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数码照片取代了纸版的照片。而过去150多年,大量照片的拍摄与积淀使图像志出版成为可能。
(三)地图学的发展与印刷技术的提高
如前所述,方志曾经历了从早期地记到图经的演变,中国古人在对地理环境和行政疆域进行测绘与研究的同时促进了舆图的发展,各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此类舆图。到了近代,尤其是欧洲地图测绘技术和摄影技术的发明和传入,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1898年成立的武昌亚新地学社是中国成立最早、出版地图最多的一家地图专业编绘私营机构。武昌亚新地学社开创了中国采用铜版雕刻、石印印刷技术出版中小比例尺地图的先例。著名学者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与上海中华印刷厂合作,积极引进国外测绘制图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机器,并于1930年开始编纂大比例尺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分省地图。1932年中国第一次运用航空摄影制图,这项技术使人们可以脱离地面利用高空平台来测绘地图,进而改变了人类近300年来形成的地形图测绘生产方式。[6]截至1953年,中国国内十几家私营地图出版社共编绘出版各类地图300多种,累计印行几千万册。[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了谭其骧主编的第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近年出版的各地城市地图集多以前述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图为主要内容。
除此之外,由于全球化贸易的推动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开放门户,各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沿江开放口岸城市也编绘了相当数量的地图。这些海外地图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史、文化史和方志研究重要的补充史料。
(四)图像志编纂出版的发展趋势
图像志编纂很有发展前景,大有可为。中国学者除在收藏、整理和研究图像史料等方面取得成绩之外,在图像史料的编纂出版方面也用力颇多。在人物图像志方面,1996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冯克力创办《老照片》。该书从一出版便引起学界的关注,一度创造出单辑销量三四十万册的纪录,20年下来,最高的单辑累计销量已达七八十万册,还曾掀起一股老照片出版热潮。[8]
在机构或区域图像志方面,2016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了六卷本的《江西百年图典》。该书共收录6000多张图片,180万字,可谓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了江西省百余年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历史文化风貌。2017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海宝、张争鸣编著的《显影:无锡电影胶片厂40年影像志(1958—1998)》,该书通过精选的200张照片生动地再现了无锡电影胶片厂40年的兴衰轨迹。
在以地图为主题的图像志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武汉、苏州、绍兴、青岛、桂林、澳门、温州、湖州、柳州、汕头等15个城市均已出版了城市古旧地图集。以汕头市为例,谢湜教授团队通过系统的调查与收集,共获得来自汕头本地文博与档案机构、国内知名图书馆、个人收藏家,以及英、法、美、日等国相关机构与汕头市相关的古旧地图38种(《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20年)。上起1762年,下迄1948年,这些历史地图展现了汕头城市老地图的全貌。
三、图像志编纂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价值源自需求与功能的实现。图像志编纂出版的文化价值主要源自这类志书存史、资政和育人三个方面功能的实现。换句话说,图像志的编纂出版首先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记忆保存的需要。其次,图像志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的基础材料,还承担着服务科学研究的重要功能。最后,图像志的编纂出版还具有文化记忆传承的功能。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
(一)图像存史
就地图集而言,“城市地图是城市图像文献中的重要门类,它不仅是解读城市变迁、探索地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所展现的丰富的史地元素(山川、湖泊、河流等)、人文信息(道路、港口、建筑、治所等),“乃至测绘、印刷等科技文化,以及近代以降渐至发达的都市文化与旅游内涵,大量辐射到不同学科领域,提供多元的、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重要史料信息”。[9]近年,随着城市扩建、老城改造、工业遗产园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旅游业发展、地方文化品牌建设,各地对于老旧城市地图史料的出版需求日益高涨。
就人物图集而言,摄影术的拍摄对象主要分为景物和人物,而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所以在摄影术日渐普及的前提下,人们往往通过拍照记录重要活动场面,以及群体合影和个人特写。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以人物为主的老照片在图像史料中占较大比例。将这些老照片进行收集、整理、考证、修复、保存,甄选适宜的部分编纂、出版、展览等可为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史料。
作为历史场域的影像记录附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图像志非常珍贵,其存史特点主要如下:(1)在空间维度上,以一地为限涵盖该地域特定时期疆域、道路、建筑概况,或各行业人物肖像或工作场景。(2)在时间维度上,时代跨度都较长,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史料记载了在一定时段内地理面貌的变迁,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服装服饰的变迁。(3)在内容维度上,包括自然和人文、公共和私人生活等多个方面。在自然和人文资源方面,主要记录了山川、河流、道路、城市、建筑、治所等信息;在公共生活方面,主要记录了军旅、政治、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相关的历史事件。例如《平谷老照片——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书,工农业科技推广、工厂的建设、技术的改进、平整土地、修建水库、合作社、中小学教育等在地区发生的大事,在这部图像志中都有多幅照片收录,呈现了特定时代的地区生活面貌,对人们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史,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非常有帮助。在家庭生活方面,这部图像志中收录了不少家庭的全家福和人物的肖像照,这些照片不仅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且从肖像风格和着装的变化可以揭示整个地区时代变迁的一些风貌。
(二)服务科学研究
通过对历史图像的认知,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某个时代复杂的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即所谓的以图证史,以图传史,图文互证等。
例如,1949 年10 月1日下午3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国由于当时的拍摄器材缺乏,特地请苏联摄影师一行17 人进行拍摄,后由于苏联摄影师所住宾馆存放胶片的房间起火,拍摄胶片损失殆尽。所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看到过开国大典的彩色场景,只有来自延安的记者拍摄的黑白且模糊的照片记录。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年大庆前夕,导演黄建新为拍摄《决胜时刻》曾于俄国档案馆发现记载开国大典的残缺胶片并购回。在这个基础上,中央档案馆首次公布根据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影片复原的开国大典彩色照片多幅以及档案文献200 余件,史料价值极高,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这份关键史料对于国史的研究意味着某个方向的延展。1971年11月15 日,在第26 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中被剥夺20 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席位上高兴得仰天大笑,喜悦、畅快、豪放、自信,这张照片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史料,无论文字怎样描述,都无法像这张照片那样直观、简洁、准确、生动地呈现历史的精彩瞬间。
图像志不仅存史,而且资政。在服务科学研究方面,以老旧地图集为主要内容的图像志与当下地方建设结合得更加紧密。以城市地图集为例,目前广受各地市关注的工业遗产园区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原,没有哪一项规划方案的制作不需要使用过去老旧地图的。“城市地图是城市变迁的忠实记录者。城市老旧地图集的出版,由于其在图像呈现方式上的不可替代性,无论是对城市史、城市史地、城市规划与建设、都市文化,还是就地图学史而言,都具有充分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10]这是图像史料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文化集体记忆与传承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编修史志过程,不仅完成了以史鉴今的文化传承,更形成了文化的集体记忆。图像志的编纂也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前述大量图像志多以群体的普通人图像或地图作为主题,是人民群众内生的关于文化传承和集体记忆需求的直接反映。2020年汕头市政府以《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的编纂出版纪念汕头开埠160周年、汕头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其文化集体记忆与传承意蕴深厚,都市文化品格立意高远。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变化,以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口述史、影像史、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等为主要方向的公共史学蓬勃兴起,这反映了大众对于文化记忆与传承的强烈需求,也反映了史志的书写要走向大众。[11]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关于“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先后师从柏格森和涂尔干,他融合二人的思想,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认为所有记忆都受到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和形塑。
“集体记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边界在不断扩大。不过,相关研究仍集中于遗迹、电影、博物馆、大屠杀、法国革命等近现代事件。近年来,国内民间与学界的研究也大致如此。[12]在某一主题的集体记忆方面,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在推动的科学家口述史料抢救与整理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口述史研究中心在做的以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工业化为主题的口述史料整理工作,中国传媒大学开展的以长征等为主题的口述史整理工作,等等。在学术界之外,也有大量民间力量在进行各种形式的集体记忆项目,包括中国三线建设集体记忆项目,某某行业、某某工厂的记忆项目……这些集体记忆项目,由于都发生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后,所以都存有大量的老照片,有形成图像志的基本条件,但也濒临灭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研究员认为老照片“也是亟须抢救、保护和传承的珍稀文献和记忆文化遗产,希望能一步步地得到国家相应层级的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相信老照片“以其蕴涵历史信息的丰富厚重性和历史影像的形象真实性,将会震撼不同层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并得到相应层级的关切、保护和传承、弘扬,使其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光彩”。[13]而《平谷老照片——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书首印4000余册在短时间内基本售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本地区图像志的认可。
四、结语
图像志的编纂出版是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是地方集体记忆形成和文化品格塑造的有效方式。在读图时代,图像志的出现显示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学术发展的背景,这一方式更受年轻人的喜爱。图像志的编纂出版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记忆保存需求的基础上,还承担着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功能。当今方志编纂中应有意识地加强图像志编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方志工作“活起来”。
在图像志的编纂出版过程中,需要注意史料的征集、考订、编纂、设计、出版等具体环节的处理,提高图像志的学术性和可传播性。由于篇幅所限,此点将另行撰文,故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