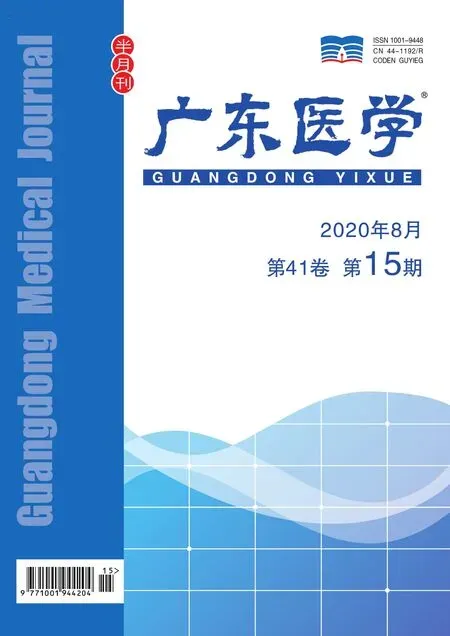布托啡诺应用于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镇痛效果和安全性多中心观察
张明, 吴明, 孟启勇, 余宝军, 施学志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清远 511500); 2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深圳 518000); 3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深圳 518000); 4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广州 510010)
疼痛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主要症状,其程度往往剧烈、令人难以承受,曾被学者描述为 “生命中最糟糕的痛”[1]。不幸的是,虽然镇痛治疗在大多数急危重症疾病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在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疗中仍被不置可否[2]。两项来自美国和法国的调查报告分别指出:多数工作者因畏惧不良反应而未给予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足够的镇痛处理[3-4]。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权威指南也因镇痛药物应于该病的直接证据不足而未对疼痛管理做出应有的阐述[5]。因此,寻找有效且安全的镇痛药物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优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布托啡诺是一种新型的阿片受体激动拮抗剂,具有不良反应少、镇痛效果强的特点,而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类危重疾病中。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它应用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是以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早期患者为研究对象的多中心、前后对照研究,目的是观察布托啡诺的镇痛效果和不良反应。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组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自身前后对照的观察研究,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间在清远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南部战区总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ICU收治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项目经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患方的知情同意。
入组标准:(1)年龄>18岁的成人;(2)CT检查确诊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发病后入住ICU并严密监控生命体征超过24 h;(4)患方同意参加研究;(5)Hunt-Hess分级Ⅱ~Ⅳ级。
排除标准:(1)有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碍;(2)经历急诊手术;(3)需机械通气;(4)除尼莫地平外,需其他静脉应用的药物以控制患者收缩压在180 mmHg以下;(5)深度昏迷,对恶性刺激无反应;(6)阿片类药物过敏;(7)观察时间内原发病不稳定需调整治疗方案。
共有60例患者同意入组,但5例患者因颅内情况、呼吸情况恶化等原因剔除,故最终纳入研究55例,其中男20例(36.4%),女35例(63.6%),年龄(55.22±8.06)岁,格拉斯哥(GCS)评分14(7,15)分,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Ⅱ(APACHEⅡ)评分(9.93±3.20)分。Hunt-Hess评分Ⅱ级的患者10例(18.2%),Ⅲ级21例(38.2%),Ⅳ级24例(43.6%)。根据患者的意识水平分层为两组,能准确表述疼痛(应答组)患者31例,不能准确表述疼痛(无应答组)24例。另外,为排除非药物因素对观察指标的影响,本研究观察了同期住院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病情,患者家属同意对患者情况进行监测和记录,但未同意接受额外的药物(布托啡诺)。对照组患者共20例,其中男6例(30.0%),女14例(70.0%),年龄(53.40±8.66)岁,APACHEⅡ评分(10.15±3.85)分,GCS评分14(7,15)分。Hunt-Hess评分Ⅱ级的患者4例(20.0%)、Ⅲ级8例(40.0%)、Ⅳ级8例(40.0%)。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策略 入组观察组的患者在试验开始的首个2 h内,适应环境、调整尼莫地平(德国拜耳公司 批号:国药准字 J20050050)剂量并被记录各项指标。再使用稀释后的布托啡诺(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批号:国药准字 H20143106)静脉微泵注入,剂量10 μg/(kg·h)。使用布托啡诺1 h后再次开始记录各项指标,时限3 h,届时试验观察结束。对照组被观察并记录了6 h的病情,以试验开始后的第4小时为分界,将观察时间定义为观察“前期(T0)”和“后期(T1)”。两组患者的观察过程在严密监护生命体征的条件下进行,且不影响其他治疗方案。
1.3 疼痛的评估 能描述疼痛程度(Hunt-Hess Ⅱ、Ⅲ级)的患者每小时被询问对疼痛的主观感受,使用“数字化评分”(NRS,0~10分)表示。对于不能描述疼痛程度的患者,参照文献中评估神志障碍患者疼痛的方法(NCS评分),根据患者是否有痛苦的肢体动作(如异常扭曲)、面部表情(如痛苦面容)、发音(如呻吟)、视觉频繁运动(频繁眼球运动)四方面取量化评分,每项0~1分,0表示未发生,1表示已发生,4项评分之和衡量患者痛苦表现程度,每小时测量1次,取平均值。
1.4 生理指标的监测 实验开始后,采用校准过的监护仪监测数据,每5 min记录1次患者的心率、平均动脉压(上臂无创血压)、呼吸频率,取时间段内的平均值。每小时测定1次动脉血氧分压(PO2)数值、乳酸等,并取平均值。
1.5 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的观察 观察可能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如呼吸抑制、低氧血症、低血压、过敏、胃肠道反应(呕吐)、寒战、死亡等,以及患者的GCS评分的变化。其中,呼吸抑制定义为用药后呼吸频率小于10次/min。低氧血症指中流量吸氧(浓度30%~50%)情况下,动脉PO2数值低于70 mmHg。低血压为平均动脉压下降超过基础水平的2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验证分布特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用药前、后或观察前、后期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疼痛程度的变化 对于能应答的患者而言,对照组T0和T1的疼痛评分未显著改变。T0时,两组N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82,P=0.766)。但是,能应答的患者NRS评分在T1显著下降了2.8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对于无法准确描述疼痛的患者而言,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该部分患者中,两组T0时疼痛程度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65,P=0.120),观察组T1时的疼痛程度亦较对照组同期程度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不同时间疼痛评分的变化 分
2.2 生命体征的变化 对照组T0和T1患者心率、呼吸未显著改变。观察组T1时,无论是应答或是无应答的患者,其心率、呼吸频率都较T0下降。另外,观察组T1时的心率、呼吸频率较对照组同时期的患者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的变化 次/min
2.3 药物的不良反应 观察组患者使用布托啡诺的3 h内,观测到与药物明确相关的血压下降4例,未见呼吸抑制、过敏、呕吐、寒战、低氧血症,用药前后患者的动脉血氧分压无显著改变。患者用药前后的GCS评分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发生血压下降的患者,3例来自意识水平障碍的患者,但未见休克的情况(如尿量减少,乳酸增高),用药前后患者的乳酸水平未见增高。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氧分压、乳酸水平
3 讨论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一种高发的急危重病,其主要病因是隐匿的动脉瘤破裂、血管畸形等,难以预防。随着影像、介入、外科技术的改进,该病的病死率仍高达45%,致残率亦居高不下。发病早期更优化的管理模式可能是提高其疗效的重要手段[6]。其中,疼痛的管理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据资料显示,约4/5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会经受严重的疼痛刺激,其主观感受强度平均高达8分(0~10分)[5],这与我们的结果相类似。此问题正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指南提到,镇痛治疗有利于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早期的病情控制[7]。但由于研究的不足、证据的匮乏,其具体的治疗方案仍未见论述。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神经重症患者在临床实践中常接受阿片类受体激动剂作为主要的镇痛药物,其具有价格便宜、镇痛效果好的特点[8]。但是,它同样存在多种不良反应,包括呼吸抑制、胃肠道功能、抽搐等。更有研究发现,该类药物的使用可能增加颅内压力,不利于脑灌注压的稳定[9],使其饱受诟病。
布托啡诺是新型的阿片类受体激动拮抗剂,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10]。本研究中,意识保留、能应答患者用药后疼痛评分显著下降,意识水平障碍、无应答的患者痛苦表现亦减少,均证实布托啡诺发挥了足够强度的镇痛效应。此外,我们还看到,镇痛后患者的应激水平降低,心率、呼吸频率均有下降,不影响气体交换。根据“隆德概念”理论推测,这有利于控制脑容量和颅内压,改善脑组织能量代谢[11]。遗憾的是,由于伦理学的要求,本研究未采取措施测量颅内压或脑代谢指标,进一步的病理生理学研究可能是必要的。
同时,布托啡诺还具有激动和拮抗双重效应,不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在本研究,未发现该药物引起的严重不良反应,包括对呼吸的影响。然而,由于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肠道功能抑制、寒战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待观察。另外,本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低血压现象发生在意识障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亚组。对于此类患者,严密监护血流动力学是必要的,更精确的血容量可能改善这种现象。
本研究采用了自身前后对照的研究方法,设计布托啡诺用药后1 h为疗效观察的起点。根据布托啡诺的“起效时间短”药理学特点,设置“短周期”是合理的;同时,该药物代谢周期短,镇静作用轻微,故不影响神志观察,对颅脑损伤的患者评估是有帮助的;使用布托啡诺以前设置了为期2 h的观察周期,有利于患者适应环境,稳定尼莫地平剂量,调节血流动力学状态。我们也看到,镇痛治疗协同尼莫地平的使用,对绝大部分患者的血压控制是有利的,并不需要过多的降压药物参与。
除了阿片类药物之外,有潜力成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镇痛药物的还有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如对乙酰氨基酚等[8]。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此类药物在神经重症患者中的效应。可惜的是,更理想的静脉注射剂型往往不容易获得[12]。此外,此类药物是否增加再出血风险也是处理蛛网膜下腔出血病程中有待观察的[13]。联合使用阿片类和非甾体药物,可能也是有效镇痛、减少不良反应的探索方向。
本研究存在难点依旧是如何评估意识水平障碍患者的疼痛程度。先进的影像学手段证实,这部分患者同样能感受到疼痛,并且伴有脑代谢方面的不良影响[14]。虽然曾有观察Hunt-HessⅡ~Ⅲ级患者疼痛的研究,但如何控制无应答患者的疼痛是历来同类研究所回避的“雷池”[15]。其原因可能是至今仍没有可靠的评分系统供量化、对比,评估此类患者是否疼痛还是需要依靠临床医生的观察评定。比较有前景的是本研究仿效的NRS评分,它是通过观察对象表情、动作来评估脑损伤患者对恶性刺激的反应性[16],但它能否用来评估镇痛药物的疗效的确还需进一步确定。在本研究中,无α受体活性的布托啡诺使得无应答患者的应激状态趋于平稳,可能从侧面验证了其对疼痛刺激的缓解作用。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这是一项观察研究,试验设计过程中未设立安慰剂,未采用随机原则,理论上可能带来偏倚。第二,本研究是一项短期研究,不能提供镇痛治疗对远期预后影响的证据。第三,从伦理学的角度上,未对患者施行颅内压监测等干预手段。因此,更严格的随机对照研究可能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