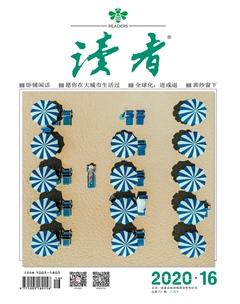马车夫
阿来

骑手的形象与人们通常想象的大相径庭。这个人身材瘦小,脸上还布满了天花留下的斑斑印迹,但他就是机村最好的骑手。
试驾马车那一天,麻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人们围成一圈,看村里的男子汉们费尽力气想把青鬃马塞进两根车辕之间,用那些复杂的绊索使它就范。这时,麻子骑着一匹马徘徊在热闹的圈子外边。这个人骑在马上,就跟长在马背上一样自在稳当。折腾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能给青鬃马套上那些复杂的绊索。青鬃马又踢又咬,让好几个想当车夫的冒失鬼都受了点小伤。
人们这才把目光转向勒马站在圈子之外的麻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脸上那些麻坑一个个红了。他抬腿跳下马背,慢慢走到青鬃马跟前。他说:“吁——”青鬃马竖起的尾巴就慢慢垂下了。他伸出手,轻拍一下青鬃马的脖子,挠了挠马正呼出滚烫气息的鼻翼,牲口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家伙,脸上带着沉溺进了某种奇异梦境的浅浅笑容,开始嘀嘀咕咕地对马说话,马就定了身,站在两根结实的车辕中间,任麻子给它套上肩轭和复杂的绊索。中辕青鬃马驾好了,边辕两匹黑马也驾好了。
人群安静下来。
麻子牵着青鬃马迈出了最初的两步。这两步,只是把套在马身上那些复杂的绊索绷紧了。麻子又领着三匹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这回,马车的车轮缓缓地转动了一点。但是,当麻子停下步子,轮子又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走啊,麻子!”人们着急了。
麻子笑了,细眼里放出锐利的亮光,他连着走了几步,轮子就转了大半圈。轮毂和轮轴互相摩擦,发出旋转的轮子必然会发出的声音:
叽——
像一只鸟有点胆怯又有点兴奋地要初试啼声,刚叫出半声就停住了。
马也竖起了耳朵,谛听身后那陌生的声音。
他又引领着马迈开了步子。
三匹马,青鬃马居中,两匹黑马分行两边,牵引着马车继续向前。转动的车轮终于发出了完整的声音:
叽——吭!
前半声小心翼翼,后半声理直气壮。
那声音如此令人振奋,三匹马不再要驭手引领,就伸长脖颈,耸起肩胛,奋力前行了。轮子连贯地转动,那声音也就响成了一串:
叽——吭!
叽——吭!叽——吭!叽——吭!
麻子从车头前闪开,在车侧紧跑几步,腾身而起,安坐在了驭手座上。他取过竖在车辕上的鞭子,凌空一抽,马车就蹿出了广场,向着村外的大道飞驰起来。
从此,一直蜗行于机村的时间也像装上了飞快旋转的车轮,转眼之间就快得像射出的箭矢。
这不,马车开动那一天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那些年里,麻子一脸坑洼里得意的红光还在闪烁,马车又要成为被淘汰的事物了,因为拖拉机出现了。拖拉机不但比马车多出四只轮子,更重要的是,一台机器顶得了许多匹马。拖拉機手得意地拍拍机器,对围观的人说:“四十匹马力。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四十匹马。”
人群里发出一声赞叹。
拖拉机手还说:“你们去问问麻子,他能不能把四十匹马一起套在马车前面?”
其实,拖拉机手早就看见麻子手勒缰绳,骑在他心爱的青鬃马上,待在人圈外面,那颇像是第一次给马车套马时的情形,但他故意要让麻子听见这话。麻子也不得不承认,拖拉机手确实够格在自己面前摆威风。不要说那机器里憋着四十匹马的劲头,光看那红光闪闪夺目的油漆,看那比马车轮大上两三倍的轮子,他心里就有些可怜自己那矮小的马车了。
拖拉机油门一开,机器的确就像憋着很大劲头一样怒吼起来。高竖在车身前的烟筒里突突地喷射出一股股浓烟,那得意劲儿就像这些年里麻子坐在行驶的马车上,手摇着鞭子,嘴里叼着烟头喷着一口口青烟时的样子。看着力大无穷的拖拉机发动起来,麻子知道马车这个新事物在机村还没有运行十年,就已经是要被淘汰的旧物了。
麻子转过身细心地套好他的马车。他驾着马车,要让所有想坐马车的孩子都坐上来,去跑上一趟。过去,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坐他的马车的。他是一个不太喜欢孩子与女人的家伙。加上那时能坐马车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孩子都没有坐过他的马车。但他驾着马车在村里转了两三圈,马车还是空空荡荡的。那些平常只能爬到停着的马车上蹭蹭屁股的孩子,这会儿都一溜烟地跟着拖拉机跑了。村外的田野里,拖拉机手指挥着人们摘掉了挂在车头后面的车厢,从车厢里卸下一挂有六只铁铧的犁头。熄了一会儿火的拖拉机又突突地喷出了烟圈,拖着那副犁头在地里开了几个来回,就干完了两头牛拉一套犁要一天才能干完的活。村里人跟在拖拉机后面,发出了阵阵惊叹。只有麻子坐在村中空荡荡的广场上,点燃了他的烟斗。
过去,他是太看重、太爱惜他的马车了。早知道这马车并不会使用百年千年,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他真的就用不着这么珍重了。明白了一点时世进步道理的他,铁了心要让孩子们坐坐他的马车。第一天拖拉机从外面开回来时,天已经黑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马套上了。人们还是围在拖拉机旁热热闹闹。他勒着上了套的马,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马车之上。人们一直围着拖拉机转了两三个钟头,才有人意识到他和马车就在旁边。
“看,麻子还套着马车呢!”
“嗨,麻子,你不晓得马车再也没有用处了吗?”
“麻子,你没看见拖拉机吗?”
麻子也不搭腔,他坐在车辕上,点燃了烟斗。
拖拉机的吸引力真是太大了,麻子想补偿一下村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坐一趟马车的心愿都不能实现了。他卸了马具,把马轭和那些复杂的绊索收好,骑着青鬃马上山去了。这一上山,就再也没有下山。还是生产队的干部上山去看他,领导说:“麻子,还是下山吧,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反问:“马怎么就没有用处了?”
“有拖拉机了,有汽车了。”
“那这些马怎么办?”算上拉过车的马,生产队一共有十多匹马,“不是还需要人放马吗?那就是我了。”
第一个马车夫成了机村最后的牧马人。机村人对于那些马、对于麻子都是有感情的。他们专门划出一片牧场,还相帮着在一处泉眼旁边的大树下盖起了一座小屋,那就是牧马人的居所了。时间加快了节奏飞快向前,新人新事不断涌现。同时,牧马人这样的人物就带着一点悲情,隐没于这样的山间了。隔一段时间,麻子从山上下来,领一点粮,买一点盐,看到人,他那些僵死的麻子之间的活泛肌肉便浮起一点笑意,细眼里闪烁着锐利的光,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当馬车被风吹雨淋得显出一副破败之相的时候,他就赶着他的马群下山。每匹马的背上都驮了一些木料,他给马车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窝棚。
机村终于在短短的时间里,把马车和马车夫变成了一个属于过去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在记忆深处,马车还停在广场边一个角落里,连拉过马车的马都在,由马车夫精心地看护着。马和马车夫住在山上划定的那一小块牧场上,游走在现实开始消失、记忆开始生动的那个边缘。
拖拉机上的漆还很鲜亮,那些马就开始老去了。一匹马到了二十岁左右,就相当于人到了六七十岁,所以马是不如人经老的。第一匹马快要咽气的时候,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麻子坐在马头旁边,看见马眼中映出晚霞烧红西天,当通红的霞光消失,星星一颗颗跳上天幕时,他听见马的喉咙里像马车上的绊索断掉一样的声响,然后,马的眼睛闭上了,把满天的星星和整个世界关在它脑子的外边。麻子没有抬头看天,就地挖了一个深坑,半夜里,坑挖好了,他坐下来,抽起了烟斗。身边闪烁着明明灭灭的光芒,马的眼睛却再没有睁开。他熄灭了烟斗,听见在这清冷的夜里,树上、草上所起的浓重露水,正一颗颗顺着那些叶脉勾画的路线滴落在地上,融入深厚而温暖的土里。深厚的土融入黑夜,比黑夜更幽暗,那些湿漉漉的叶片却颤动着微微的光亮。
他又抽了一斗烟,然后,起身把马尸掀进了深坑。天亮的时候,他已经把地面平整好了。薄雾散尽,红日破空而出,那些伫立在寒夜中的马又开始走动,掀动着鼻翼发出轻轻的嘶鸣。
麻子下山去向生产队报告这匹马的死讯。
“你用什么证明马真的死了?”
他遇到了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埋了?马是集体财产,你凭什么随便处置?皮子、肉都可以变成钱!”
他当然不能说是凭一个骑手、一个车夫对马的疼爱。他因此受了这么深重的委屈,但他什么都不说,就转身上山去了。其实,领导的意思是要先报告了再埋掉,但领导不会直接把这意思说出来,领导也是机村人,不会真拿一匹死马的皮子去卖几个小钱。但领导不说几句狠话,人家都不会以为他像个领导。麻子这个死心眼却深受委屈,一小半是为了自己,一多半还是为了死去的马和将死的马。从此,再有马死去,他也不下山来报告。除了有好心人悄悄上山给他送些日常用度,他自己再也不肯下山了。
这也是一种宿命,在机器成为新生与强大的象征物时,马、马车成了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力量的符号,而麻子自己,不知不觉间,就成功扮演了最后的骑手与马车夫,最后一个牧马人的形象。他还活着待在牧场上,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
从村子里望上去,总能隐约看到马匹们四散在牧场上的影子。那些影子一年年减少,十年不到,就只剩下三匹马了。最后的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马找不到吃的,又有两匹马倒下了。那一天,麻子为马车搭建的窝棚被雪压塌了。当年最年轻力壮的青鬃马跑下山来,在广场上咴咴嘶鸣。
全村人都知道,麻子死了,青鬃马是报告消息来了。人们上山去,发现他果然已经死去。他安坐在棚屋里,细细的眼睛仍然隙着一道小缝,但里面已经没有了锥子一样锐利的光。
草草处理完麻子的后事,人们再去理会青鬃马时,它却不见了踪迹。直到冬去春来,村里有人声称在某处山野里碰见了它。它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它在饮水还是吃草?答案就有些离奇了:它快得像一道光,人还没有看清楚它就过去了。那你怎么知道它就是青鬃马?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就这样,神秘的青鬃马在人们口中又活了好多个年头,“文化大革命”一来,反封建迷信的声势那么浩大,那匹成为传说的马,也就慢慢被人们忘记了。
(若 子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宝刀》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