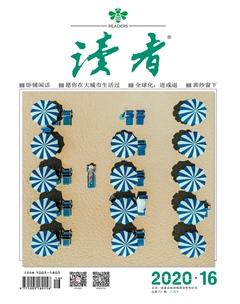喝开水
韩少功

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的感觉。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生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水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壤,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也绝不会用生水待客。烧一壶开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虽然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的概率一定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噬。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致“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们的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著名文学著作《十日谈》的产生,据说就始于一群男女藏入佛罗伦萨的乡间别墅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
中国人热爱喝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
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古英语中的chaa以及现代英语中的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的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的早发明10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
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烧烤饮食的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烤一下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药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了。在先秦和西汉,中国就有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更使中国医学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相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成为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19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并且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放血疗法下被活活治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求人——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也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被很多现代人无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已。
不过,福祸相依,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口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由好事变坏事?比方說,中国没有出现像欧洲15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那样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丧失了欧洲16世纪以后推进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的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欲主义、战祸连绵等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乱和不寒而栗。17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荡荡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肉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6000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个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马”。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1亿多再次暴增到3亿多(有一说是4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时,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皇帝,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就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兴,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19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繁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余 娟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熟悉的陌生人》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