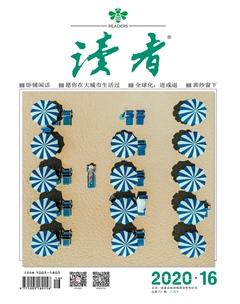守护莫高窟的年轻人
王双兴

陆佳瑜为参观者讲解
上山
来莫高窟工作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每天站在通往景点的大巴上,“觉得每天都很闲,不会有提升空间”。生活节奏被改变,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应该可以获得成长”,便来了莫高窟。
入职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游旺季马上就要来了。陆佳瑜有两个月的培训时间,白天听研究者、讲解员上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解说词,凌晨3点入睡,早晨6点起床复习,然后上洞窟,练习讲解。两个月时间看完8本书,笔记写满两个A4笔记本,陆佳瑜发现:“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莫高窟的知识根本学不完,感觉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莫高窟,也有人是毕业季找工作,无心插柳地来了。2005年,俞天秀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还纳闷:“莫高窟招计算机专业的干吗?”进入数字化研究所那一年,只有办公的电脑配有一根网线。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旁边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
有位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部门的安慧莉2009年入职,这个学工业设计出身的姑娘,此前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是8点档电视剧开始前,那个缓缓飘落的“飞天”图标。刚到敦煌时,安慧莉发现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买了一瓶绿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师傅绿茶一模一样,但商标处写的是“小二黑”。这个女生有点沮丧,觉得“待两年,肯定是要走的”。
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甘肃省省会兰州中转,然后沿着河西走廊抵达敦煌,沿路看着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心里都猜测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画临摹师彭文佳,来敦煌是因为对莫高窟艺术的向往。同窗同学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画廊和工作机会。而她想要和外界联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去25公里外城里的网吧。登录QQ,收到老同学发来的消息:“你们在敦煌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1挡挂到5挡”
现在,陆佳瑜的生活渐渐和工作融为一体。以前看《解忧杂货铺》,现在看《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现在变成了赵声良、王惠民,去书店都是直奔专业类的书籍。她不能忍受每次进一个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觉得是在退步”。
每天,当陆佳瑜带游客在开放洞窟参观时,另一群人正在非开放洞窟“面壁”。四五月天气回暖,利于材料黏结,壁画修复师们对231窟的“治疗”开始了。他们爬上脚手架,用毛笔除尘,用注射剂黏结,隔着一层镜头纸,用修复刀修复壁画……
这支队伍中,“80后”是主力。张瑞瑞是231窟修复师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前几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工作。她学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专业对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触壁画修复工作。和每个修复师一样,工作的前几年,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师父和泥、递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学习、提问。
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着手指列举留下来的理由:工作环境单纯,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成就感强。
耐不住寂寞的俞天秀,在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后,慢慢发现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模莫高窟,将莫高窟的影像数字化,保存起来。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40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今正定县)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现在画面里。“以前我们的成果都被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自己见过,其他人无法得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时确实觉得自豪: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到如今,俞天秀已经在莫高窟待了15年。那个跑去城里上网的画师彭文佳则度过了16年,在她看来,莫高窟就像一个乌托邦,不仅有永远汲取不完的艺术养分,还有世外桃源一样的环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诱惑,也没有太多功利的东西,非常纯粹”。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他记得,有前辈讲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吭声,最后说了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10年后再说。”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已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10年,他说:“1挡挂到5挡,就一直往前跑了。”

已辞世的老一辈守护人,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
接力
年轻人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在莫高窟对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脚的戈壁滩一直朝南,在“九层楼”正对着的沙丘上,是一个墓园,安葬在那里的,是来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轻人。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后来回国,四处逃难,8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在完成学业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水用完还要留着派其他用场;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着反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20余座墓碑端立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年轻人拿起来。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林 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