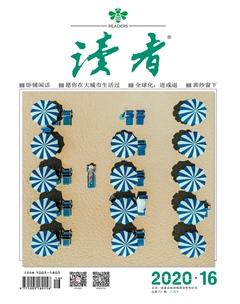人生过处唯存悔

何兆武
我年轻的时候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跟日本打仗。那时候想得很天真,认为抗战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是个美好的世界。后来发现,打仗是胜利了,可是离美好的世界还很远。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颠沛流离,也不愿做亡国奴。16岁那年,北平沦陷了,我回到湖南老家,从岳阳到长沙那一段,坐船要走5天。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这让我想到一个有点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样算是进步?从速度上看,火车更优越;可是坐船不仅欣赏了美景,心情也极好。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
为什么西南联大不大,当时条件又非常差,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答案就是两个字——自由。我在本科到研究生的7年里换过3次专业,读过4个系,那是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也是因为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私人之间也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我做学生的时候,没有统一教材,各个学校教的大不一样,各个老师讲的也不同。国文老师喜欢教哪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文章。
“中国通史”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个班,各有一套自己的内容和理论体系。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个王朝都还没讲完。北大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老师照本宣科,还不如播音员抑扬顿挫,学生也不会得到启发。
我亲见亲闻过物理系两位高我一届的才子杨振宁和黄昆谈论爱因斯坦新发表的学术文章,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当时我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
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能超越前人,能看出前人的不足反而是一个年轻人所必备的品质。自惭形秽的人,如我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的贡献,一个是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梁启超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郭沫若在自传里也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胡适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先驱,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功绩是伟大的。
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堂兄从沈阳来北平玩,19日父亲下班回来,进门就对堂兄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了,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
1936年秋天,我上高一,9月18日9点18分,日本军队故意挑这个时间开进北平城,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在北平城里耀武扬威。大队坦克车从新华门的前面开过去,那时候柏油路不太好,我放学回家看见坦克轧过的痕迹清楚极了,今天还历历在目。
做亡国奴的心情不好受。留在敌占区的同学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大家一个字母都不学,开始全班都是零分。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敌伪下令全北平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

年轻时的何兆武
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很少。很多年纪比我大一点的青年学生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很优秀,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挺辉煌。有一位前辈叫沈崇诲,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八一三”事变时,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艦“出云”号,26岁就殉国了。
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日本投降,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罢课,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并不能完全自主,不得不跟着环境、跟着条件走。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年轻人下乡五六年、七八年,把青春都荒废了。所以“文革”导致一代人的文化缺失,接不上气。
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却没有在这个领域做出多大贡献,反而拿了个“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自己要负点责任,环境也要负责任。我从30多岁到60多岁在历史研究所,应该是最能出成果的时间。不过,那时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
我们这一代已经“报废”了,现在是青年人的时代了。我老了,不会用电脑,你们说的智能手机、微信我更不懂。我还是老一辈人的习惯,只能看书看报、看印出来的东西。我读的书、听的音乐都是古典的,我的欣赏水平到19世纪为止,现代化的东西接受不了,没有那个基础训练。我不太了解现在青年人的想法,我身体不好,不出门了,跟青年接触很少,等于是与世隔绝了。
时代永远向前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人。人总是要被时代抛弃的,总会有赶不上的一天。
小时候,我家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和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三个人。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是真正的下层人民,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和掌柜的聊天。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卢梭《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同样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这个阶级压迫那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压迫这个阶级。这就好比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理想的不可实现就把它一笔勾销,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也不要过于天真,把什么都想得太简单,不然就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好友王浩曾在昆明翠湖边谈了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我当时正在看一本写歌德的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这个世界和人生,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
(小 诗摘自《时尚先生Esqu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