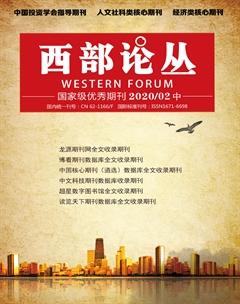我国民事诉讼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与功能
摘 要:田中成明先生在《现代社会与审判:民事诉讼的地位与作用》一书中,基于日本法治现状,表达了ADR会动摇诉讼审判在纠纷解决体系中中枢地位的担忧,提出日本民事诉讼未来改革的方向应坚持司法在纠纷解决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推进日本社会的“法化”进程。在此基础上,他还肯定了民事诉讼的政策形成功能。我国目前与当时日本的情况相似,均在进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那是否可以套用田中成明先生在书中的结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核心地位会被动摇,其功能也是政策形成功能呢?这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回答。
关键词:民事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实施
一、内容简介
这本著作出版于1996年,研究的主题是民事司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日本社会在逐渐“法化”,发生的纠纷日趋多元复杂,但传统民事诉讼却不能很好地应对,因此需要扩充审判的作用。随着司法对政策形成功能关注度的提高、诉讼外ADR的充实、纠纷解决中行政调解与私人和解的比重增大,司法作为“法的支配”最后屏障的中枢地位正在发生动摇,呈现出“去法化”的倾向。然而,日本这样一个还处于“法化”过程中的社会,在“法化”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去法化”战略是否恰当呢?作者运用“法化”、“非法化”(去法化)和“管理型法”、“普遍主义型法”、“自治型法”这两类模型对促进公正迅速审理的方式、现代政策形成诉讼的应对以及ADR的扩充与活用的方向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应确认并坚持司法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中枢地位,进一步推进日本社会的“法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再去超越各种制度性、程序性制约,构建一个更利于解决纠纷的民事司法体系。
本书的吸引力有两点:一是在于其将研究主题对准了民事司法在社会转期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与中国近几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问题高度契合。二是在于作者透视问题的独立视角。本书在写作时,日本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学术思潮上都受到欧美国家的深远影响,但作者能够对欧美相关学术观点与司法改革趋势做出独立判断,并能结合日本本土法治现状提出坚持“法化”道路的观点。
如前所述,本书成书基于日本本土法治情况,提出的观点适用于日本,但是否同样适用于我国呢?近几年,我国与当时的日本一样,也在社会“法化”不足、甚至尚未确立以裁判和当事人为中心的程序、法院仍处于超职权主义的情形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正在进行。那这是否如傅郁林先生(本书导读作者)所说,中国在“瘦子陪胖子减肥”?我国民事诉讼的核心地位是否也会因此而发生动摇?其在这次改革中的作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能拿本书中的结论去套,而是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回答。
二、DDR会动摇我国民事诉讼的核心地位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我国的DDR与域外的ADR的共性与差异。中国DDR与域外ADR均以建立完善非诉讼程序、整合纠纷解决资源为中心任务,以追求国家的善治与法治为目标。但两者的内涵和外延不完全一致。“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适应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需求,兼顾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和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而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往往是单指诉讼之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除此之外,我国DDR在构建理念、发展模式、调解与审判的嫁接关系上也与域外的ADR有所不同。
从基本理念上来看,与域外ADR构建相关的基本理念包括以下四种[2]:一是“接近司法/正义(Access to Justice)”。基于该理念发展出的ADR大多为司法辅助型ADR,旨在缓解司法压力,将司法从无法接近的现实中解救出来。二是自治与社区运动。基于该理念发展出的ADR大多为司法规避型ADR,主张通过社区调解、行业调解和商事调解等规避司法程序、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三是恢复性司法。该理念主要体现在刑事领域的和解制度中,主张被害方与被告方的协商与对话,从而缓和两方的紧张关系。四是服务型政府理念。基于该理念发展出的ADR主要为行政型ADR,主张通过行政调解与和解、委托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而我国DDR以“国家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为构建理念,即在国家宏观统筹、确认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法治保障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各方的参与和良性互动。
从发展模式上看,域外ADR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模式。普通法系主要通过该模式推进ADR的发展,其特征在于依赖市场化成本效益和激励机制鼓励当事人采取非诉讼化的方式纠纷解决,其形成的调解规则自治化与民间化的程度较高。二是立法模式。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该模式构建ADR,即通过立法与顶层设计建立若干非诉程序,如日本的《ADR促进法》,欧盟的《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2008/52/EC 指令》。三是司法模式,即司法推进模式,则是以司法机关为主导,通过司法政策、实践创新和具体指导,推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发展,在取得效果之后,再形成立法和正式的制度。[3]而从我国DDR发展的阶段以及改革中赋予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创设司法确认制度、构建法院附设ADR制度和专职调解员队伍等具体措施来看,我国DDR的发展模式为司法推进模式。
由此看出,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发展模式来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是由司法推进和引导的,其并不能动摇诉讼的固有地位。此外,我国是将调解与裁判并置于民事诉讼程序内,并将调解作为民事审判程序的一种結案方式,而域外部分国家包括日本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之外设置了专门的调停程序,这就能反映出中国与域外民事诉讼在纠纷解决中的定位差异。况且,即使ADR能够对民事诉讼的地位造成影响,那也不是动摇式、虚化式的影响。窃以为,诉讼制度与程序本身的完善与法治程度才是影响其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在纠纷解决中,若诉讼自身没有竞争力,失去了民众对其的信任与认可,便怪不得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抢了它的核心地位。如果人民不能在案件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民众逐渐对诉讼程序失去信仰,到那时候,即使无需ADR的影响,司法也会形同虚设。
三、我国民事诉讼的功能——政策形成还是实施?
作者在书中指出,现代型诉讼除了具备运用判例进行法创造的规范功能以及通过正当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这两个传统功能外,还具备对立法、行政、社会舆论及社会运动等公共政策的形成功能。关于民事诉讼的前两个功能,笔者十分赞同。纠纷解决功能自不必说,造法功能则需要进一步澄清。卡多佐认为,司法的过程就是法官造法的过程。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制度,且立法权由人大享有,因此便有法院只能服从和适用法律,不能进行法官造法等法教条似的观点。但实际上,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还有定期发布的指导案例,均会涉及一些现有立法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解释法律与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
关于作者所说的民事诉讼之政策形成功能,笔者则不敢苟同。窃以为,诉讼的提起、法庭上的辩论、判例的自发性运用等司法活动确实会对立法、行政、社会舆论等公正政策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促进政策的形成,而是促进政策的调整与修正。诉讼程序的开展过程也并非是政策形成的过程,而是政策实施的过程。至少在中国语境下是这样的。达马什卡认为,中国的司法程序是在一种能动型的政府和一套科层式的权力组织机制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属于政策实施型程序。[4]在政策实施型程序下,诉讼程序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还要体现现有司法政策的要求。在中国,当中央发布某项政策时,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会根据该项政策制定相关的考核指标,督促下级司法机关全面落实该项政策。基于绩效考核的动力或压力,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便会不自觉、甚至是有意偏向政策的要求。可见,政策有很可能影响案件的裁判,司法形成的判例也不僅表达了法院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立场或态度,更是体现了某项政策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法治环境下,民事诉讼的作用更多是促进政策的实施,而非促进政策的形成。
注 释
[1] 龙飞.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域外比较与借鉴[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9(1):82.
[2] 范愉. 借鉴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J]. 中国应用法学. 2017(3):52-53.
[3] 范愉. 借鉴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J]. 中国应用法学. 2017(3):54-56.
[4] 达玛什卡.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8.
参考文献
[1] 龙飞.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域外比较与借鉴[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9(1).
[2] 范愉. 借鉴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J]. 中国应用法学. 2017(3).
[3] 达玛什卡.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王晶(1996.10—),女,河南省南阳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