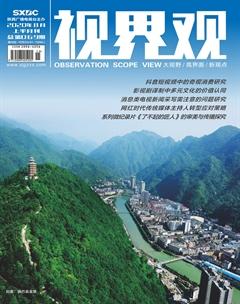论国画美学思想对版画创作的启示
张程程
摘 要:在鲁迅的教诲下,向传统艺术学习的思想根植于版画青年的心中,体现在版画青年的创作中,使版画艺术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对国画与版画的交叉关系的探讨,解读国画美学思想在版画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国画美学;版画创作;审美交叉
为了使版画民族化、本土化,适应群众审美的需要,鲁迅提醒版画青年注意向传统绘画、古代画像石和民间艺术汲取营养。这种创作思想对版画青年产生重要影响,古元、江丰、力群等一批画家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生命力的版画作品。90年代以來,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潮流的冲击中,版画亦通过向传统回归的方式来强化个性意识。而今版画青年更应立足传统,将从民族民间艺术、姊妹艺术中得到的启示运用于版画创作。
一、“计白当黑”在版画布局中的运用
受老庄和玄学思想影响,国画讲求虚实相生,画家在画面上采用留白的表现方式,成为国画构图的一种特殊形式。留白亦称布白,即布置画面中的空白,创作时不仅要在实处悉心雕琢,亦要在虚处反复经营,所谓“计白当黑,妙趣乃生”就是此理。画面中的白是画面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其他的线条、形状一样具有意义的,不仅与黑形成对比,同时也是意境传递的载体。正如诗词中的“言外之意”和音乐中的“弦外之音”,在画面留白处,便是那意境深远、意味深长,令人无限遐想的妙处。
黑白木刻的艺术魅力来自于黑白布局形成的强烈对比和视觉张力,黑白语言是版画的灵魂,其运用体现了版画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国内版画创作以凸版为主,无论是以黑衬白的阴刻还是去白留黑的阳刻,都要求版画家具备正负形意识,在刻制时保持对负形的敏感,通过画面中的白来塑造黑。由于人的视觉总是先注意到画面中深色事物的轮廓,因此画家在创作时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用白色来对比和凸显黑色,以此强调画面重点,分配主从关系,使之服务于整体。同时,白色还起到控制画面虚实的作用,画面中缺乏黑色会显得轻浮、软弱,而没有白色亦会使人感到压抑、沉重,这与国画中的留白一致。
赵延年在《鲁迅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中通过强烈的黑白对比刻画了鲁迅直面人生、勇于斗争的性格,画面中的白色积极主动的传达着作品的意义。鲁迅神情严肃,十字形的黑色围巾与白色长衫形成强烈冲突,在沉重的黑色背景下,一道道犀利、硬朗的白色线条像割开黑暗的利剑,响亮且振聋发聩。头部周围的白色不仅起到塑造形体的作用,而且具有象征意味,那一根根向上挺立的头发仿佛他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
二、“骨法用笔”在版画刀法中的转换
谢赫提出“六法论”作为评价艺术的重要法则,其中“骨法用笔”确立了线条在国画中独立的美学意义,成为千百年来国画用笔的规范。“骨法用笔”意在要求画家注意线条的质感,行笔时将气力贯注笔尖,使笔墨形迹免于臃肿呆滞、软绵无力,而具有紧劲连绵、多力丰筋之态。前人对线条的表现力进行不懈探索,光白描绘法就有高古游丝、钉头鼠尾、战笔描等十八种,山水画亦有披麻、解索、牛毛等皴法,通过用笔形成的线条美感成为了国画审美的核心。
刀法是版画创作的核心,其地位作用与国画中的用笔相似,除基本的造型功能外,其本身也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国画讲究“骨法用笔”,版画也应该“骨法用刀”,注意表现刀痕的质感,行刀时避免顺应线条的刻制方法,以破除线条的轻滑软弱,使线条具有凝涩感和厚重感。版画根据不同的刀型,概括出推、挑、切、铲、凿、转、刮、戳等用刀方式,运刀过程中画家通过对线条滞、畅、凝、涩的把握,决定行刀时的轻、重、缓、急,这与国画用笔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李桦整理的四十八种木刻基本刀法中,亦借鉴了国画用笔的正、侧、卧、露、藏锋等方法,丰富了版画刀法的运用方式。他的《怒吼吧!中国》是一件非常注重线条和刀法运用的作品,画面构图简洁,背景空无一物,着力刻画被缚在木桩上挣扎反抗的男人。人物身体的线条转折明确、刚劲有力,清晰地交代出骨骼的转折和肌肉的走向,体现了画家对线的敏锐把握与对刀精准运用。人物右腿和上臂正在发力,肌肉隆起,因此外轮廓的线条转折和联结较为明显,而左腿和小臂着力更小,线条相对舒缓。木桩和绳索线条的用刀流畅,与人物身体艰涩的线条相区别,使画面形成一松一紧的节奏感。
赵延年偏爱平口刀的丰富表现力,刀法概括洗练、线条厚重质朴,他汲取国画灵活多变的用笔方式,在《海》中刻画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渔民。老人的面部通过刀法的正侧交替、提挑摇摆、薄铲深切塑造出皱纹,类似于国画山水中的解索皴。通过大平口刀切刻出来的细小皱纹方转有序,富于变化,体现出赵延年高超的艺术技巧,如同国画中通过对笔的熟练掌握,达到“秃笔写尖”“大笔写细”的效果。
三、“墨分五色”在黑白木刻中的体现
我国古代盛行的“五色”理论源自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黑青赤黄白”五色,而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主张“素朴玄化”,以墨代色。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运墨而五色具”,被视为“墨分五色”观点的开端。他认为墨色的浓淡深浅变化可以表现出丰富的色彩感,因此不必拘泥于物体表面的色相,后来“墨分五色”逐渐被解释为“焦、浓、重、淡、清”五种墨色。五种墨色不仅在明度序列规律上与“黑青赤黄白”相一致,亦能表现单一色彩的浓淡变化,虽然牺牲了事物的固有色,但有限色彩的删减释放了无限的色彩想象空间。画家通过对用笔、用墨、用水的控制,以破、泼、积、渲的方式就可以表现物体的远近、明暗、凹凸、深浅、厚薄、层次等的丰富变化。
国画用墨色表现自然物象的方式,得益于墨色在饱和度和明度上的细微差异,这与黑白木刻通过黑白灰关系形成不同对比强度从而产生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相一致。鲁迅强调“木刻终究以黑白为正宗”,就是因为黑白木刻仅通过黑白二色即可表现出丰富的视觉变化。版画中的灰色不是指明度和纯度上的灰色,而是依靠不同型号刀法的穿插、组合和排列方式在画面上形成点、线、面疏密聚散关系,使观者在视觉上形成的弱对比的区域。黑、白是位于两极的色彩,层次丰富的灰色穿插其中不仅有助于塑造形体,而且可以中和黑白二色的强烈对比,表现更加温和细腻的情感,形成另一种视觉美感。
黑白语言是所有色彩语言的总和,通过黑白的对比交融就可以使画面产生色彩感,比如对画面环境的营造,可以使观者联想到与之相对应的色彩,从而在心理上将对象的色彩赋予画面,由此产生色彩共鸣。徐匡是一位非常擅于用黑白语言表现色彩感的画家,他在黑白木刻中偏爱用小圆刀和小角刀刻出细小的刀痕,通过疏密不一的刀法组织表现色彩的明暗和冷暖。如《喜马拉雅》中草地、白色衣服和云都被处理成白色,但画家通过刀痕的组织方式、疏密和形状表现出了不同的色彩。画家还不厌其烦地细致刻画了人物、草地和背景的大面积灰色,与画面中的黑、白共同建构起物体的固有色和明暗层次,让人仿佛看见了一幅扎实的油画。
四、“诗情画意”在版画创作中的追求
国画创作非常重视意境的营造,意境就是画面上情景交融的詩意联想效果,古人将绘画与诗进行融通,通过画面的诗意构建悠远的意境,以达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由于绘画是一种具有“召唤性结构”的文本,因此画家将情思隐含于画面,可以使观者在欣赏的过程中体味到画家“暗示”的内容,并通过联想和想象还原于脑海,看似“不在场”的物象实则贯穿整个作品的创作和欣赏过程。意境是画家借景抒情、表情达意的艺术境界,通过对有限事物的描绘引发观者无限的情思,使观者在思想上受到感染、心灵上生发共鸣。对意境和诗意的追求是国画创作追求的目标,宋代徽宗设置画科考试就常常以诗为题,要求画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可以说,意境的有无是评判作品成败的标志,意境的深浅是衡量作品高下的因素。国画中意境的营造常常通过笔墨和构图来实现,用笔讲究“笔断意连”,即笔迹消失但气势连贯,形成画面的空灵幽远之感;或在构图上通过留白语言激发观者的丰富想象力,亦可传递画面的未尽之意。
吴凡的版画以“简”取胜,其文学和传统艺术修养深厚,他将国画意境的营造与版画创作相结合,创造了许多具有诗情画意的优秀作品。《蒲公英》借鉴了国画留白的艺术语言,画面上只塑造了几种简单的事物:小女孩、蒲公英、篮子和镰刀,背景为大面积的白色,形式单纯而内涵丰富。物体的表现类似于国画工笔与写意的结合,人物刻画不注重于精雕细刻,篮子和镰刀也是简单勾勒、点到为止。画面左下角的题字和款印不仅起到稳定构图的作用,更使画面体现出诗(意)、书、画、印相结合的国画处理方式。整幅作品构思巧妙、简洁精炼,其意境犹如一首抒情小诗。
艺术的发展得益于人们对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各艺术门类是艺术家表现情感的方式和美的途径,其中蕴含的审美情感相融相通,在向美的终极目标行进时殊途同归。创作版画在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中找到向传统艺术借鉴的方式,因此在中国扎根深营茁壮成长,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对当下版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途径予以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俞建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2]周建夫.木刻技法分析[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
[3]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