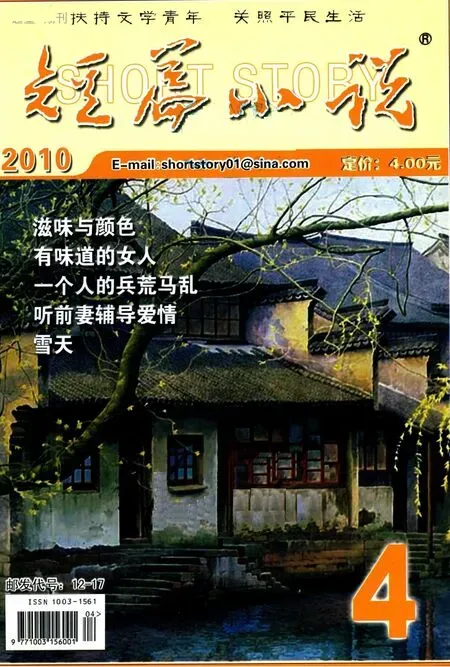焦桐记
◎唐黎标
责任编辑/董晓晓
一
两个女子走进茶楼时,雨还淅淅沥沥地下,整座城都湿了。她们收起伞,相对而坐。一个女子点了杯龙井,另一女子点的是滇红,茶香袅袅之时,西湖与滇池仿佛只隔着一张茶桌。
“这么说,你很早就认识他?”点龙井的女子先说话。
点滇红女子说:“那年我十三岁,上学时总会经过他家楼下。那是座老式的小楼,粉刷成浅黄色。当时我觉得,每扇窗户后面的人家都该一样,两三口人,过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当我听到从他家屋里传出的琴声,才知并非如此。”
可能碰见往事,女子有些恍惚的伤感,慢慢啜茶,不想一根茶梗混入嘴中。想吐出去,飞快地瞅了一眼对面女子,又含回去,用牙尖细细地嚼,洇了一嘴苦涩的余味。
龙井女子并没留意,指尖搭在映成碧色的杯沿上,失神地望着窗外。滇红女子咬咬嘴唇,继续说道:不怕你笑话,当我第一次听到那琴声时,并没见过真正的丝桐,还以为是钢琴。
我父亲是个三轮车夫,整日守在火车站,若是遇到生面孔的外地人,他就开着车在城里多兜几圈。外地人要是不肯吃这个亏,我父亲便会抽出一把宰牲口用的剔骨钢刀,露出满脸凶相。他就是靠这个养家糊口,无论怎么卖力,我家都一览无余地穷,看来,他的凶也是不值钱的,难免要将霸气带回家。父亲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便是,去,给我买酒。
父亲喝酒时,只穿一件脏兮兮的三角裤头,蹲在床板上,左手端酒杯,右手夹烟,眯缝着红彤彤的眼睛,想起谁骂谁,老亲旧友街坊邻居甚至电视里的人也不放过。一边骂,一边将烟灰弹得到处都是,我的筷子经常是跟一截簌簌的烟灰同时落进菜碟里。除了将筷子缩回来,我还能说什么?当时,我连头都不敢抬,他那个三角裤头松松垮垮,里面的东西动不动就挣脱出来,父亲也不在意,常常是漫不经心地伸手将其送回去,继续喝酒吃菜骂人。至于我母亲,每天只知道抱怨,抱怨屋子太乱、父亲没能耐、她自己满身都是病、我不知道帮着干家务,越抱怨越伤心,吧嗒吧嗒掉眼泪。
父亲要是听烦了,抬腿就给母亲几脚。父亲总是用右腿来教训母亲,因此我毫不怀疑,他右腿要比左腿强壮有力多了。挨完揍后,母亲的抱怨没了,坏心情也杳无踪迹,甚至比以前更加勤快,抹桌子擦地,隔了一会儿,还主动问父亲,用不用我再给你煎俩鸡蛋下酒?
这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听到这,你大概也就理解了我听到那琴声时的心情。后来有一天,我见到了弹琴的人,是个女子,穿着月白色旗袍,身材高挑,五官云淡风轻。当时,她正在楼下买菠萝,轻声细语地问完价,也不还价,伸出葱细的手指,捏住菠萝狰狞的叶子,放进塑料袋里,扭身便回了。
我望着那女子背影,怅惘好一阵子。从此,只要见到她,便跟在后面,她讲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甚至一个眼神都让我那么着迷,不知不觉模仿起来。回到家,母亲发完牢骚之后,也会留意到我的变化,大惊小怪地问,你跟谁学成这样,难受死了。
我岂能理会母亲难不难受,照样整日暗中留意那女子。后来听说她是个高中音乐老师,丈夫也在同一所学校,教美术。这样的女子,会有怎样的丈夫呢?我又将好奇心转移到她丈夫身上。说来也巧,我很快就见到了他。
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忽然下起雨,我没带伞,便将书包顶在头上快步跑,快到巷口时,一不留神摔倒在地。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问道:“用不用我帮忙?”
我双手撑地,将脸仰起,这个角度望去,他显得异常高大,背后是灰蒙蒙的天空,密雨如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他撑着伞送我回家。为了不被淋到,我紧紧挨着他,以至于他透过衬衣纤维的体温,我都能丝丝缕缕感受到。风里不时还有股淡淡香气飘来,是路边的几株丁香开了。
走到他家楼下时,恰好听见那个女人在弹琴,他说,有琴声的地方便是他的家。我下意识地朝楼上看一眼,其实,我早该猜到,只有他才配得上那个女人,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却酸酸的,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曲子?”
“《潇湘水云》。”他一脸痴迷地回答。
“你妻子弹的钢琴真好听。”
“这是丝桐,一种古琴,”他微微一笑说,“不过,我却喜欢叫它焦桐。听过蔡邕吗?他就喜欢用烧焦的桐木造琴,后来人们便把好琴都称作焦桐。”
我并不知道蔡邕是谁,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时,在那稠风密雨中,依稀嗅出了一丝烧焦的木炭味道,好似淋湿的炊烟。
从那天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十三岁,同龄的孩子还在奋发图强,天天向上,我却暗暗喜欢上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男人,不行,我该给他起个诗意的名字。
回到家后,我翻了许多书,可惜家中只有《金瓶梅》《十万个为什么》与一本残页的 《聊斋》。值得庆幸的是,聊斋里还有个宁采臣,好吧,他是采臣,那么我就是小倩,一缕被树妖捆绑的幽魂,爱得却那般真真切切。
只可惜我这个小倩并没有吸引男人的妖术,每次在巷口见到他,都羞得满脸通红,心怦怦地乱跳,低着头匆匆走过。而他,我的采臣,好似也不记得我了,是啊,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丫头,那场雨白下了。
既然喜欢上了他,那个女人就不再圣洁与迷人。他们经常在黄昏后出来散步,低声说笑,手牵着手,偶尔也松开,但很快又自然而然地牵在一起,就好似他们的掌心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磁石,吸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
看到这里,我嫉妒得要命,假如自己真是小倩多好,懂得妖术,借尸还魂于那女子身上,成了她,与我的采臣郎情妾意。
除了散步,他们还喜欢在周末时去公园,坐着摩天轮一点点升到高空。也许是远离地面的缘故,他们将爱意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个女人还剥了一块水果糖,放进他嘴里,随手将糖纸丢在空中。他们也许没有发现,在他们下面的座舱里,总是坐在一个小女孩,微微仰着脸,将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个细节都放在眼里,滤进心中,这个女孩当然是我。
无论地上,还是空中,我和他们始终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天蓝得要命,钢轴转动的声音掩在透明的空气里,像个不耐烦的咒符。我微微闭上眼睛,想,说不定什么时候钢轴就会被拧断,巨大的摩天轮将会像蒲公英一样飘到空中去,到了那时,我会不会顺着伞骨一样的铁架,爬到他们的座舱里,问问他,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我这个在雨中滑倒的小女孩。
二
后来有一天,又是雨得意扬扬下得好大。我放学回来,途经他们家楼下,忽然看到许多人往一辆卡车上搬东西。他穿着墨绿色雨衣,指挥几个搬运工将一架古色古香的琴从楼道里抬出来,那个女人则撑着一把藕荷色的伞,站在屋檐下,满脸担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张叫作焦桐的古琴,只看一眼,心就塌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恰好他抬头望过来,我又怕了,低下头去,不知所措。等我再抬头时,他已闪进楼内。我好恨自己,蹲下身子,从书包里取出作业本,撕去一张纸,垫在膝盖上写道,我爱你,无论你搬到哪里去。
雨水沿着伞骨,滴滴答答落下来,那张纸没躲过去,湿了,连那个“你”字也模糊成一片忧郁的蓝。我实在太慌张,哪里顾得这么多,匆匆忙忙地将信叠起来,让一个搬运工转交给他,然后慌里慌张跑掉。
我失魂落魄地跑回家,站在阳台上,恰好能看到他家楼下,搬运工将我的信交给了他,比比划划地说了些什么。他看了一眼信,又抬起头来,朝着大街环目四顾,哎呀,那是在找我。他怎么找得到呢?我忽然后悔,连拖鞋也没换,快步下楼,低声喊着,我在这里!
当我跑到大街上时,搬家的车已开走,在街尾拧拧屁股就不见了。我站在大雨中,山崩地裂一样地难过。撑着伞的路人,三三两两地从我身旁经过,都很好奇地看着我,他们怎会知道,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心里却有一种此生已去的悲痛。
那天,我被雨淋病了,在床上昏昏沉沉躺了四五天,等我好一些,走到那个最后看他一眼的阳台时,母亲刚把新洗的衣服挂在晾衣绳上。母亲或粉或红的短裤、相貌古怪的胸罩,父亲已经洗掉色的三角裤头,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的袜子,都耀武扬威地晒太阳。忽然,一滴还带着肥皂味道的水,毫不客气地落进我的脖领子里,我缩了缩脖子,一股凉意顺着脊椎一直爬到尾骨,不由冷冷地想,这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待了。
然而我毕竟资质有限,无论怎么用功学习,都没能考上高中。最后被一家技工学校录取。对此,父母却很满意,他们觉得又是高中又是大学,啰里啰嗦的,还是技校实惠,毕业就分配,早上班,早挣钱。
我念了两年技校后,被分配到一家腈纶厂,一切似乎就该如此,可我却总也忘不掉那一曲《潇湘水云》。后来,我在街上见到一个古琴培训班,想也没想就报了名,学了三个月,老师教了很多曲子,我却只学会一支曲子。老师摇头晃脑地劝诫说,别浪费学费了,你没这个天赋。我坦然笑笑,已经很满足,因为我学会的那个曲子,恰好是《潇湘水云》。
到了该处对象的年龄,有个小伙子看上了我,几经交往我们就确立了关系,但渐渐我发现,他跟我的父亲一样粗鲁庸俗,喜欢用说脏话来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目光短浅却又自以为是。这个首尾呼应的相似,看来注定了要霸占我这一生。
我还能怎样,即便不是跟这个,再碰见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于是,当我得知怀孕后,便开始跟未婚夫筹划婚礼,选个良辰吉日草草将自己嫁出来便是了。
无论怎么草率,婚纱照都得有。那天,我在影楼里等未婚夫,没想到隔着橱窗却看见了他,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我想都没想就跟了过去。
后来,他走进那个我们都熟悉的公园,买了一张摩天轮的票,我也匆匆忙忙买了张票,跟当年一样,坐在他下面的座舱里。
摩天轮渐渐升高,再霸道的时间,也不能让往事缩水,我又想起当初的情景,无论天上地下,那都是无法跨越的距离。然而,眼前并非往事,世事偷工减料,他的身边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将水果糖放入他口中的娇妻。我暗暗猜测,也许他们已经分手,这样一想,心不由怦怦跳动,既紧张又兴奋。
摩天轮离开地面,时间就变得缓慢了,我紧紧盯着他的背影,既然命运已经安排我再一次见到他,就不要再让其走掉,很多明媚而忧伤的日子,还有那场混杂着丁香味道的大雨,又都从记忆里辗转归来。
只可惜,摩天轮不止带着我们升到高空,还会一点点送回地面,离人群越近,我越恐慌。曾几何时,我自称小倩,懂得法术,妄想着吹一口仙气,将他定住,可现在的我,不知是否已经修炼成精。在我走神之际,他已离开摩天轮,一步步远去,我紧追几步,没想到脚下一滑摔倒,再抬头时,他已不见。难道要再一次失去他,我心里好难过,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说话的人正是他,站在我眼前,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路人话,却让我既感动又委屈地流出眼泪。我的泪让他迟疑,伸出的手又缩回去。是的,我必须为自己的眼泪解释,情急之下,不由说道,我的脚好疼。就这样,他搀着我,要把我送回家。后来我说渴了,他在路边买了一瓶冰镇雪碧,我攥着雪碧,坐在路边,久久不说话,其实是拖延时间。他忽然问道,你为什么一直在跟着我呢?我愣住了,撒个谎说,我觉得你很像我以前一个音乐老师的丈夫。他仔仔细细打量我,哦了一声,不再说话。我一见他这副神情,更加确定他们已经分手,于是便说,我很想见她。他犹疑了一下说,那很容易,我家就在附近。我不由大失所望,原来自己的猜测并不准。
他的家住在三楼,尽管这已不是以前的那个房子,可对我来说依然保留着一种神秘的亲切。当年,我多么渴望轻轻敲开这扇门,看看里面到底跟自己熟悉的世界有何不同。然而现在,却是男主人亲自打开房门,侧着身子请我进去。
我一眼看到鞋架上的那双粉红色拖鞋,心安了,看来他的妻子并不在家,谁曾想他却说,你的老师就在书房,去看看她吧。
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屋内空空荡荡并没有人影,唯有一张肃穆的遗像挂在西墙。他站在我身后,满脸悲恸地说,她已经死了三年了。
原来是这样,我片刻的惊愕过后,赤裸裸的惊喜便涌了满脸。
随后,我便看见了那张神秘的古琴。这么多年,它一直在我的想象里时隐时现,此时终于得见。看上去,与别的古琴也没什么不同,只是在下面很认真地刻了两个字,焦桐。我轻轻抚摸那两个字,想起当年他说话时的神情,于是觉得这琴还是不同的。
三
我慢慢将手移到琴弦上,随着嗡的一声,不由向后退了一步,也就在那一刻,我仿佛见到了那个女人端坐琴前,真奇怪,一张复制她生前音容笑貌的遗像,并没有让我有丝毫感觉,可这琴却让我觉得她仿佛还在。
我回过头,忽然发现他的目光复杂而奇怪,顿了顿,只听他说,谢谢你,如果不是刚才遇见你,我已经决定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取出瓶安眠药,苍白的药片,跌落于猩红的地毯上,好似洒了一地奇怪的睡眠。
忽然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很小的时候,我就模仿过那个女人,现在我完全可以成为她。我盘腿坐在琴前,弹了起来,当然是那曲《潇湘水云》。他倚着房门,坐在地毯上,泪流满面地听着,我不由抬头瞥了一眼那个女人的遗像,心里得意至极。
那天我回去时,未婚夫早已等得不耐烦,一见我就大发脾气,质问我去了哪里,害得他在影楼空等一场。我很平静地告诉他,不用拍婚纱照了,我们结束吧。
第二天,我毫不犹豫地打掉孩子,然后去找他。果然不出所料,他既高兴又惊讶,我们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尽管我很清楚,刚刚做完流产不能做爱。
几个月后,我们领证结婚,没有婚纱照,没有典礼,我只让父母跟他匆匆见了一面。新房就是他的家,装修都免了。只是那个书房、那张琴、那遗像,却也好似陪嫁一般,纹丝不动,让我很不舒服。也罢,若非那一曲《潇湘水云》,我也不能如愿以偿。
一开始,我还带着感激的心情,打扫书房,擦去每一缕灰尘,每每与遗像里的女人对望,心里未免有一丝隐隐不安,竟然觉得自己像贼。
我一直担心,他会询问我跟那个女人的事,毕竟在谎言里,她是我的恩师。幸好,他避免伤心,对此只字不提,甚至连我的工作也从不过问。一日三餐,夜夜相拥,偶尔听我弹一曲《潇湘水云》,这对他就足够了。
时光打磨日子,我得对他有所了解。这时候的他,早已辞去老师的工作,不教书,改成写字,做了一个自由撰稿人。没有朋友,与亲人也很少来往,唯有我在他身旁进进出出。晚上拎着蔬菜水果日用品回来,第二天早晨上班又拎着满袋垃圾下楼,生活周而复始,一遍遍临摹那个曾经让我刻骨铭心的爱。
这正是我要的生活,在单位我是个守着呆板机床的挡车女工,在市场我是个讨价还价的家庭妇女,可回到家里,我就是个雍容高雅的女主人。有时推开窗户,望着路灯流泻的长街,我就想,会不会有个小女孩,也站在那里,满脸向往与羡慕地望过来,就像当年的自己,这样一想,枝枝蔓蔓的疼惜便爬满了心间。
偶尔,我也暗中刺探,他难道真就记不起我,那个曾经与他雨中同行的小女孩。还有那封被雨打湿的信,他是否依然保留?事实上是,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一丝一毫那个小女孩的踪迹,以至于让我也恍惚得好似与那个小女孩断绝了来往。
转眼,我们已结婚一年,贴在梳妆台上的喜字,褪去了最初喜气洋洋的色彩,可我的肚子却一直静悄悄。医生说,可能我上次流产时留下病根,今后也不能生育。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并不介意,反而邀功似的说,我给你买了一件旗袍。我听了也有几分感动,毕竟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件衣服,然而当我将旗袍穿到身上时候,脸色却变了,我本是穿M码,他买的却是S码。
“你穿着真合适。”他站在镜子外侧,笑吟吟地称赞。我望了眼镜子,目光又左拐右拐进了书房,猛然记起,那个女人身材高挑,不正是穿S码吗?想到这里,我不由觉得旗袍多出来的地方灌满了阴森森的凉气。他却还在我耳旁说:“记得你喜欢紫色,像丁香的颜色。”
我终于忍无可忍,大声质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紫色?”他愣住了,好半天没有说话,一脸无辜。我忽然后悔起来,不该无缘无故朝他发脾气,可真的没有缘故吗?
尽管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最后还是向我赔了不是。事情似乎就过去了,我也希望如此,可类似的事情,日后总是不断地发生。
每天早晨,我买回豆浆油条,他却将牛奶煎蛋摆在桌子上,很殷勤地说,我记着,你喜欢吃七分熟的煎蛋。累了一天,夜里躺倒床上就想睡觉,可他却开着床头灯,倚着床头看书,当我抱怨的时候,他很诧异地盯着我说,你以前不就喜欢睡前看一会儿书吗?我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木菊、茑萝、茉莉,可每次他只踩着凳子给一盆绿萝浇水,我质问他为何厚此薄彼?他说,你不是只喜欢绿萝吗?我仰脸瞅了瞅,竟然记不起来什么时候买的这盆永远不会开花的花。
这些事,本来一直都在,只是我没在意,一旦在意了就泛滥成灾,勾出许多不可名状的不自在,心里闷闷的。
清明到了,没有雨,入夜后,街上多出许多人影,我隔着窗口望去,只见他们或蹲或站地在十字路口烧纸,左一簇右一簇的桔黄火焰,还有那潜在夜色里的黑烟,急匆匆地飞走在阴阳两界的驿路上,都是为了怀念。
他回来很晚,身上带着酒气,眼睛红肿,泪迹未干,进屋后鞋也不换就倒在床上。我蜷着腿坐在他身侧,有些气,又有几分疑惑,他从来不喝酒,为何今天醉得如此厉害。就在这时,他忽然一翻身,口里急切地喊道,焦桐,焦桐!
我不由朝书房望去,忽然间明白了,焦桐不止是一张琴的名字,不由光着脚跑进书房,双手扶着墙,仰起脸问那张遗像,你是不是叫焦桐?说话啊!随后,我蹲在地板上,榨汁机似的哭了起来。那一天是清明,焦桐的祭日,我的难日。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显得局促不安,一味地讨好,擦地、抹桌子、倒垃圾,极其不自然地问我,早餐想吃什么?我不冷不热地回答,豆浆油条,对了,顺便到超市买一瓶六必居的臭豆腐。
他领命而去,背微微驼着,身子有些晃。我当然知道,醉后初醒的早晨,身体会很虚弱,然而偏偏装着不知道,让他干这个,干那个,不是不心疼,只是他的那场醉与我无关。
是的,最初我是想扮演那个女人,获取他的爱,可这个角色我不想演一生一世。然而,要想摆脱她,也很难,甚至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女人阴魂不散,在这个家里无处不在。每当我坐在琴前,她便借尸还魂,没错,我对音乐毫无天赋,何以那一曲《潇湘水云》却弹得余音绕梁,原来,她才是小倩,从一开始就附了我的体。
四
我开始去破坏所有与那个女人有关的东西,让绿萝神秘失踪,将床头灯拧掉,紫红色的旗袍一寸寸地剪破扔进垃圾桶。当然了,最让我不安的还是那个书房,趁他不在家,我找了一个收破烂的,将焦桐琴低价卖了。就在小贩欢天喜地要离开的时候,他回来了,将琴抱在怀里,坐在地上失声大哭。
我只好将钱退给小贩,连声道歉。小贩大失所望,临走前,在我耳旁小声问:“你的老公精神不好吧?”
我瞪了他一眼说:“你妈精神才不好。”
他成功保卫了他的焦桐以及那间书房里的一草一木,这是他的底线。我站在地板中央,环臂冷笑,好吧,既然我没法清除掉这些残渣,那就除掉自己身上一切与那个女人有关的相似。从此,我不再轻声说话,很少打扫房间,内衣内裤攒到一起洗,旗帜一样挂满阳台,甚至还请来父母助阵。他们果然配合,父亲将空酒瓶摆得满地都是,喝酒时,依然只穿三角裤头,衰老的狒狒一样蹲在沙发上,母亲上厕所很少冲马桶,每次走进书房,都指着那女人的遗像,阴阳怪气地说,这个狐狸精,咋还挂在这儿?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他以沉默对峙,只是有一天,我忽然在床头柜里发现半瓶安眠药,原来,他再次萌生死念。我慌了,将父母遣送回去,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难道就这样,败给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吗?我不甘心。
后来打扫书房时,发现一张揉成一团的稿纸,打开一看,上面写道,焦桐你好。这是一封信,仅仅写个开头。他竟然思念到给一个死人写信,失败的感觉让我恼羞成怒,刚想将信撕碎,忽然在桌角又看见一个写好地址的空信封,收信人依然是焦桐,地址却是人间的门牌号。
我恍然大悟,那个女人原来并没有死,她只是离开他,去了别处。这些年来,战胜自己的也并非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而是活生生的思念,这更让我感到屈辱与不安。忽然,他的脚步声在我身后慌慌张张响起,我连忙将稿纸扔进纸篓,移动手中的抹布,去擦书桌上的灰尘,可落在心里的灰尘怎么办?
此后,我经常发现他瞒着我给焦桐写信,然后,匆匆忙忙地将信邮寄出去。每次,他拿着信去邮局,我都站在窗前,久久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人潮如流的长街上,心里好怕,会不会有一天,他连自己都塞进信封里,邮给那个女人?为了完完全全拥有他,我必须想个办法,于是谎称去旅游,来到那座城市,不,应该说是这座城市……滇红女子说到这里,紧紧盯着对面女子,如同凝望一张遗像。
龙井女子一脸淡定地说,没错,我就是焦桐,但你放心,我早已忘掉了他。她黯然道,希望是这样。说着,低头喝茶,茶却随着往事凉了。
窗外的雨停了,两个女人起身离去。在门前,她客客气气地说,我开车来的,不如送你回家。焦桐也没推辞,钻进车内,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从另一扇门闪进车内,发动引擎,将车朝着远处驶去。
雨后初晴,整个世界都婴儿一般干净。她将车开得飞快,不一会儿便离开繁华地带。焦桐刚要提醒一下,别开太快,便听她说,我有些渴,麻烦你将车后座那瓶雪碧递给我。
焦桐回头看了一眼,伸手去取,然而扎着安全带,手够不到,于是将安全带解开。就在这时,她忽然猛地一踩油门,车直奔路旁的一棵大树冲去,焦桐不由分说便从车窗飞了出去。焦桐伤势严重,流了很多血,不等送到医院便死了。她由于扎着安全带,只是受点轻伤。毕竟出了人命,交警刑警都找过她,这件事,她一直瞒着他,谎称自己在外地旅游。
半个月后,她回到自己城市,走到家门前时,不免有些紧张,不过,想到焦桐已经变成真正的遗像,早晚会被他忘掉,心里又浮现出一阵凯旋而归的狂喜。然而,当她打开门,换掉拖鞋,一脸炫耀地走进书房时,却发现墙上的那张遗像竟然不见,连焦桐古琴也没了。他从身后走来说,我已经想好,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你,就该全心全意待你,过去的事,不再去想,因此你一走,我就将琴卖掉了,很便宜。
她呆住,原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那么徒劳与好笑,可是他哪里会知道,处心积虑去杀一个人是很辛苦的,哪怕是为了爱。此后,他果然完全忘掉了焦桐,没有再写一封信。是的,他并不知道焦桐已经真正死去,他所忘记的不是鬼魂,而是过往,这样的结局她满意。
又一天,也是雨后,他们自驾出游,一路上说说笑笑,心情都很富足。忽然他说,我有些渴,你把那瓶雪碧递给我。雪碧?她的脑袋嗡的一声,惊慌失措地问,什么雪碧?你放哪了?他笑着说,不就在车后座吗?你要是够不到,可以把安全带先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