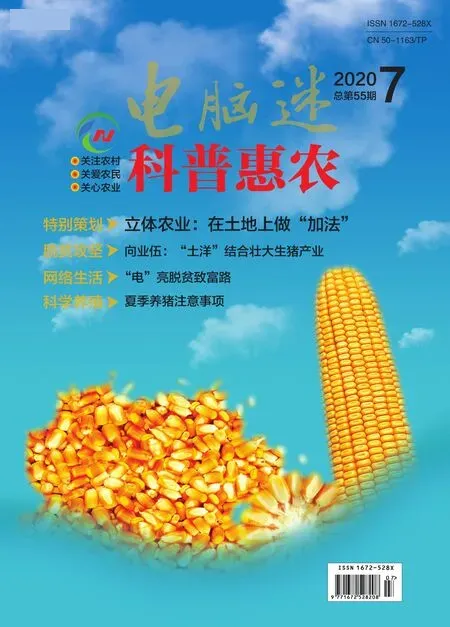收麦 麦收
本刊通讯员 阎仁厚
在平地里、在山坡上,到处都是黄色的波浪,像无穷无尽的黄云,翻滚在乡亲们的眼睛里、心窝上。阳光滚烫,田里的麦子先是杏黄色,烤上一两天,便是一地金黄了。
隔日早上四五点,父母就到了地头。父亲往右掌心吐口唾沫,握紧了镰刀,弯腰,右手一挥,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一片麦子倒下,像一群驯服的绵羊,匍匐在他的脚下。父亲抓起一把麦子,一分为二,大手一拧,就成了一条草绳,然后将一摊割倒的麦子拦腰兜起,又是一拧,一捆麦子就好了。父亲又开始重复这样的动作。当汗珠不断滴落在干燥的黄土地上,滋啦一声消失的时候,父亲身后是数不清的麦捆。
也有人不用这样辛苦,五爷爷就是一个,他正躲在阴凉处喝茶呢。五爷爷是木匠,颇烦干农活,今年他请了两个麦客割麦。麦客是甘肃人,听说从陕西东部渭南一带开始赶场,走铜川过咸阳,一路就到了宝鸡。
累了,父亲喝几口水,伸伸腰,又把自己还给了麦田。矮胖的母亲,紧张地挥舞着镰刀,可还是远远落在父亲的身后。她土黄色的汗衫上,是一圈圈白花花的汗渍。
父母接连一个礼拜早出晚归,终于将麦子割得所剩无几。他们找邻居商量碾场的事。我看见,那两个麦客,背着简易的铺盖,从五爷爷家离开。他们的活忙完了,要去寻找新的雇主或者继续向西。
碾场是一件需要多家协作的事务。大清早,就要将麦捆解开,平摊在碾场上,铺成匀实的地毡,任阳光将这地毡烘热烤干。正午日头正猛,拖拉机轰隆隆地开了进来,有时候是拖拉机机头带着个大碌碡,疯了似的在麦毡上撒欢,转着圈碾压。麦粒脱落,哔哔作响,有的麦粒一蹦几尺高。拖拉机驶入另一家的碾场时,这边几家人在一起,快速翻场,给麦子翻身,候着下一轮碾场。
挑完麦草,常常是傍晚时分了。试一试风向,父亲开始扬场。他铲起一锨麦子用力一甩,木锨在空中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麦粒纷纷坠在近处,轻的麦秸和杂物被风吹到远处或者浮在麦粒上面。戴着草帽的母亲,就用一把大扫帚掠去杂物。父亲手里的木锨飞舞着,不断有麦粒打在母亲的草帽上、身上、脸颊上,噼里啪啦作响。麦粒簌簌落地的声音,木锨刺啦啦铲地的声音,扫帚哗啦啦的响动声,汇成了一曲童谣,响在我的少年时代。
最后人们忙着将麦粒聚堆装袋,这是轻松的收尾工作。怕的是突然而至的雷雨,一声雷响,雨说来就来。于是人群就一阵慌乱,手忙脚乱地将油纸苫盖在麦堆上、装好的袋子上。等保护好麦子,才发现自己早已淋成了落汤鸡。
粮食搬回家之后,这一天的忙碌才算结束。腰酸背疼的人们稍微洗漱一下,就躺下了。一会儿呼噜声此起彼伏,比夏虫的鸣叫声更有气势。
次日天气不错,人们就一脸欢喜,要抓紧时间晒麦子。如果天阴或有雨,脸上就挂了乌云,湿麦子最易受潮发霉。
这些都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现在的夏收都是机械化,也就两三天的工夫。麦客消失了,一些过程消失了,许多人也老去或消失了。远去的木匠五爷爷就埋在了麦田里,听着年年响起的“算黄算割”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