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周畅先生
■陈永
20 18 年7 月26 日,厦门大学音乐系资深教授周畅(1931—2018)先生仙逝。同年第9 期的《人民音乐》,刊载了项阳撰写的《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追念先生》之纪念文章,该文中的追忆叙及周畅先生对项阳的因材施教培养过程,先生在厦大的研究生“四环教育”培养模式以及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和参政业绩等等。
我作为周先生曾经的硕士生,对先生也有不同于项阳师兄的感知和认识。在2019 年7 月下旬,我去广东大埔县大麻镇大留村考察了先生的故里,访问了周氏宗亲。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感知大埔县悠久的客家文化和近代的红色文化,以期从中寻得周先生仁德至善、爱生如子的修为所由,探寻先生心系家国、入世经世的思想之源。
所见、所闻,具象的回忆,抽象的意念,点点滴滴,奔涌心头。
一、恩
人生的成长,常伴有他人的相助。这种相助不寻常,很关键,有可能影响人的一生,成为其栖居在世的“意义源”。
我于1995 年考入厦门大学音乐系,幸列周畅先生门庭,成为他的硕士生。先生把我领进了音乐学术之门,今日弟子所忆所思,首要感谢的是先生的知遇之恩和点石之教。
那时候的信息交流方式大都只有书信往来,考生对于知识、人性的感知与悟化全都藉助书本。当年的招生名额甚少(记得那年厦大全校只招120 名,音乐系计划3 名,考上2名),能够考上的,大都经历过“悬梁刺股”的学习或是“程门立雪”的考验,我更不例外。记得4 月份复试那天,我们两个考生,面对五位老师“折腾”了一个上午。
当时,周先生说,师范大学毕业的音乐生文化课大都还可以,但在音乐专业方面还有欠缺。先生在面试时讲的话,我入学后便一一去执行。我在音乐本体的学习上花了许多功夫,尤其对音乐创作理论、键盘和声、即兴伴奏等方面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研究生没有开设的课程,我便参与到本科生中一起学习,曾在歌曲创作大赛中获得过奖励。
“爱生如子”,是我们在那个年代对师生关系的一种温情表述,也应该是很普遍的事实。
厦大艺术学院音乐系当年的两位导师(周畅、方妙英),带了3 个年级的研究生共8 名,每逢过节,同学们都会被老师邀请到家中去聚餐、交流,畅享美味,欣赏音乐。赏心乐事中,忘却了烦忧,免除了思乡之苦。指导小组的几位恩师,对学生总是笑眯眯的,长者慈祥的呵护,使我们倍感幸运和幸福。
我所见的周先生是一位敏于行而寡于言的学者,勤于治学,严于持教。弟子每当遇见的,又是慈面祥目、温言善心的先生。在学习期间,先生只给我有过一次正式的“批评”——他希望我改正我性格中的某一弱点。事实上,先生看得很准,他指出的弱点,正是影响我一生发展的“瓶颈”。当时先生说得很淡然,我听从了先生的建议并逐渐改正,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与周先生待人的仁善、委婉风格不同,师母田寿龄(1931—2019)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又是热心快肠的另一种风格。师母知道我的后方还有家口,会有不小的生活压力,遂给我介绍一些家教或社会音乐讲座等,伴我顺利熬过了物质贫困而精神充实的三年。①
1998 年6 月11 日下午,周先生给我上了毕业之际的最后一课,对我谈及理想、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诸多事情。先生对弟子的爱护、鼓励和不舍之情都在言语间,融化和温暖着我的心。先生给我的临别赠言是“胸怀大志,实事求是”。先生是这样为楷,我亦如此追随。此赠言,是我后来学业成长中的精神动力,一直鞭策和砥砺着我前行。
先生有“点石”之教,弟子非有“成金”之效,但师恩师训,当铭记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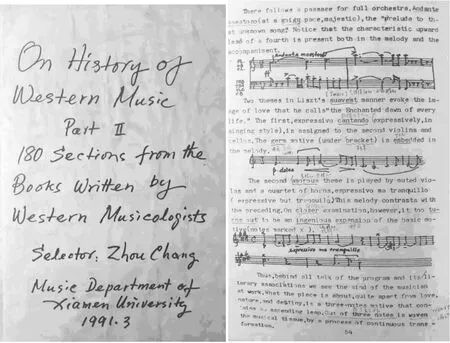
周畅编《西方音乐史》(英文版)教材封面、内页(手抄本,1991)
二、师
周畅先生的教学生涯和学术研究,其主轴是中国音乐史。他是1982 年烟台“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主讲导师之一。
自1980 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人才流动线路和学术版图较之前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于京、沪等学术重地,厦门显得有些偏塞,深度的学术交流相对较少,周先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过程中。先生把他最后二十余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厦门大学音乐系的管理、教学、培养人才的系列工作中以及社会音乐文化的建设事业中。
周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融汇了古今中西的综合体系。他在武汉音乐学院任教时(1956—1985)编写了《中国音乐史》,后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又编写了《西方音乐史》(英文版,1991),出版了专著《音乐与美学》(2001)、《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2003)等。
周先生给我们讲“西方音乐史”时采用全英文教材,使用英语口语教学,只有在遇到部分长句、生僻词汇和晦涩难懂的地方,才间插进少许汉语翻译。期中考试,先生让我们用英文进行音乐史的交流研讨会,同学之间提问、回答都必须用英语。那时,虽然我们的英语大多很蹩足,但在先生引领和鼓励下,学习都很投入,收效亦很大。其后数年,先生的多位弟子考上北京、上海等地院校的博士生,与先生率先推行的专业英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周先生研究音乐史学,始终以历史文献为据,结合深入细致的音乐本体分析,还借鉴西方艺术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了《胡笳十八拍》、福建南音以及现当代中国作曲家的系列作品。
周先生在论文《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1982)中阐述了对于中国音乐史研究和写作的几点看法,都是他多年思考和实践的学术问题。该题目,已经对先生自己的学术的广、深、精,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周先生的上述治学经验,早已施行到他的研究生培养训练教学中。他围绕音乐理论学科中的古- 今、中- 西、技- 艺等几种主要关系,构建了音乐理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融汇古今中西音乐文化于一体的教学体系。
“不精一技不谈艺,不通一艺不谈美”,这是先生时常告诫我们的。他认为,音乐理论研究是以史学为基础,通过音乐的分析,最终上升到音乐美的阐释。所以,音乐理论研究的基石是音乐本体(音乐技能、音乐作品),不管研究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还是西方音乐,离开了音乐作品,理论研究都是空谈。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这是先生提醒我们平时要多看多听,练就音乐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美,自在其中。周先生上课,总要带来各类音乐性的资料:有文献、曲谱、音像资料等。那时所用的音像都是盒式录音、录像带,大多是先生自己在家通过电视节目转录的,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拓展和辅助了教学。每次上课前,我们都要提前去先生家,帮他把这些资料扛到教室。先生为了教育,为了学术,用心、用力,在多样化的教学训练中,推进音乐史的学习和研究。
先生讲课,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音像听辨结合音乐分析,贯穿于中国音乐史的每一章节中,我记忆最深的是讲《胡笳十八拍》和白石道人歌曲。先生都会示范给我们大段的吟唱,还要布置我们课后背唱。每周都要背唱大量的中国古代歌曲(还有方妙英先生布置的民歌),当时感觉好苦啊!但是,对我们后来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甚至音乐生活,其影响都是深远的。
周先生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坚持古今贯通。对20 世纪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先生主要以重要作曲家及其作品,作为贯通历史的主线。当他讲解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时,大都是现身说法,感同身受。我记得,当讲到作曲家冼星海时,先生完全回到了他自己曾经饱尝艰辛的抗战岁月,出入历史现场,把冼星海及其音乐精神,讲出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质感”和“骨感”。先生带领我们泛听了冼星海的大部分声乐作品后总结认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黄河怨》具有歌剧咏叹调的性质。先生说,假若当时能有好的歌剧脚本和好的艺术环境,冼星海定能够写出经典的歌剧作品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先生对厦门大学音乐教育事业的设计、运筹和践行,付出与收获同在,业已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对音乐系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获得多项荣誉:1992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表彰其“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5 年获厦门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1997 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励,等等。②

广东省大埔县大麻镇大留村周家围屋

怡和书屋
三、先生
“先生”这个称谓,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对于周畅先生来讲都是名实相符的。他是老师,是仁者,也是入世经世的知识分子。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至于至善”,对照于此,弟子仰视周先生的一生亦正是在此勤、善的路上躬行不息,更以勤、善的修为要求殷切教育学生。
入学之初,先生对我的第一训诫是要“自强不息”“三年学出五年来”。先生对学生严中有爱,对身边的人,不分贵贱,都充满仁德善心。
仁善的周先生,自带不怒而威的人格。我总难忘,先生上课时那宽仁和悦的颜面,还有其后给人的敬畏感。先生讲课中,时有停顿,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的间歇,先生会站起身来,缓缓侧身,眼光向窗外的海边望去,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在学生每次担心答问出错时,先生却并不问责,只是点点头,微微一笑,继续讲开去。这颜面,胜似千言万语,无形中催促着我们加倍努力。
在校学习时,我所理解的周先生更多的是一位教育家、学者、士人、仁者。直到在他的追悼会上看到学界之外发来的电唁和前来吊唁,有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人士等。原来,先生作为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致公党主委,参政议政,为国家为社会献策献力,做了很多经世有益的事情。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周先生在每年政协全会上,都要提出一些提案。在音乐方面,周先生曾提出加强建设中央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等国家级音乐机构的提案,分别被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采纳;提出抢救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珍贵古乐的提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采纳。其他各方面的提案,还有《关于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立法的建议案》《对引进外资直接投资应能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案》《关于正确引导消费者选用国货案》《关于拓宽对外宣传渠道的建议案》等。③先生代表致公党为福建政协的特别提案《既堵又疏,做好新移民工作》,获得1999—2001 年度福建省政协优秀提案。④先生还撰写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稿,如《在危机中把握引资机遇》《把握内需幅度,做到投资适度,争取效益优度》等,发表于《人民政协报》和《世纪之光》。⑤
先生在教育过程中,亦贯穿着经世思想。课堂上,除了音乐的专业施教,还有更多的公民教育、人格教育。他常给我们讲,艺术家应该以多种眼光看世界,适当自然地关心和触及政治,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有助于艺术学科的观照性发展。先生还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延伸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他关注当代,褒扬和研究那些书写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音乐家及其作品。从先生的学术成果来看,他早期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与美学。进入新世纪后,先生对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非常关注。他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2003)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和评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歌曲,如《我和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中国》《爱我中华》《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等。
周先生的艺术政治观,他的家国情怀,与他所经历的变革时代、他的家族起落和个人学养等都密切相关。先生祖籍河南,晋代南迁福建,再后又迁至广东梅州的大埔县。如今的大埔,青山绿水中,掩映着白墙灰瓦的客家老式围楼。大埔客家人所建的新式屋楼都会有一个楼名,其命名中总包含有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些字词,如:德、贤、福、安、和、贵、贤、良等等。周先生家的老屋始建于1918 年,名为“怡和书室”,也是传统的围楼结构,现已成为梅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围屋正门两边的墙上,竖式书写着八个大字“怡情悦性”“和气致祥”,右左相对应,“怡”“和”之间,彰示出房主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
周先生曾经就读过的大埔县大麻中学,也是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的母校,此校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优良的教学质量,历代人才辈出,是大埔县如今保存着完全中学建制的少数几所乡镇中学之一。从大埔县深厚的文化传统及其有序的古今文化承递进程中,我也看到了周先生仁德修为经世思想的所来与所去。行走在先生故里,我所理解的周畅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教育是礼乐相成、知行合一式的传统教育:乐教——礼乐同辉;文教——大文化传统;行教——经世致用。
在《中国当代美学名人志》一书中,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周畅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政治抱负和审美趣味等,其中有“美学答问”10 问,第3 问是“我对当前美学走向的看法”,周先生的回答是:
古往今来,美学都是多走向,此乃必然,今后亦如此。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走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外古今之精粹,以无限宇宙的广阔人生实践为根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构想,独出心裁,走自己的路。⑥
这段话,综其大体,可看成是周先生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观、学术观和知行观的概括性表达。
周畅先生之于我,可谓面谕三载,示教千则。而今我渐明白,是一位客家贤达点化了一个土著巴人,缘远而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之学途,当涌无尽时……
那风,还在厦海漫步;
那云,仍在鹭岛徘徊;
先生,永在至善的路上;
师恩,长留弟子的心中……

1997 年,周畅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
①修改此稿时,又添悲戚:师母田寿龄老师于2019 年9 月15 日在厦门仙逝。先生与师母,在天堂相聚,依然持续着他们的仁善,化育桃李,恩泽学人。
②陈京元《致公党人的风采》,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 年版,第74—78 页。
③⑤陈金元《致公党人的风采》,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 年版,第77页。
④《福建政协60 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 页。
⑥《中国当代美学名人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第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