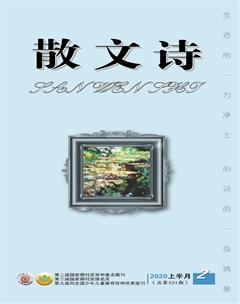云上赛拉隆
梅里·雪[藏族]
赛拉隆:风吹吐鲁掌
我们钟爱的眠床是开满金露梅的草地。放下身段,仰天平躺。把浊体交给路过的云、路过的风,它们替我打扫内心的沉、灵魂的重。可以嗅牛粪的草根味,可以饮青草尖上的露水,可以聆听牛啤、马嘶、鸟鸣。
诗人扎西尼玛借用牧人的望远镜,寻找他多年前丢失的羊群。
牧人臧阿卡顺手指给他,被风赶着远去的云说,那就是个传说。
我相信,草原一定隐藏了诗人的秘密,依旧云遮雾罩,一片苍茫。
仁谦才华爬在牛粪前,他说,这是童年的味道。
倏地,草地上的花一下炸開了,声音清晰而柔软,像他的笑容。
闭上双眼,整理好心情,让拂过面庞的风,清空所有浮世的欲望。此刻,花神跌坐于金莲花,一眼看开这万里浮云。
笑而不语……归去,回望。山神的峨博也和我们一样,被风吹着,被雾裹着。
吐鲁掌,正抱云而眠。
赛拉隆:鹰巡吐鲁坪
云停在坪上,赛拉隆在云上。
牦牛的影子,绿绒蒿的影子,鹰隼的影子时隐时现。
一声迅疾的鸣叫衔住了草原的空旷。
一只鹰回到吐鲁坪,回到虚无的真空,像谁扔进时间深处的一点响动。它会碰响什么?
一圈一圈逡巡、探究,一群人的到来是新鲜,是陌生,是惶恐,与无人摄影机对视,同样是飞翔,终究谁被摇控?谁没有了自由精神?
鹰靠翅膀高过山顶上的我们,而人,想要飞,只能用干净的灵魂。一声啸叫,天空苍茫茫地倾斜下来。一株雪莲花,哑默的根须,稳住了赛拉隆108条漏斗型的山谷。
山隐于云,云驮起鹰。
一溪流经草地的雪融水,勾勒出天穹的浑圆。
我们走进云深处,感恩驮着吃食负重而行的马匹。感恩牵马的老人,忍受着生活在夹缝中的压力和内心的疼痛,依然藏起生活的重。
向上跋涉。你说,这片草原有你的苍凉,也有你的幸福。
我们坐在坪上,看见的每一片云每一丝雾都是你迷茫的一生。
守望今生的赛拉隆,鹰翅大开大阖的山川,也是你一生难舍不弃的暖意天堂。
吐鲁沟:天窗眼
世界被绿淹没,必须从肋骨上打开一扇窗。必须打开天窗说亮话,让峡内峡外的风,有自由通行的出口。
幽闭的黑,阴谋,阻挠,都要被光阴戳穿,暴在光亮处。
从一孔,我看见你内心的明净,也看见天空的空。
也许,日子该有酒,浓得化不开的绿就是肺叶的琼浆,那倒吊的瓶子,是酒神的器具还是观音的净水瓶?谁来看,谁知道!
一滴,万物就睁开眼睛。
二滴,佛说,要有光。
三滴,赛拉隆高山草甸的雪山就映在眼前。
绿海太大,幽谷太深,天窗一开,一泓明亮竟在人间低处。
赛拉隆:盆子沟
进入盆子沟之前,一场落雨是隆重的。
洗你,濯我,将灵魂清洗干净才能进入植物的王国,去看众生。
一山草木,回归风烟俱净,
一株迎客松,独站沟口,迎送往来浮云。
赛拉隆,我从容接受这浇喜的礼遇,携鸟鸣的轻盈,带着草木的空灵走近你,拜访从参天古树中起身的大德支家佛,怀想和敬意被湿漉漉的空气收藏。
我们说着元宝形的聚宝盆,人间的沟壑也已将苍茫过往藏起。
青砖,雕花,古旧的木楼,蹲在时间深处,岁月只剩下一座府宅的骨架。
獭拉的叫声,喊住了雨,三户村民的炊烟,将我拉弯的思绪拽回人间。盆子沟,宽大幽深的胸怀里,满山苍松书写寂静。
村庄里的蒲公英举起了小伞,挂着的露水珠一颗比一颗明亮。
赛拉隆:皮袋湾简笔
记下西大寺、云山寺、妙音寺、鲁土司衙门佛堂、支家佛、马家佛、杨家佛——
它们是皮袋湾存在的依据。
记下紫桦图、几辐条池、大文国、三岔、寺掌沟——
这里紫桦只有图,大文不是国,八辐金轮的池水泼洒整个山谷。
记下皮袋湾河流,从水经注流经千年,带着母亲的歌谣,流进黄河。
记下,满山谷的野——野山茶,野蔷薇,野葡萄,野芹,野草莓,它们被松柏托举着,或被浅草暴露出来。每一种野都怀揣治病救人的祷词,深植大地。
记下铜钱峰、金蟾衔草、迎客松、鸟鸣滩、馒头山、五行树……每一景的腰间都斜挂着一条绿松石的项链。
记下石头砌墙、篱栅院落、田畴毛葱、嫩芽时蔬和半山腰的疏疏人家、深谷幽居,少了闹市喧嚣,青山相随,花香相伴,活成自然人。回归渺小,像青苔,像小草,也像山野人家种的小毛葱,带着岁月的清明简淡。
记下野花,有着低调的、不张扬的美,拾花捡夏,一个人的心性也会纯净高华。
记下野鸟鸣唱,啾啾、呱呱的叫声异常生动,让你我的心柔软到感念山水光阴的深情和朴素。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整个人被绿淹没,连同灵魂,却怎么也写不出赛拉隆沧海一滴的葱茏。
赛拉隆:西大寺印象
四百多年后,无常世事留给人们去说吧——罗刹女仰卧的后山,阳光暖照。绿植醉云,也醉山间的几只山羊。
殿前两棵檀香树,花絮满缀。怀着岁月的秘密,醒悟如佛。
煨桑炉,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大肚能容的桑烟,时浓时淡,更像一个人的无常人生。
一座寺,记住一段风云;一个人,还原一座寺的历史。
三盏酥油灯,无己,无物,燃烧着院落的寂静。
几卷经书,数根捻好的酥油灯芯,与一个孤独的人相伴就是半日光阴。山太深,光阴太老,守住一座寺的人,慢慢活就好。
走远了。一回头,那个驻寺的老人,担着水桶去挑水,摇.摆的身子,像是与寺前那棵历经沧桑岁月的檀香树交换着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