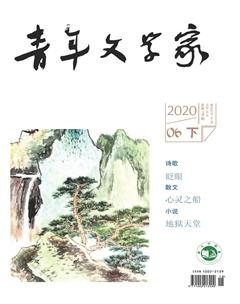论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凉
摘 要:“慷慨”指情感浓烈激越,体现出建安文人立身处世原则中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悲凉”即时代氛围和文人心态的比喻性描述,是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冲突后建安文人对于个体自我价值的内视。本文以“三曹七子”的诗歌切入,力求回归文本,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特征。
关键词: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文学自觉
作者简介:杨芳,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8-0-02
建安文学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建安文学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尤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他们以直抒胸臆之笔描写艰难时世,志述翔实,以“风骨”著称,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在文学创作上的自觉意识。“慷慨”指情感浓烈激越,“悲凉”即建安前后时代氛围与文人心态的比喻性描述;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特征体现了建安文人个体意识的增强和文学主体性的丰富,蕴涵着他们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个人价值的看法和离乱社会的深厚关怀。
一、“慷慨”——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文学的变化、兴废与社会发展共变。建安文学的断限起于曹氏迎献帝于洛阳(公元196年),止于曹植下世之际(公元232年),此三十余年间于士林展露头角的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重新思考进入仕途的可能性,表现出对于建功立业的极大热忱;同时作为汉末魏初动荡社会的亲历者,文学作品中又裹挟着悲凉气息。
“慷慨”是建安风骨的本色。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3]慨叹政治理想、人生苦短,曹植“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诗》)勉励友人乐观向上,又以“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野田黄雀行》)[3]唱和亲友往来;建安诗歌言及“慷慨”者不在少数,“雅好慷慨”显然代表着建安文人趋同的审美追求。而“慷慨”背后又内蕴着浓厚的悲剧色彩:王粲《七哀诗》“慷慨”董卓诸乱下社会的失序,生民的悲苦,对明主贤臣的渴望;曹操《 蒿里行》、《薤露》写对人民颠沛流离、社稷尸骨盈野的哀恸,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叙述徭役的不堪重负,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刻画孤儿的悲惨遭遇,曹植《泰山梁甫行》悲叹海边民众的贫苦生活。此类作品秉持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情感上浓烈激越,显露出建安时期特定的情绪,均可称之为汉末实录。“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激发了士人浓烈的忧患意识,故建安诗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1]而曹氏集团的崛起及其表现出的对贤士的亲善态度,又吸引着“建安七子”等文人志士積极投身于曹魏正统观的改造与重塑。
举荐制是西汉传至魏晋的选官制度,原为士人进仕的正常途径,而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迭握朝政,朝廷“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王符《潜夫论》),举荐制成为世族门阀把持政局的特权,寒门素族退而选择“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徐干《中论》序)[4],或通过“扬名养誉”一争跃龙门的机会。汉末三分天下后,谋求天下正统的合法性地位成为魏蜀吴三家需要迫切解决的命题。然曹操《求贤令》一出,曹氏政权“唯才是举”,似乎又让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拨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4]的特权,看到了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可能,而作为“孔子二十世孙”的孔融、出生名门望族的王粲等人便是曹氏需要笼络的重点对象。建安七子在归属曹魏之前或名重当时,或为他朝仕臣,或潜身穷巷抱节自守,虽出处不同却抱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试读王粲《从军诗·其一》: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3]
全诗抒发了作者跟随曹操征讨军阀、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语言清峻、内容壮大;王粲《从军诗》五首可谓是“七子”中“慷慨”壮志的代表诗作。而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曹氏父子更是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植《白马篇》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他们于鞍马间赋诗作文,尽显英雄本色。结束北方割据后,曹魏政权实力最强,曹操对外征战神武,对内任人求贤,以此团结了大批文士为天下一统、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而慷慨赴死,乃至“轻官忽禄”的徐干之辈最终也应召入世。建安前期文人的出处进退心态并非汉末之际受“党锢”影响而生发的犹豫心理,反倒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之气概,这也正是以军功起家的浊流曹氏需凭借以文化传家的清流名士来巩固人心统治的结果。
二、“悲凉”——个人自我价值的内视
“悲凉”是建安风骨的底色。汉晋之际的军阀割据激起了士大夫阶层对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怀,使之承担起兼善天下的道德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因此他们积极进取,关心当下政治前景,以谋求实现个人价值的名位,故其建安前期的作品大都作品洋溢着刚健之美。然而邺下文人虽受到曹氏父子的礼遇却大都未能进入曹魏集团的权力中心,以致建安后期多以文学侍从的角色铺写应制之作,充当着政治的缘饰品。仕途经济的受挫与文人的理想宏图所产生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再加上灾荒、瘟疫所带来的生命的焦虑,推动着建安文人陷入了精神的消沉并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价值。
“悲凉”也是对建安文人精神气质和时代氛围的比喻性描述。“悲”是心理上与现实产生落差的一种意绪,“凉”是生理上对温度的一种感受,是可触摸的生命消逝的直观体验,这种由生理到心理再到生命所散发出的悲凉感,建安诗歌中屡见不鲜。曹操《苦寒行》云:“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3],阮瑀《诗》云:“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3]王粲《七哀诗》云:“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3]建安文人有意创造出形容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萧索意象,哪怕是再慷慨激昂的作品也不可避免的染上忧郁色彩,徐干《室思》、曹植《吁嗟篇》、刘桢《赠从弟》等诗作,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悲凉意绪的流露。北方地域苍茫、物候苍凉,而战乱不息,疾疫肆虐,人命危浅,客观环境的“凉”与主观心境的“悲”相契合,文学作品作为“心灵的外化”自然会流露出一股沉重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上升到理性层面,其实更是建安文人对于生命意识的悲凉。
继“百家争鸣”之后,汉末儒学独尊体系的坍塌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学界也因此将建安文学视作文学自觉的滥觞。建安前后,儒家大一统思想不再成为世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而新的正统观念还未建立,在对儒家人生观、价值观持有怀疑态度的情况下,人们逐渐突出自我意识,尤其是对生命有着执爱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生命受到非自然死亡的威胁时,他们不再一味地鼓吹伦理道德,而是转向把握现实人生,即使身在魏阙,却奉行着及时行乐的原则,以此冲淡死亡的伤感。
当死亡的恐惧近在咫尺时,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似乎是出于人类生理属性的本能,但是人类觉醒之后,面对生存与死亡,却开始了思考生而为人的终极价值。建安文人作为较先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思考人的生命意义时,表现出了两种态度:一是增加其生命的密度,消极地游戏人生,以求白驹过隙般的生命旅途过得精彩愉快;一是增加其生命的厚度,积极地立德立言,以此彰显人格的独立。桓灵之际针对士林精英的党锢之祸其实已经在魏晋士人的心理上使其对政权和儒家正统产生了间隔和疏离,而建安文人之所以归附曹魏,或是由于之前儒家“仁以为己任”的内在精神驱动,或是出于维持和改善当前生活状况的需要,亦或是屈于政治当局而被迫入仕,但是一旦他们所选择和相信的仕途经济长期受挫,他们只会更加主动的回归依附曹魏之前的心理状态甚至是自动调节与统治阶级的心理间距,而及时行乐、实现人格独立,就是这种心理距离的产物。
及时行乐的心理多在其公宴诗中有所体现,透过它能窥见建安文人建安后期主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陈琳曰:“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3]曹植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3]王粲曰:“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3]以上援引诗例足见公宴诗在内容上多叙写君恬臣嬉、友朋相游,主人公极为重视个人短暂之人生、内在之享乐;而情志上表达的却是壮志难酬、生命易逝的沉痛与悲观,所以他们选择了将追求享乐与表达个性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标杆。应玚、刘桢甚至还有《斗鸡诗》、《射鸢诗》记录日常游戏心态,而明白、晓畅的诗歌语言更是直接展现了诗人对于纵情的认同和宣泄。故《文心雕龙·时序》言: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
建安文人重视感官愉悦的尽兴放纵并非一人之独自行为,而是有组织的群体性聚会,他们重视个人生前的生命体验以及现世的享乐风气可见一斑。
人的价值包括生前和身后,另一种态度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借助“不朽”事业来延续精神的长度。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
面对生命无常,曹丕认为只有志于“不朽”事业,才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献身于著书立说在建安文人看来不仅仅是为了留名后世,而是划定一片精神领域用以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并试图在依附当权以维持当下生计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独立的人格,以接续汉末“党锢之祸”后兴起的独立之精神。汉晋之际是为士之群体自觉向个体自觉的嬗变时期,建安文人承上启下,由此开始了文学自觉的自我实践;他们敢于正视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秉持着忧患意识的同时又自觉彰显了自身内在的个体价值,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理性思考和呈現。
三、结语
建安风骨的“慷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得以实践的文学表现,体现的是士大夫立身处世原则中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而建安风骨的“悲凉”是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冲突后建安文人对于个体自我价值的内视,包裹着建安前后特有的时代气息。本文简单言及对建安风骨总体特征的认识,就此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M].上海:中华书局,1962.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