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绍棠“乡土文学”的形成与主题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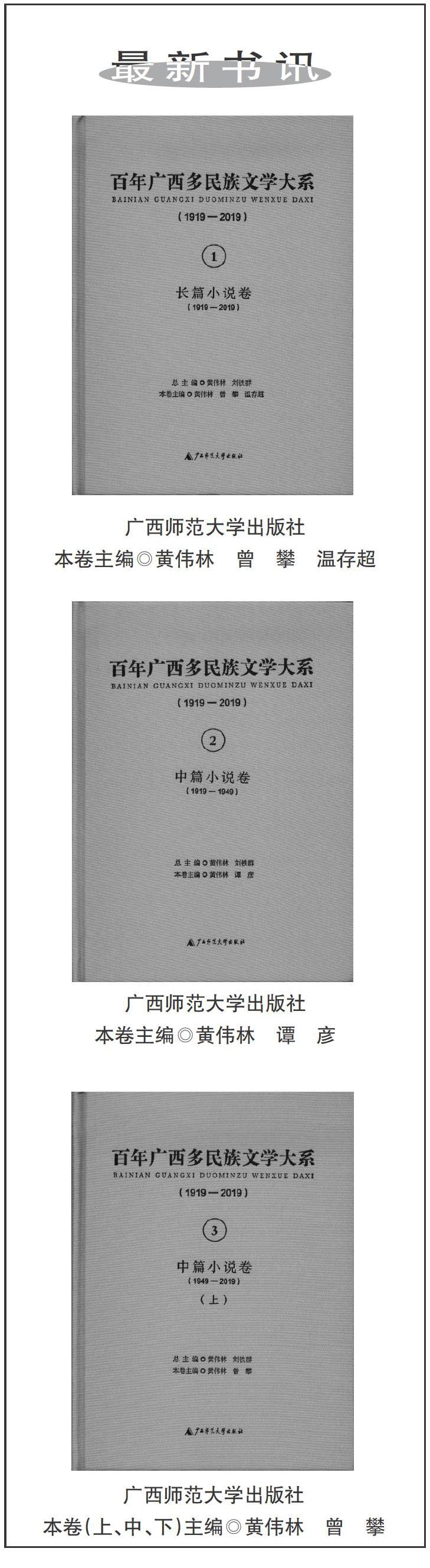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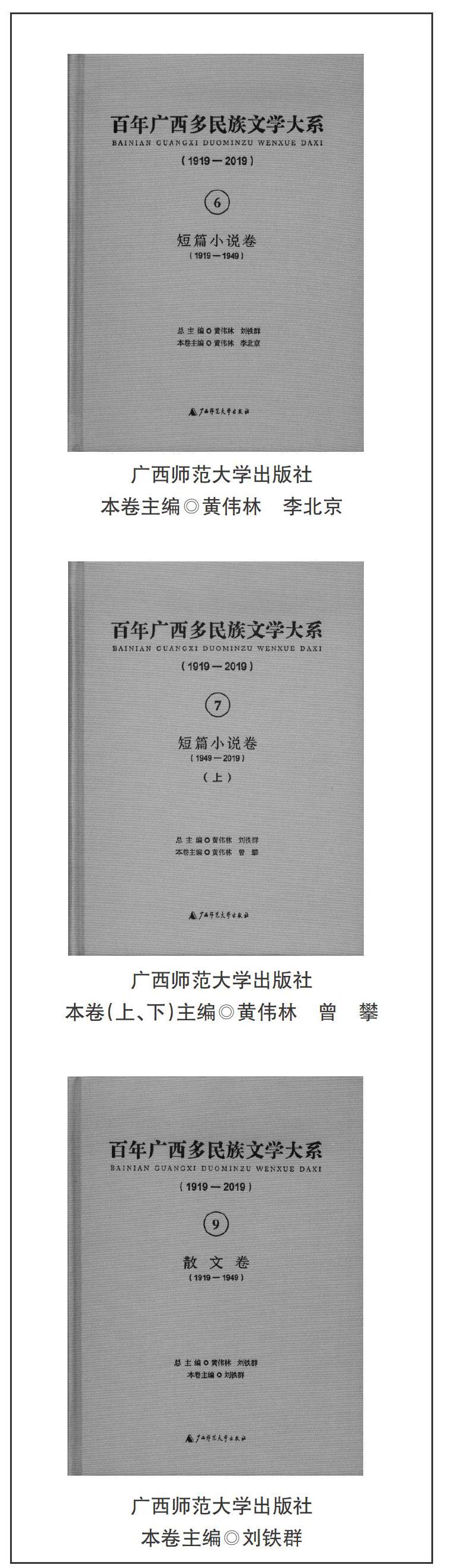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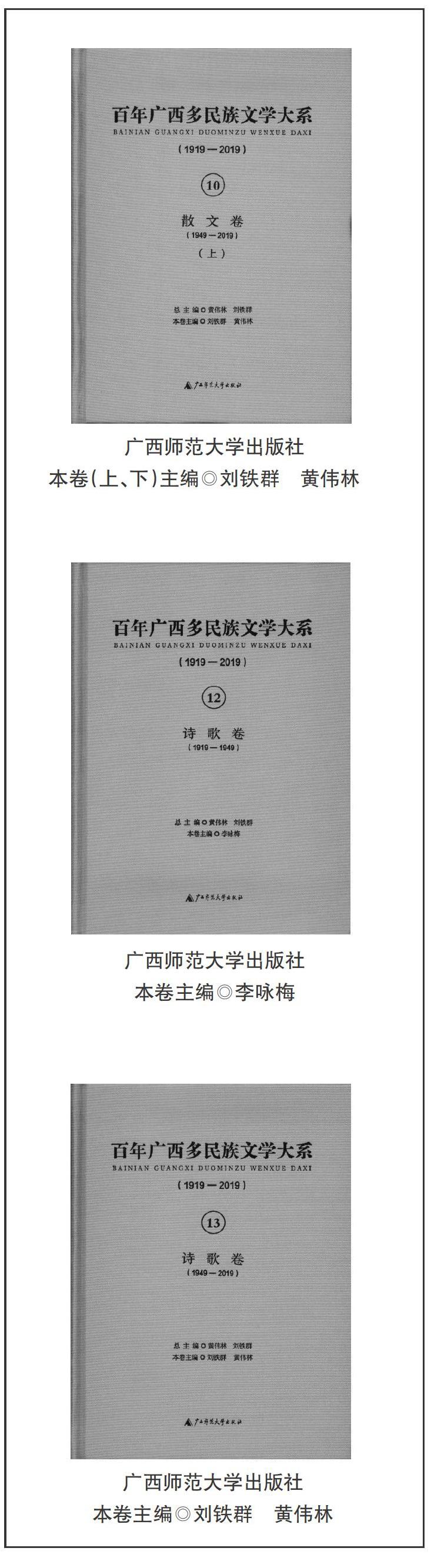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绍棠无疑是伴着五星红旗,在中国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文学新星。他历经风雨,在丰沃的生活原野里,精心而勤劳地浇灌着艺术的“青枝绿叶”,终于使他绽开了美丽的花朵,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泥土的馨香。这就是刘绍棠和他新的“乡土文学”的丰收,并带动一大批作家,从而开辟了一条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新“乡土文学”及“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艺术道路。
一
“乡土文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说,“乡土文学”是相对“城市文学”和“洋气”而言的,其意近似于我们常说的“民族特色”。狭义上说,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是鲁迅在1935年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对“乡土文学”的定义: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己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根据这则定义,鲁迅先生首先强调的是“隐现着乡愁”,他认为凡是身处北京而追忆故乡的事情、抒发自己乡愁的,“无论是用主观或是客观的方法,皆可称为‘乡土文学”①。他以此为标准,收录了蹇先艾、冯沅君、裴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人的小说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创作发轫于五四时期,也是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②。在鲁迅创作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如王任叔、彭家煌、台静农、蹇先艾、许杰、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魏金枝、徐玉诺等人。他们的作品或描写封建统治下农村的闭塞、落后、破败、野蛮,或表现乡间劳动者的生活疾苦、思想麻木、畸形人生,或展現乡村农民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下,乡村地主阶级和农村有产者的衰败、乡土文明的衰微和崩溃。这些作家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蹇先艾表现贵州地区的乡村,彭家煌坚持湖南地方的书写,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许杰等人则着力描绘浙东地区的风貌。
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出现了以沈从文为核心,废名、萧乾、凌叔华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他们的创作被丁帆称为“乡土浪漫派”小说③。同时还涌现了以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人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他们从东北流亡至关内,深感故乡沦陷的伤痛,但是他们的创作并没有展现共同的地域色彩。
“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两个乡土文学流派,同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在50年代走向成熟和活跃期,横跨了现、当代两个文学时期,但两个流派风格迥异。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作家,作品多描写白洋淀地区的北方水乡风貌。其成员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的写作都受到了孙犁的影响,文学风格和审美趣味大体相近。他们着力体现“白洋淀”水乡的“田园牧歌”风情,淡化了战争烽火的背景,创作风格清新、朴素、柔美。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品。而“山药蛋派”则是以赵树理为中心而形成的乡土小说流派,主要成员还有马烽、西戎、孙谦、束为等人。这些作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有着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从事文学创作后,与山西地区的农村生活也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贴近山区农民的生活,以农民的眼光来观察、认识和表现生活,善于运用百姓习以为常的生活俚语、俗语,以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传统为资源,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显著特点。
但是50年代中后期,“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柳青、周立波等人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流派。直到80年代,以刘绍棠为代表,形成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这是我国乡土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二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1949年十三岁时发表第一篇小说《邰宝林》,从此步入文坛。50年代发表了《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的桨声》《夏天》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然而,50年代末期受到历史动荡的影响,他被迫搁笔,但是始终未停止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十年动乱结束后,他于1979年发表《地火》《鸡鸣风雨女萝江》等长篇小说以及《地母》《含羞草》《藏珍楼》《芳草满天涯》等短篇小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激情在被压抑二十余年后,终于在80年代得到释放,迎来了个人创作的高峰期,形成了自己明确的创作风格。
80年代,西方意识流、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想涌入,一大批作家纷纷效仿。但是,乡土题材的创作始终未能湮没在此起彼伏的文学更迭潮流中。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讲,自现代文学伊始,乡土文学就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新时期仍有像浩然、林斤澜、汪曾祺、刘绵云、王梓夫一样的新老作家,坚持农村题材的创作,保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他们的坚守,也巩固了刘绍棠坚持乡土文学创作的信心。刘绍棠积极深入农村生活,于1980年夏秋两季,赴吉林、河北、湖北等多地调研。行程结束后,他发出了“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④的呼吁。与此同时,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于当年《十月》第3期发表。小说受到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其中体现的民族风格、乡土民情,为人称道,并且获得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
刘绍棠在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提出了乡土文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他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明确提出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这一主张:
现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一批水平很高的作品,实力很强的作者,已经头顶着高粱花,跃上北京的文坛。今后,只要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决、更追求,师承前辈而有所出新,借鉴外国外地而为我所用;那么,有的写京东平原,有的写京西山地,有的写长城塞北,有的写近效菜区……热烈地拥抱我们的地母,北京的乡土文学必将在1981年形成、发展、繁荣,而得以公认。
在这之后几个月,他连续发表了《乡土风情画》《建立乡土电影》《乡土与创作》《县志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一大成果》《建立冀东的乡土文学》等短论,反复论及乡土文学问题,强调“继承和发扬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的浓郁的地方特色,建立乡土文学”⑤。并逐渐扩大这个主张的内涵,提倡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
刘绍棠的主张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获得了很多人士的支持和响应。1981年9月,雷达和刘绍棠两人通信,深入探讨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及发展方向。刘绍棠在信中说:
乡土文学的发展和提高,对于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画廊,对于提高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发展艺术风格流派的多样化,都很有实际价值。而这种对创作的实际价值,正是我思考得比较多的。
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刘绍棠阐释了他所主张的乡土文学的理论内涵,提出了乡土文学写作的五条原则:
一、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
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
三、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
四、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五、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
对于这五条原则,他又在《〈蒲柳人家〉二三事》作了概括说明:
土气的作品,我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我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续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命运。
此后,随着全国文艺界开展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刘绍棠的创作及其理论逐渐被人重视起来。
《蒲柳人家》这一小说的成功、乡土理论被文艺界重视,增强了刘绍棠的创作自信。他秉持“在自己最熟悉的乡土上打深井……永远坚持定写农民,写田园牧歌,写光明与美”⑥的信念,向乡土文学的纵深突进,坚实推动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发展。同时,他不断奔走实践,积极推动全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并亲手编辑出版了《乡土》小说集。他凭借数百万字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在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
在运河畔生活了几十年的刘绍棠,同运河的劳动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本人曾这样概括小说的主题:“我的所有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讴歌劳动人民的美德和恩情。”⑦正是以此为主旨,他的作品从多侧面反映了运河的历史变幻,对运河两岸“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作了生动而深情的描绘,挖掘了运河两岸人民特有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刘绍棠的“新乡土文学”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多侧面反映了运河的历史变幻。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北运河两岸的苦难历史和时代风貌:死气沉沉的运河滩上,传出的灾难深重者反抗的呐喊(《瓜棚柳巷》);漂泊在大小码头的船夫、艺人、工匠的呼号,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荇水荷风》);蒲柳人家的英才,满怀民族解放的激情,运河两岸燃烧着抗日的烽火(《蒲柳人家》)。也有体现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作品,石在、梅畹贞(《两草一心》)及洛文、青风和黄梅雨(《二度梅》)等人的坎坷经历,饱含了时代动荡给个人造成的深重灾难;蛾眉婚姻爱情生活中的波折历程,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病态、时代的症结(《蛾眉》)。《小荷才露尖尖角》中塑造了两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形象:大学三年级学生俞文芊,从一个土头土脑、憨气十足的小伙子,成长为懂两门外语、掌握了一定专业知识的未来建设人才;心灵手巧的花碧莲由农村庄稼能手,变成京花联合衬衫厂的熟练工人。农村的伟大历史性变革,也使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新组合,变得错综复杂。而在这场变革中,传统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造就出新时代的风流女性(《十步春草》)。
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叙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其着力点建筑在一个民族的自强意识上,表现了抗日烽火与女万元户的忧患意识。半个世纪以前,北运河平原上的抗日志士为了暗杀大汉奸殷汝耕而自发地组织起来,出生入死,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奋斗精神。关省三是通州的巨富,虽处在日寇追逼的淫威下,却依旧不愁吃穿,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苟且偷安的生存方式,发誓与日寇汉奸不共戴天,毅然铤而走险,因而牵出一系列人物,展示了烽火年代的热烈斗争场面。而80年代的香河县女二道贩子住的是几进几出的新房,用的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日本面包车,她同样也不满足于目前的生存方式,她在不断地竞争的同时又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在她身上,又折射出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个性之光。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交叉描绘及深度开掘,表现了作家的恢宏气度,给人一种悲壮的历史纵深感和高度的审美情趣。
刘绍棠小說内容立足于“运河故乡多灾多难和多事的土地”,塑造人物形象则以“反映我们祖国的幸福生活,可爱的人物的模范的故事”⑧为己任。他在《关于小说民族化的浅见》一文中说:
小说创作充分表现中国人民的民族的和革命的崇高理想,奋斗精神、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掌握和运用中国人的健康优美的民族语言,描写和展现中国人的美好的风俗习惯,是小说民族化的核心和基础。
于此基点出发,作家深入挖掘了运河两岸人民所特有的人性美。
首先刘绍棠作品中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以“侠义、忠烈、坚贞、聪慧、善良”为特征的形象系列。这些普通平凡的劳动人民构成了不朽的民族之躯,他们身上彰显了我们民族崇高的精神品质。《蒲柳人家》里的周檎、望日莲、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柳罐斗、吉老秤;《瓜棚柳巷》里的柳梢青、柳叶眉父女;《花街》里的叶三车、蓑嫂;《草莽》里的桑铁瓮、桑木扁担、陶红杏、叶雨、云锦;《蛾眉》里的蛾眉、唐早春;《鱼菱风景》里的邵火把、杨天香;《小荷才露尖尖角》里的俞文芊、杜秋葵;《烟春四五家》里的蔡椿井、豆青婶。这些卓然而立、栩栩如生的人物,都是作者精心刻画的结果。
《蒲柳人家》的一丈青大娘是一位劳动妇女。她虽年过半百,但有胆有识,豪气逼人。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英雄那种舍己救人,慷慨大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美德。她不顾危险,从弹坑里把邻家的童养媳望日莲扒出来;看到望日莲遭受毒打,敢于冒险援救;为了能使望日莲跳出火海,心甘情愿陪一笔嫁妆认她为义女,并竭力成全她的婚姻,都是这种美德的表现。《草莽》中的桑铁瓮父子,是同一丈青大娘一样,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人物。不同的是,一丈青大娘心软重“情”;而桑铁瓮父子是“受人一饭之恩,当以万石相报”,重“义气”。花船上的月圆姑娘在沦落风尘之前,曾于鹅毛大雪之际,把讨得的饭煮熟,送给被困于破庙中的桑家父子。当他们知道恩人受骗被典卖到花船之后,桑铁瓮一拍大腿:“知恩不报是小人,咱们得搭救她出火坑。”凑不齐六十块大洋的赎身钱,桑铁瓮瞪起眼睛一跺脚:“头插草标卖了我,也要赎同月圆姑娘。”桑木扁担急中生智,找到骗卖姑娘的白苍狗子算账,又挟持白苍狗子姘头来到白家大院,逼迫白云娘子拿同银圆,终于将月圆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作者将一丈青和桑家父子的侠情义胆,放在特定时代、典型环境的背景之下,就不单单是一般的同情心和普通的江湖义气,更多的是出于对同胞姐妹苦难命运的关怀,出于对黑暗势力的愤恨,因而更能反映出民族性格的传统美德和本质特征。
“中间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也表现出了一种民族性的净化与进步。像《蒲柳人家》中的云遮月,《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花街》中的玉姑,《乡风》中的金铃兰,《瓜棚柳巷》中的花三春。她们身上虽然还残存着种种剥削阶级的恶习,但是,在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她们终于成长为一个真正具有崇高精神的中华民族妇女。《瓜棚柳巷》中的花三春性格复杂,她从小在“放鹰”的女人堆里长大,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性,她和柳叶眉放刁耍泼,割情舍义的行为足以令人发指。但她对爱情的忠贞,却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矢志不渝的传统美德。在生活的磨难中,她终于看到了柳叶眉身上那种闪烁着民族优秀品质的性格光华。她在和贾二哈巴、汤三圆子作决死斗前,让摸鱼儿捎给柳叶眉的遗嘱,表明她认识到了生活的真谛,深受民族伦理道德感染。从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道德力量的强大威力。作者自己曾说过:“人有人性,人有人情,因而就必须在作品中写出人性和人情,没有人性和人情的作品,没人爱看,不如不写。”⑨人性和人情正是刘绍棠塑造人物的出发点,浸透了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心设计。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题材作品,不仅书写了运河的苦难历史、挖掘了运河两岸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还着意描绘了运河地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蒲篱苇舍、瓜棚柳巷、田园绿柳、鸟语花香的运河图景,在运河滩上光着葫芦头、露出屁股蛋、带着红肚兜野跑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他们“过家家,拜花堂”的游戏,令人生羡。奇特神秘的“放鹰”船,别有风味的“榆钱饭”,运河当午的裸纤夫,“花船”上的烟花女子,薄暮中的穷家浴女等都是运河两岸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刘绍棠在《〈蒲柳人家〉二三事》中曾这样说:“必须通晓与掌握他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人性世态与环境景色。”这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在作者笔下,尽管运河两岸的人们经历着民族的时代创伤,打下了痛苦磨难的烙印,但是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意志始终未能泯灭。小说中描绘的生活图景,充满勃勃生机,给人恬静和优美之感。如《蒲柳人家》的一段:
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象(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雾似的水气。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蝈蝈在豆丛下和南瓜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
牛羊家禽,鸟虫草木,残阳晚霞,田野村庄,树木河流,炊烟薄雾,蝈蝈、豆丛、南瓜花、柳梢月,这一系列事物的组合,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点染,其实颇见艺术匠心。这些景物,本来就充满乡土色彩,再加上农民、牧童等特定的写意人物,格外传神且寓于情韵,勾勒出乡村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情境。又如《草长莺飞时节》第十章中写齐柳生路过河堤时的一段描写:
堤上,黄鹂鸣翠柳;堤下,蒲苇和水草丛中,蛙声噪耳。满河鸭子,白毛凫绿水,红掌拨清波,引颈呱呱叫;这些年,运河沿岸村庄已经没有一只船,放鸭子的人乘坐绑在木梯上的笸箩,遠看就象(像)一只只大葫芦飘下了河,别有风趣。堤圈里的田野上,小麦已经扬花,早稻正在插秧,有的一家一户,有的三人一帮五人一伙,浇水的口唱小曲,插秧的笑语欢声,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
这是一幅立体的运河农忙图,层次鲜明,色彩多姿,从堤内到堤外,绿色的岸柳、蒲苇和水草,清波上浮动着白色的鸭子和红色的鸭掌,相映成趣,生机盎然,可谓十足的“赏心悦目”。
刘绍棠“乡土文学”的创作及内涵,不仅是我国乡土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时代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传大复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乡土文学”让我们更能不忘初心,更能记得住乡愁。如此,对于刘绍棠“乡土文学”所开创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也需要我们年青一代文学工作者的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③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第44、80页。
②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20页。
④李玉昆:《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河北学刊》1986年第2期。
⑤刘绍棠:《乡土与创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第230页。
⑥⑦刘绍棠:《〈蒲柳人家〉二三事》,《中国农民报》1983年9月18日。
⑧石兴泽:《刘绍棠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⑨刘绍棠:《创作漫谈剪辑》,《春风》1981年第1期。
(杨宜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