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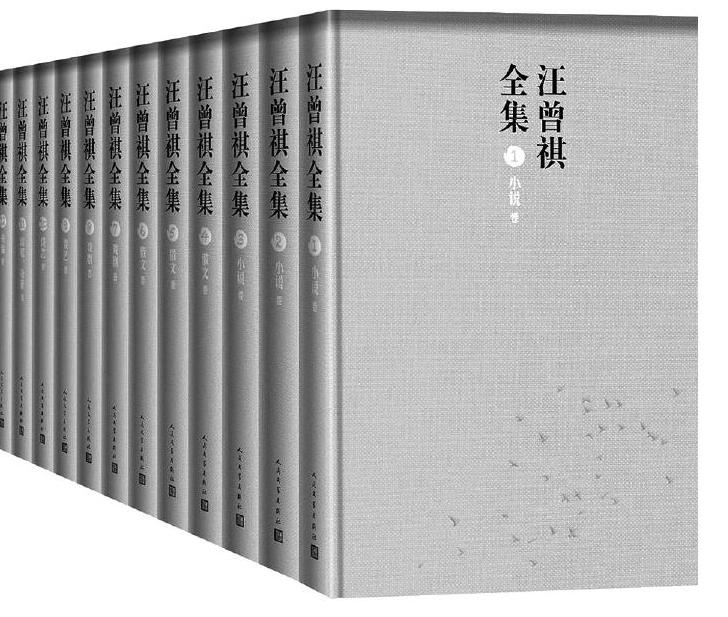
汪曾祺写过《〈职业〉自赏》①,其中提到:“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比较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不过,要探讨汪曾祺前后期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或许《异秉》比《职业》更合适。相对于篇幅短小精干的《职业》,《异秉》的体量更大,结构、语言、风格变化更显明,也更能体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创作探索历程。
汪曾祺曾经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恢复了自己在四十年代曾经追求的创作道路,就是说,我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创作,跟四十年代衔接起来。”②这种“衔接”最好的体现,便是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像《复仇》③《鸡鸭名家》④《职业》⑤,前后两版比较,都有大量的异文,但主体结构未变。《受戒》⑥前半段化自《庙与僧》⑦。而《异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鸡鸭名家》《受戒》一样,都是写作者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但前后版本写作风格变化之大,在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首屈一指。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将《异秉》这个题材写过三次,第一次的题目叫《灯下》,当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由于写作时间存在疑问,本文依据发表时间,称为“1948年版”),标题叫《异秉》;第三次是1980年,汪曾祺剛重拾小说之笔,笔下流出的第一篇小说,既不是一出即震惊文坛的《受戒》,也不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这篇旧作重写的《异秉》。⑧
受教于沈从文:“要贴到人物写”
汪曾祺的写作之路,是在沈从文的引领下开启的。
1937年,因为日军占领江南各地,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外国的只有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国的只有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沈从文开了三门选修课:“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各体文习作”。前一门课,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开过了,后面两门,则与沈从文知名作家身份有关。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担任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汪曾祺在1939年秋季入学,他又是奔着沈从文才考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所以,汪曾祺应该一年级即已开始受教于沈从文⑩。
比他高一年级的外文系学长许渊冲说汪曾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11,这也是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印象。但是,沈从文的每门课,汪曾祺都会选,都认真上,与他对其它课的态度大不相同。
也是借助汪曾祺后来的回忆,旁人才能了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方式:
沈先生是凤凰人,说话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小,简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二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创作实习》由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各体文习作》有时会出一点题目。我记得他给我的上一班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写的散文很不错,都由沈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了。他给我的下一班出过一个题目,这题目有点怪:“记一间屋子的空气”。我那一班他出过什么题目,我倒记不得了。
……沈先生教写作,用笔的时候比用口的时候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或谈这篇作品,或由此生发开去,谈有关的创作问题。这些读后感都写得很精彩,集中在一起,会是一本很漂亮的文论集。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都失散了。12
沈从文把《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这一类的题目习作叫“车零件”,说:“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写的东西就不耐读,不吸引人。这种方式汪曾祺很赞同,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鲁迅说的“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13。
沈从文还有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汪曾祺也记了一辈子,那就是“要贴到人物写”。汪曾祺自己行文有时用的是“贴着人物写”,其实是将湘西话翻译成了普通话。“贴到人物写”,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能听懂的人不多。汪曾祺回忆说“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班上,能理解、接受沈从文这一文学观念的,恐怕只是少数。
即使是汪曾祺,一开始也转不过来,“我们年轻时往往爱把对话写得很美,很深刻,有哲理,有诗意”。汪曾祺有一次写了这样一篇习作,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14“聪明脑壳打架”与“贴到人物来写”,显然是对立的,这个要怎么理解?我们可以来看看汪曾祺在1983年一次青年文学讲习班对沈从文这一创作观念的分疏:
以我的理解,一个是他对人物很重视。我觉得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或者是主导的,其他各个部分是次要的,是派生的。当然也有些小说不写人物,有些写动物,但那实际上还是写人物;有些着重写事件;还有的小说甚至也没人物也没事件,就是写一种气氛,那当然也可以,我过去也试验过。但是,我觉得,大量的小说还是以人物为主,其他部分如景物描写等等,都还是从人物中派生出来的。
……我认为沈先生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指作者和人物的关系问题。作者对人物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是和人物站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觉得应该和人物平等。当然,讽刺小说要除外,那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因为那种作品的人物是讽刺的对象,不能和他站在平等的地位。但对正面人物是要有感情的。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士兵、手工业者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很欣赏“温爱”这两个字。他没有用“热爱”而用“温爱”,表明与人物稍微有点距离。即使写坏人,写批判的人物,也要和他站在比较平等的地位,写坏人也要写得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儿“同情”。这样这个坏人才是一个活人,才是深刻的人物。作家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溶(融)为一体。我说大部分时间,不是全过程,有时要离开一些,但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贴”得很紧,人物的哀乐就是你的哀乐。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就是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这样紧紧地“贴”着人物,你才会写得真切,而且才可能在写作中出现“神来之笔”。
……第三,沈先生所谓“贴到人物写”,我的理解,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是游离出去了,环境描写与人物相脱节,相游离。如果贴着人物写景物,那么不直接写人物也是写人物。我曾经有一句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当然必须切合人物的身份,不能让农民讲大学生的话。对话最好平淡一些,简单一些,就是普通人说的日常话,不要企图在对话里赋予很多的诗意,很多哲理。托尔斯泰有句名言:“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另外谈谈语言的问题。我的老师沈从文告诉我,语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一句话要找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加以表达。当然也有华丽的语言,但我觉得一般地说,特别是现代小说,语言是越来越朴素,越来越简单。比如海明威的小说,都是写的很简单的事情,句子很短。15
当然,这些感悟,是汪曾祺在后来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慢慢体会出来的。在西南联大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汪曾祺还是会时不时写“聪明脑壳打架”的小说,而且他赞叹的沈从文“不可言说的温爱”,在40年代汪曾祺那里,还未必能成为稳定的情感。这一点,我们从《异秉》故事的三度重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语体文习作班佳卷”
沈从文教习作,有着别的教授无法企及的优势。一是他对中外的小说作品非常熟悉,可以帮助学生打开眼界:“看了学生的习作,找了一些中国和外国作家用类似的方法写成的作品,让学生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二是沈从文利用他在文坛的人脉,将比较满意的学生作品推荐出去发表,也能给予初学习作的学生以极大的鼓励。
汪曾祺无疑在班上同学里出类拔萃。目前所知沈从文最早向别人提到汪曾祺,是1941年2月3日,他写信给在福建厦门大学任教的施蛰存,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16。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汪曾祺在1940年春至1941年初,已经在昆明《中央日报》《今日评论》、重庆/桂林《大公报》等媒体发表小说《钓》《翠子》《悒郁》《寒夜》《复仇——给一个孩子上半年的故事》《春天》《猎猎——寄珠湖》,还有两三首新诗。作为一名中文系大一到大二的学生,这一成绩可以说颇了不起。这成绩当然含有沈从文为其揄扬的成分。
《灯下》则是沈从文对汪曾祺等人进行的“训练—发表”模式的典型之作。这篇小说是如此典型,以致让汪曾祺日后忘掉了此前发表的八九篇小说,他晚年回忆说:“我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这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是所谓‘散点透视吧。沈先生就找了几篇这样写法的作品叫我看,包括他自己的《腐烂》。这样引导学生看作品,可以对比参照,触类旁通,是会收到很大效益,很实惠的。”17
《灯下》篇末标明的时间是“三月十八日写成”,发表则是同年九月出版的《国文月刊》一卷十期“习作选录”,当期的“编后记”明确指出了作者身份、作品性质及沈从文在发表中所起作用:
本期《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是西南联大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
估计汪曾祺也没有保留这篇习作,它也没有收入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但汪曾祺还是牢牢记住了这篇习作,并且告诉采访者“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18。
《灯下》真的就是写“一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小说出现了如下的人物:
陈相公。他在服伺“新买来的礼和银行师子牌汽油灯”。
陶先生。在翻剪报集成的章回小说。
苏先生。用欣赏书画的神情看王二切肉。
王二。一边切肉,一边接钱。还忙着让儿子扣子补货。
扣子。在写账。
卢管事。在校核账目。
陆二先生。蒙馆放学后来,谈点“新闻”。
虾二爷。
张汉。
老炳。
卖鱼的疤眼。
其余的,都是“不上名姓的熟人”。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也都散漫无依。卢管事问陈相公“今天买了几个铜板酱油”,虾二爷问陆二先生“今儿在东家太太家吃了甚(什)么来了”,老炳问陆二先生“唐伯虎有几个太太”——这个题目引人入胜,“听过的,没听过的,都很诚心耐心的听着”,连正在读《应酬大全》的陈相公也放下了书,“呆呆的听着,又想着”。
接下来,张汉看了虾二爷点烟,遂“把自己丢在回忆里”,大谈“烟啊,一共有几种?有五种:水,旱,雅,鼻,潮”。旁人则问虾二爷“大太爷的田买成了没有”,于是我们知道,虾二爷大约是一位掮客之流人物,而且很傍着“大太爷”这样的阔人。卖鱼的疤眼临走时,他还追上去吩咐“明儿送十斤蟹到大太爷宫(小公馆)里去”。
总之,一切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式的,“散点透视”。它跟每天晚上灯下发生的谈话,并无不同,没有什么高潮。对于这种日常的、琐碎的、言不及义的谈话,作者只有一段总结:
谈话还是继续下去,不知是为何开头的,不知怎么又转换了话题,也不知到甚么时候才会停止,一切都极自然,谁也不肯想想。大家都尽可能的(地)说别人的事情,不要牵涉到自己。(自己的甘苦,顶好留到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说说去。)各种姿势,各种声调,每个人都不被忽略,都有法子教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这是通篇唯一点明主旨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想显示自身的存在,但又不愿意把自己的“甘苦”交出去,变成别人嘴里咀嚼的谈资。于是每个人贡献出的,都是“别人的事情”,陆二先生说说东家太太的厨艺人品,还有“蒙馆先生不应当说的话”,虾二爷谈谈阔人买房买地的“新闻,还有唐伯虎独占九美,烟有几种,打牌怎么赢了钱之类的闲篇”,然后就是往老炳背上貼纸乌龟,在张汉头上放草花翎,将陆二先生的衣角用串钱小绳系在桌腿上,种种熟人间的恶作剧。这是小城“无聊”的日常生活。而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就以这种无聊的方式维持与运转着。
汪曾祺说,沈从文为了让他写好《灯下》,找了几篇类似的作品给他看,其中包括沈从文自己创作的小说《腐烂》(1929年)19、《泥涂》(1932)20。《腐烂》描写上海闸北的稻草浜一块“总永远那么发臭腐烂”的地方,看相的,赌博的,卖淫的,酗酒的,收捐的,还有流浪的小孩子,形形色色,从日到夜,又迎来鸡叫天明。“天上有流星正在陨落,抛掷着长而光明的线,非常美丽悦目”。《泥涂》则写“长江中部一个市镇”上种种的生活片断,视线一直围绕着一个妇人从早至晚的一天奔走。
从题材上说,《腐烂》《泥涂》与《灯下》都有相似之处,但两位作者的姿态与视角都不大一样。汪曾祺描写药铺众人的灯下聚谈,更冷静客观,感情更内敛,不像沈从文,面对底层生活,面对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群,总有一种“悲悯”在笔下。
可以用来比较的还有一篇名作,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21。这篇小说也写抗战后方四川一个乡镇茶馆里的各色人物,有前清的监生,地方的闲汉,当过团练的袍哥,焦点是治保主任与小恶霸的冲突。这是一篇充满戏剧张力的讽刺小说,每个人都呈现出一种漫画化的嘴脸。它的批判锋芒,指向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四川实施的兵役制度。
而《灯下》呢,当然字里行间,也时时透出一点儿嘲讽的味道。但总的说来,它是平静的,无所针对的,似乎作者只是想画一张那一天(随便哪一天)小城灯下的人物速写,从上灯写到人散。药铺完成了它作为聚谈地点的使命,人们又过了平常的一天,不投入什么感情的一天。
汪曾祺正是从大学二年级起,迷上了西班牙作家阿左林,“写了一些很轻淡的小品文”。我們可以将《灯下》也归入这些“很轻淡的小品文”中去。阿左林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很大,他自己说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而阿左林的特点,跟废名一样,是小说带着散文诗的成分。汪曾祺特别欣赏阿左林的地方,在于他描写“安静”的擅长,描写“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阿左林笔下的西班牙是一个古旧的西班牙,真正的西班牙。”22
“京派”受阿左林影响的作家不少,如何其芳、李广田、师陀等。汪曾祺对阿左林的热爱与模仿,《灯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也有所谓“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暗含在众人的动作与言语中,各人的社会地位,彼此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在汪曾祺脑海里,其实清清楚楚,但是他只肯在《灯下》里写冰山一角,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以散文诗的形式书写安静,却又藏着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生活的暗流。这是汪曾祺从阿左林那里学来的创作方式。
摆熏烧摊子的王二在《灯下》出场不多,除了开头的手忙脚乱切肉收钱外,只有灯下众人将散时,才提了一句“王二本想来店堂里头坐坐,趁现在稍微闲一点的时候。他叫了一声‘扣子,可是回头一看,只好又说‘没有甚(什)么,你别打盹”。王二想让儿子替自己招呼剩下不多的主顾,自己也加入灯下的谈话会,然而人已经散了。
说真的,这回街上可真寂静得可以,阴沟里的沉积畅畅快快的吐着泡沫,象(像)鱼戏水。卖唱的背了松了弦子的二胡,踽踽走过。一天星斗。
王二在灯下的药铺重新出场,已经成了《异秉》的主角,而且在1948年、1980年出演了两回。
“等王二来,这才齐全”
现在收入2019年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的1948年版《异秉》,文末标明“十二月三日写成。上海”。小说发表则是《文学杂志》1948年第二卷第十期。而1980年版《异秉》的篇末,汪曾祺自注“一九四八年旧稿”,这无疑是将发表时间当成了写作时间。
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将1948年版《异秉》归入1947年创作,不知是否因为发表日期为1948年,按文末标示,倒推为1947年12月所作。然而这个时间也有疑问,因为1947年7月16日汪曾祺致信在北平的沈从文,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很久以前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来尚有一篇《异秉》,是否尚在手边?收集时想放进去,若一时不易检得,即算了,反正集子一时尚不会即动手编,而且少那么一篇,也不妨事。23
《最响的炮仗》写于1946年11月19日至20日,发表于1946年12月28日天津《益世报》。如果汪曾祺写完后立即寄沈从文,再由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时间线是对得上的。问题是,如《异秉》是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给沈从文,那么《异秉》的创作时间就绝不会是1947年,而应该是1946年的12月3日,此时汪曾祺也在上海。到了1947年7月汪曾祺再致信沈从文,说“很久以前”也说得过去。沈从文估计将《异秉》也推荐出去了,但不知何故迁延,到1948年才得以发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7年6月1日方在北平复刊,1948年11月又再次停刊,本身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文学杂志》1947年已经刊出汪曾祺《戴车匠》《牙疼》两篇小说,《异秉》放在1948年3月的二卷十期,完全可以理解。
汪曾祺在上海,但《益世报》是大报,《文学杂志》是京派重要刊物,不应该见不到。但不知为何,沈从文固然无法寄回两篇小说的原稿,而1949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居然也未收入《最响的炮仗》《异秉》两篇。究竟是何原因,很难说清。但《异秉》写于1946年末,殆无疑义。
高邮的一些老人,画过汪曾祺幼时东大街(现人民路)的店铺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出,汪曾祺去上小学,必须走半条东大街,他写过的许多店铺,如戴车匠、侯银匠、如意楼……都在这条街上,最近的,莫过于保全堂。踏出汪宅,来到东大街上,斜对过就是保全堂。要去大淖,也会经过保全堂。可以说,保全堂是汪曾祺在高邮最熟悉的所在,不光因为离家近,更因为,这是他家的产业。
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也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药的店员)、“相公”(学生意未满师的)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我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24
保全堂煮饭的老朱,每天要到大淖去挑水,汪曾祺也常常跟着,所以也熟悉大淖。老朱这个人物,在1948年版《异秉》里没有,到1980年版才出场。
《异秉》书写的时间十分精确,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候,“一天已经过去了”,那这段时间呢?“对于许多人,至少在这地的几个人说起来,这是好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把这也算在一天里头。更合适的是让这一段时候独立自足,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所以“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唯其这种时候,药店里的气氛是安适的。白天,管事、同事、学徒,都“属于这个店”,唯独这段时间,好像属于他们自己,可以“或捧了个茶杯,茶色的茶带烟火气;或托了个水烟袋,钱板子反过来才搓了的两根新媒子;坐着靠着,踱那么两步,搓一搓手,都透着一种安徐自在。一句话,把自己还给自己了”。就连唯一还有干活儿的学徒,吸鼻涕也吸出了“自得其乐的意趣,跟白天挨骂时吸得全然两样”。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和煦、闲适的气氛,“小店堂里洋溢感情,如风如水,如店中货物气味”。
我们的主角王二,可不像在《灯下》那样没有存在感了,店堂里群贤毕集,但大家“心里空了一块。真是虚应以待,等着,等王二来,这才齐全。王二一来,这个晚上,这个八点到十点就什么都不缺了”,作者又进一步强调“今天的等待更是清楚,热切”。
王二呢?王二还在做生意。汪曾祺笔头一调,开始了他已经娴熟的铺叙:熏烧摊子是什么样,王二的生意又好成什么样,这在《灯下》里一笔带过,在《异秉》里得用力写:
王二他有那么一套架子,板子;每天支上架子,搁上板子:板子上一排平放着的七八个玻璃盒子,一排直立着的玻璃盒子,也七八个;再有许多大大小小搪瓷盆子,钵子。玻璃盒子里是瓜子,花生米,葵花籽儿,盐豌豆……洋烛,火柴,茶叶,八卦丹,万金油,各牌香烟……盆子钵子里是卤肚,薰(熏)鱼,香肠,炸虾,牛腱,猪头肉,口条,咸鸭蛋,酱豆瓣儿,盐水百叶结,回汤豆腐干。……一交冬,一个朱红蜡笺底洒金字小长方镜框子挂出来了,“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美味羊羔五香兔腿”。先生,你说这该叫个甚(什)么名堂?这一带人呢,就省事了,只一句“王二的摊子”,谁都明白。话是一句,十数年如一日,意义可逐渐不同起来。
晚饭前后是王二生意最盛时候。冬天,喝酒的人多,王二就更忙了。王二忙得喜欢。随便抄一抄,一张纸包了(試数一数看,两包相差不作兴在五粒以上);抓起刀来(新刀,才用趁手),刷刷刷切了一堆(薄可透亮);当的一声拍碎了两根骨头:花椒盐,辣椒酱,来点儿葱花。好,葱花!王二的两只手简直像做着一种熟练的游戏,流转轻利,可又笔笔送到,不苟且,不油滑,像一个名角儿。五寸盘子七寸盘子,寿字碗,青花碗,没带东西的用荷叶一包,路远的扎一根麻线。王二的钱龙里一阵阵响,像下雹子。钱龙满了时,王二面前的东西也稀疏了:搪磁(瓷)盆子这才现出他的白,王二这才看见那两盏高罩子美孚灯,灯上加了一截纸套子。
忙完了这段,王二能够坐下了,他很想进店堂去,参与里面的聊天与哄笑,但他终究留在了凳子上,因为“不愿留下扣子一个人,零碎生意却还有几个的”,王二只是坐在外面,“入神,皱眉,张目结舌,笑”。
等到王二真正收了摊子,读者才知道,为什么今晚如此与众不同。原来,“今天实在是王二的摊子最后一天了。明天起世界上就没有王二的摊子”。明天,王二就要搬到隔壁的旱烟店去,有半间自己的店面了。
王二想搬吗?不想。十几年来,他习惯了在这么一丈来长,四尺宽的地方摆摊。而且,他喜欢一面做生意,一面听店堂里的人聊天说话,“晚上听里边说话已成了个习惯。要他离开这里简直是从画儿上剪下一朵花来”。只是,生意日益发达,他有了改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十几年中他娶了妻,生了儿女,“他不愿意他的扣子像他一样在这个檐下坐一辈子。扣子也不小了”。这才是关键。
对于店堂里的人来说,王二说不上多重要,他不打断别人说话,也不抢话说,是一名绝佳的听众。比起店里的先生和客人,还有教蒙馆的,他很懂得分寸。但是久而久之,王二成了这座药店,甚至整座小城的一个时间标志:“王二这一坐下,大家重新换了一回烟茶:王二一坐下,表示全城再没有甚(什)么活动了。灯火照在人家槅子纸上,河边园上乌青菜叶子已抹了薄霜。阻风的到了港,旅馆子茶房送完了洗脚汤。知道所有人都已得到舒休,这教自己的轻松就更完全。”
目睹着王二的发达,他们调侃地叫着“二老板”,但这种调侃明显是善意的。连学徒也在心里,用了一个《申报》上看来的新名词,叫王二“幸运儿”。王二的兴旺发达,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是吹了十几个冬天的西北风挣来的。“叫这么一声真是欢欢喜喜的。为王二欢喜,简直连嫉妒的意思都没有”。
王二此前求“先生们”给他的小店起个字号,自己再去刻个图章。这是一种标志,有了字号和图章,王二就不是游商小贩了,也是坐地开户的正经商户。这是一种经济上、社会地位上质的变化,这对王二很重要,对王二的儿子扣子更重要,“他一想到扣子把一方万胜边枣木戳子沾上印色,呵两口气,盖在一张粉连子纸上,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王二想催一催先生们,但又不好意思。没想到,陆先生主动提起了此事,并且想得很周到:“你不是想日后把店传给儿子吗,我们觉得还是从你们两个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就叫王义和好了。”王二听着这些话,只觉得“一辈子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当陆先生告诉他,图章也刻好了,在卢先生那里时,王二“啊——”一声,说不出话来。他感动极了。而正是这几句对话,引发了今晚保全堂里的交流狂欢:
王二如果还能哭,这时他一定哭。别人呢,这时也都应当唱起来。他们究竟是那么样的人,感情表达在他们的声音里,话说得快些,高些,活泼些。他们忘记了时间,用他们一生之中少有的狂兴往下谈。扣子已经把一盏马灯点好,靠在屏门上等了半天,又撑开罩子吹熄了。
在这种往事叙述的狂欢中,王二“简直伤心,伤心又快乐,总结起来心里满是感激。他手里一方木戳子不歇的掂来掂去”。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到,店面,字号,木戳,还有扣子的未来,都是混合一体的。而王二这样一位勤劳的小商贩,在这一晚感受到了极大的来自周边的温情。
小说最后才写到了王二的“异秉”。似乎方才的善待与剧谈,给了一向“知分寸”的王二以勇气,他回答“如何能有今天”的问题时,表示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庄重:
王二这回很勇敢,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
“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喏,上毛(茅)房时,不是大便小便一齐来。”
他是坐着说的,但听声音是笔直的站着。
大家肃然。随后是一片低低的感叹。
紧接着,女儿来了,王二该回家了。一家父子三人在已经断了行人的街上慢慢走远。
保全堂的店门也关上了。最后一句“学徒的上毛(茅)房”结束了这一版的《异秉》。
“对生活的一声苦笑”
1980年5月20日,汪曾祺重写了《异秉》。这是汪曾祺时隔三十多年后,第一篇重涉“高邮题材”的作品,比《受戒》早了近三个月,比《大淖记事》早了六个多月。
《异秉》是重写,而且它甚至催生了《受戒》。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说:“这以前,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如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25
选择重写《异秉》,作为自己“写写旧社会”的开端,反映了汪曾祺对这个题材的钟爱。而确实,随着自己阅历、处境的改变,汪曾祺一再回顾保全堂的热闹,却每每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况味。1980年的汪曾祺,感到自己终于“可以不说假话,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他总结道:“《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的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的鸢飞鱼跃似的快乐。”26
不过,《异秉》的待遇远比不上《受戒》《大淖记事》。林斤澜回忆《异秉》的发表过程,相当艰难:
《异秉》由我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編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声,要我找机会引见。过了三几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而是根本不是小说。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汪曾祺看了“编者按”说,懂行。27
叶至诚之子叶兆言回忆:“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28其实,即使《异秉》抢先发表,声名也未必及得上《受戒》《大淖记事》。这不单是时间先后、刊物影响力的问题,决定因素还包括彼时的社会心态,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方式,等等。
汪曾祺日后讨论自己的文学风格、文学手法时,常常提及《异秉》,又由于《异秉》是重写,也不时被用来比较汪曾祺自己“四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创作的异同。从创作题材与创作风格来说,比如对“小说散文化”的实践,对“氛围即人物”的追求,《异秉》这句判断是成立的,但毕竟隔了三十多年,确如他自己所说,“感情”首先就不一样了。
但是强调“异”有时也不免过头。有时甚至让人怀疑,汪曾祺自己还记不记得1948年版的《异秉》写了些什么——毕竟,他已经不记得40年代《异秉》的准确写作时间:
有一篇小说(《异秉》)我在一九四八年就写过一次,一九八〇年又重写了一次。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29
“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用来形容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不少小说,是恰当的,如《落魄》《老鲁》《庙与僧》《锁匠之死》《职业》,甚至用来形容《灯下》,也很准确——沈从文再三当面、写信跟汪曾祺说“千万不要冷嘲”,应当就是发现了这位得意弟子笔下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倾向。但是,1948年版的《异秉》不是冷嘲之作,恰恰相反,这是一篇带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的小说。前后两版《异秉》,内在情感有着相当强烈的共鸣。
不妨先来比较一下两版《异秉》的差异:
(一)1948年版有着严格的时间:王二结束摊子那天的八点到十点,而1980年版则是一种长时态的书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下午”“有一天”;
(二)1948年版的主人公是王二,核心情节是“王二撤摊开店”,而1980年版的主人公有王二,也有保全堂的陈相公、陶先生;
(三)1948年版凸出了王二的发达,1980年版除了写王二的发达,还作为映衬,写了这一条街的“景况都不大好”。
有研究者说1948年版是“焦点透视”,1980年版是“散点透视”30。其实《灯下》才是“散点透视”。1948年版《异秉》确实很“聚焦”,大家在等王二,王二收摊,王二进店,陆先生交代字号印章,大家回忆往事,谈到“异秉”,告别……王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仿佛是对他和儿子多年努力的回报。在《异秉》中,王二不再像《灯下》似的可有可无,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篇小说看成前后篇。在长年无聊的灯下聚谈中,王二始终是边缘的,不入流的角色,而终有一日,他发达了,变成了“二老板”,于是他被这个小团体接纳了,成为被夸赞、被谈论的人物,王二获得了地位的提升。
然而,1980年版的《异秉》固然不只写王二一个主人公,1948年版也并不是焦点总在王二身上的,重点在于最后一段,当王二庄重地说出了自己的“异秉”,并随女儿离去后:
“聋子放炮仗,我们也散了。”师爷和学究连(联)袂出去,这家店门也阖起来。
学徒的上毛(茅)房。
“学徒的上毛(茅)房”这六个字,才突然让我们注意到了“学徒的”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角色。在《灯下》一开篇,学徒“陈相公”在服伺(侍)“新买来的礼和银行师子牌汽油灯”,这盏灯点亮,才意味着充满热闹的夜晚开场;别人在谈天时,陈相公在看《应酬大全》,听到“唐伯虎有几个女人”才停下来听,想。在《灯下》里,陈相公与陶先生苏先生一样,都是药店里庸庸碌碌的一员。而在1948年版《异秉》里,这个学徒更边缘化了。他只是一开始,王二还没来的时候,“在‘真不二价底下拣一堆货”,我们知道他白天是常常挨骂的,但晚上他也能拣货时自得其乐。除此以外,他就只剩下了最后六个字:“学徒的上茅房。”
汪曾祺在1948年版《异秉》里,似乎跟读者玩了一个叙事游戏。比起那些热情道贺的,畅谈往事的,有份后天去聚兴楼吃开业酒的,所有的在场者来,“学徒的”是最不起眼的存在,连王二也不会在意的存在。偏偏是他,在王二说出“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最急于在自己身上验证、尝试。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却在某种程度上刺破了前面热闹的泡沫。汪曾祺当然对王二的辛劳,他的舐犊之情,饱含同情与悲悯,但也在看似不经意之间,点出了“学徒的”这位王二的崇拜者,他的无奈与凄楚——当然,也可能带一点儿“冷嘲”或“同情”。毕竟,1946年写作《异秉》时,在上海致远中学教学的汪曾祺,也是心情低落颓废,到了想自杀的地步31。
“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
1980年的汪曾祺,经历了《说说唱唱》《民间文学》,写过京剧《范进中举》,下放张家口四年,参加过《沙家浜》样板戏创作……他再来写《异秉》,可以说,题材一致,内在情感也一致。不同的是,保全堂的分量,大大地增加了。尤其是陶先生与陈相公,几乎可以与王二分庭抗礼。而写法,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不能说是“散点透视”,而是更加贯彻“氛围即人物”的主张,将氛围写厚,写透,不然人物也立不住。
保全堂这个小圈子里,边缘人物有二,陶先生和陈相公。这从过年推牌九可以看出来:“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王二。”
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王二,因为他是一位上升的边缘人物,生意越来越好,用上了钱庄、绸缎庄才用的汽灯,也不怕别人议论,常常去“听书”。推牌九的时候,“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相反,“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赢得多了,王二也能上去推两庄。显然,王二的地位有了超越性的上升。同样是边缘人物,王二的遭际,当然会给“失败者”陶先生、陈相公一种虚幻的期望。
在1980年版《异秉》里,形象变化最大的,无疑是陈相公。这个在《灯下》与1948年版《异秉》中只有寥寥几笔的小人物,在1980年被汪曾祺细细地描写着: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他每天绝早起来给“先生”们倒尿壶。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晒药,收药。碾药。裁纸。刷印包装纸。搓纸枚子。擦燈罩。摊膏药。放尿壶。上门。临睡前还要背两篇《汤头歌诀》。他有一个多年守寡的母亲。
这一段描写,汪曾祺自己颇得意。他晚年主张小说要“短”,“短是对读者的尊重”,举的例子就是这一段:“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噜(啰)嗦!——而且,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做文章(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32
陈相公老是挨打(他在1948年版里还只是挨骂),因为“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而卢先生们打陈相公,也是“为他好,要他成人”。这就是结构性的压迫,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只有一次被打得太狠,煮饭的老朱夺下了门闩,说了一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是一种“反常识的常识”。当别人将陈相公定位为“没有不挨打的学徒的”时,没有人记得他还是一个孩子。陈相公挨了打,当时还不敢哭。只能晚上,上了门,一个人呜呜地哭上半天。
他向他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
像这样的情节,1948年版里没有。在读1948年版时,我们很难揣知作者对于“学徒的”怀有什么样的态度,同情?还是讽刺?到了1980年,情感变得很鲜明,汪曾祺把巨大的同情寄托在陈相公身上,想写的是“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33。
由于有了这种“氛围”的不同书写,结局那几乎一样的情节,也就能读出不同的况味。“学徒的上毛(茅)房”,是要说什么呢?小说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而1980版则写得很舒缓:
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
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喊了几声,没人应声。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汪曾祺有一次介绍说:“一位评论家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他看到这里,过了半天,才大笑出来。如果我说破了他们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也做到‘大小解分清,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如果再发一通议论,说:‘他们竟然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庸俗而又可悲悯的小市民呀!那就更完了。”34汪曾祺对外解读自己的作品,有时会有点“滑头”,套用一些流行的概念,但说的是自己的意思。就像那句名言“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然而什么是“深刻”,什么是“和谐”,恐怕跟一般人理解的,都不一样。
《异秉》针对的是“庸俗而又可悲悯的小市民”吗?也是,也不是。汪曾祺是用“可笑”“悲悯”来总结过《异秉》里的人物:
我写的《受戒》、《大淖记事》,抒情的成分多一些,因为我很喜爱所写的人,《异秉》里的人物很可笑,也很可悲悯,所以文体上也就亦庄亦谐。35
陈相公绝没有明海与小英子可爱,也不像巧云十一子那么招人疼,可是,庸俗的小市民的生活里,就没有美与温情吗?他们就只配得到嘲笑,而不能获得关注与同情吗?我想,汪曾祺在几十年的跌宕起伏中,以他的敏感与多情,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这一层面,理解远比很多追求“深刻”的作家深刻得多。如果说《受戒》是汪曾祺发现了旧社会的美,《大淖记事》写出了底层民众的美与善,《异秉》则是发现了庸俗的小市民身上不只可怜,兼且充满欢乐的某种情味。陶先生与陈相公作鼓振金地上厕所,反而是对他们生活中苦难的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消解,这是一种“真实的、日常的诗意”,就像陈相公每天登高望远:
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外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桔(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
很多时候,汪曾祺笔下所写,不过是艰难时世中片刻的“心旷神怡”。“随遇而安”也好,“生活,是很好玩的”也罢,没有大的沉重的压迫的氛围,这些词句就成了骗人的鸡汤,因为它构不成一整套的人生哲学与审美态度,无法让人持之以恒地在阴沟里仰望星空,在泥沼里闻见花香。所以汪曾祺一直告诫自己与世人,生活可以混乱,但欢乐才能滋润出信心: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自己对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能使别人提高信心呢?我不从生活中感到欢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欢乐。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写混乱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乱。36■
【注释】
①汪曾祺生前未发表,亦未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
②张兴劲:《访汪曾祺实录》,《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③初刊于重庆《大公报》1941年3月2日、3日。修改后刊于1946年《文艺复兴》第1卷第4期。收入《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复出后修改本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
④初刊于《文艺春秋》1948年第6卷第3期。收入《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复出后修改本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
⑤第一版刊于天津《益世报》1947年6月28日。后一版刊于《文汇月刊》1983年第5期。篇末自注:“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原稿已失去。前年和去年都改写过,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
⑥《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
⑦上海《大公报》1946年10月14日。
⑧分别引自《汪曾祺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1-36、265-273页;第2卷,第80-89页。
⑨《我的老师沈从文》,写于1981年,《收获》2009年第3期。
⑩1939年度一、二年级的“大一国文”由朱自清、沈从文共同担任。见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1页。
11许渊冲:《沈从文和汪曾祺》,见《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第61页。
1217《我的创作生涯》,《写作》1990年第7期,见《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72、73页。
13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73页。
14《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
15《小说创作随谈》,《芙蓉》1983年第4期。
16沈从文致施蛰存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18李辉:《听沈从文上课》,见《与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第157页。
191934年4月收入《游目集》。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196-212页。
20发表于1932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时报》。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107-139页。
211940年12月1日发表于《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22《谈风格》,《文学月报》1984年第6期。
23《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3页。
24《我的祖父祖母》,《作家》1992年第4期。
25《关于〈受戒〉》,《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45-146页。
26《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486页。
27《〈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见《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8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江》,《作家》2003年第2期。收入《桃花飞尽东风起》(万卷出版公司,2016)时篇名改《郴江幸自绕郴山》。初刊疑误。
29《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人民文学》1982年第5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89页。
30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对读》,见钱理群主讲《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34页。
31“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业,曾想过要自杀,他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说我没出息。信中又提到‘千万不要冷嘲。”《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读书》1984年第8期。
32《说短——与友人书》,《光明日报》1982年7月1日,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93页。
33《〈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97页。
34《小說技巧常谈》,《钟山》1983年第4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260页。
35《揉面——谈语言运用》,《花溪》1982年第3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66页。
36《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人民文学》1982年第5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89页。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