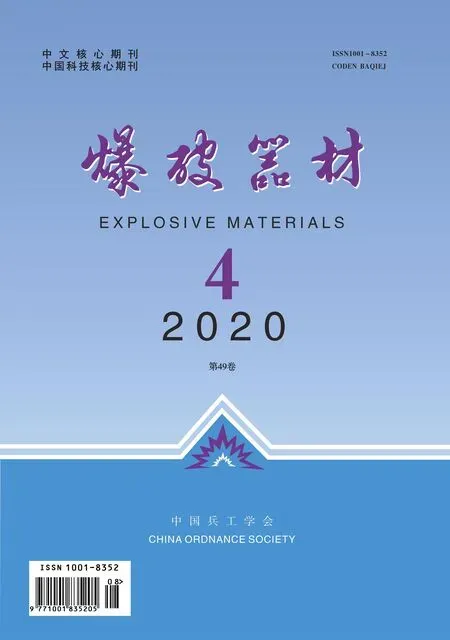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的抗爆性能❋
沈文妮 黄正祥 祖旭东 肖强强 贾 鑫 尚 伟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引言
黏土砖砌体墙有较好的承重、保温、隔热、隔声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民用建筑的承重和围护。 但是,它是典型的脆性材料,不能大量吸能以减缓冲击波的破坏。 在巨大的爆炸载荷下,黏土砖砌体墙会形成大量具有杀伤力的碎片,对室内人员和财产形成较大的威胁。 因此,开展针对砖砌体墙的抗爆研究尤为重要。
Aghdamy 等[1]以试验和仿真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无钢筋的混凝土砌体墙喷涂纳米颗粒增强聚合物和泡沫铝加固后,在动力和冲击状态下的破坏和倒塌的特征;Davidson 等[2-3]通过爆轰试验的方法分析了喷涂聚脲弹性体加固砌体墙的抗爆机理;Gattesco 等[4]对配筋砌体墙非平面行为的试验与数值计算进行了研究;范俊余等[5]模拟了砖填充墙在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响应及损伤破坏,并指出砖墙在不同比例距离情况下存在多种破坏模式;郑洪[6]研究了无孔砌体墙在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响应;蒲兴富[7]进行了传统砌体墙的爆炸效应的数值模拟;韩永利等[8]对四边约束墙体的破坏模式、抗爆能力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与单向墙体进行了比较;李效光等[9]以数值模拟结合结构静力试验的方式,对弧形砌体墙结构进行了基本力学性能研究;陈力等[10]讨论了燃气爆炸泄爆载荷作用下不同加固方式对单向和双向砌体填充墙体动力响应和破坏模式的影响。但是,对于接触爆炸下,单向支撑的黏土砖砌体墙的破坏模式和抗爆机理研究较少。
采用LS-DYNA 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以传统单面黏土砖砌体墙为例,建立了黏土砖砌体墙三维分离式细观模型,分析了不同强度接触爆炸载荷下墙体的毁伤和破坏特征。 并选用两种不同质量的TNT炸药对普通黏土砖墙体在单方向支撑条件下进行了对应的接触爆炸试验验证,将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其工作机理及响应特性,以期对黏土砖砌体墙的防爆抗爆、加固等研究起到指导作用。
1 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的数值模拟
1.1 黏土砖砌体墙的有限元模型
黏土砖砌体墙由砖块和砂浆依靠黏结作用连接而成。 砖块和砂浆的抗压强度与抗拉强度差距较大,两者之间的黏结力较小;因此,在动载荷下,砖块和砂浆的结合面是砖砌体墙的薄弱环节。
相比不区分砖块和砂浆的等效均匀化模型[10-12]和仅有单位宽度砌体棱柱的精简化模型[13],分离式模型与黏土砖砌体墙高度吻合。 采用分离式模型来描述砌体墙,砖块和砂浆分别采用不同的材料单元,求解时将两者视为不同的部分。 仿真按照相关标准[14]中的砌体墙的砌筑规制,研究厚度为365 mm(37 墙)的墙体。 建模时,砌筑方法为一顺一丁。 黏土砖砌体单墙尺寸为1 990 mm ×1 260 mm×365 mm。 由于该单墙呈轴对称,因此采用砌体墙的1/2 模型进行计算,尺寸为995 mm ×1 260 mm×365 mm。 另外,为了避免在后处理镜像操作时出现两条1.0 cm 灰缝相邻,将对称面处的灰缝削为0.5 cm,使镜像后对称面处的灰缝整体保持1.0 cm 不变。 砖砌体墙1/2 模型如图1 所示。
由于在实际建筑中,一般下挖地基,墙体自地下约0.5 m 处砌起,砌筑固连在地面上;因此,数值模拟建模时,墙体底部贴近地面的部分可视为全约束,两侧有拉筋或者立柱与旁侧的墙体相连。 这种构筑方式能够有效地限制墙体的位移和变形。 施工中,为使墙体平整美观,外侧常用一层较薄的低强度砂浆(M5 及以下)刮平。 为与实际情况相对应,对1/2模型背爆面施加纵向长条形全约束,以模拟附近墙面对砌体墙的支撑作用,使得墙体两侧约束强于上、下两侧的约束;在对称面上施加X轴方向的约束,在空气域四周(对称面除外)施加非反射边界。 由于墙体外侧粉饰砂浆强度较低、厚度较薄,忽略其在接触爆炸中的抗爆作用。
由于爆炸的发生时间非常短暂,假定黏土砖砖块和砂浆连接完好,即两者之间采用共节点方式建模。 为了模拟砖块和砂浆之间的黏结、分离和滑移,模拟接触面之间的拉伸失效和剪切失效[13],采用面-面固连失效方式(TNTS)来表示上述关系。
黏土砖砌体墙的砖块和砂浆之间的抗拉和抗剪强度比较小,滑动面上允许正应力和允许剪应力分别取为0.12 MPa 和0.14 MPa[6]。 接触面失效后,砖块和砂浆之间将产生错动、滑移,此时摩擦力阻碍两者滑动,在接触面干燥情况下,摩擦系数μ取为0.7。
1.2 黏土砖砌体墙的材料模型
1.2.1 炸药与空气的材料模型及参数
三维结构计算模型构建了TNT 炸药与空气的Euler 网格以及墙体结构的Lagrange 网格,并利用Euler/Lagrange 全接触算法模拟冲击波与结构的作用。 在数值模拟计算中,空气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模型,炸药使用∗Mat_High_Explosive_Burn 模型、JWL状态方程来表示,JWL 方程为:
式中:p为炸药爆轰产物的压力;E为炸药单位质量的内能;V为相对体积;A、B、R1、R2、ω为炸药的材料参数。
TNT 炸药的材料参数(β、K、G、σr均为零)及状态方程参数见表1 和表2,采用g-cm-μs 单位制。

表1 炸药的材料参数Tab.1 Material parameters of explosive

表2 炸药的状态方程参数Tab.2 State equation parameters of explosive
1.2.2 墙体的材料模型及参数
砖块和砂浆均使用∗Mat_Brittle_Damage 模型,该材料模型由Govindjee 等提出,是一种各向同性、脆性、损伤模型,并被广泛应用于脆性材料计算中[15]。 表3 列出了用作墙体模型的黏土砖砖块和砂浆的基本材料参数[10]。 墙体材料在爆炸中会发生大变形,而大变形会导致网格的扭曲和畸变。 为防止发生负体积错误,采用∗Mat_Add_Erosion 选项来模拟砖块和砂浆的破坏,以主应变准则作为砖块和砂浆的破坏准则,当单元中的主应变达到破坏准则时,将单元从计算中删除[16]。
1.3 黏土砖砌体墙的数值仿真结果
如图2 所示,在墙体上离炸药由远至近,取4 个不同的位置A、B、C、D。 图3 为TNT 药量为2 kg 时4 个测点空气单元的压力时程曲线。 4 个点的爆炸压力在t=800 μs 时即趋向于零,因此,数值仿真计算到t=1 000 μs 时为止。

表3 砖块与砂浆的材料参数Tab.3 Material parameters of block and mortar
当TNT 药量为1 kg,不同时刻墙体的破坏情况如图4 所示。 图的左侧、中间、右侧分别反映了砌体墙的纵断面(即对称面)、墙体迎爆面、墙体背爆面的破坏情况。 由左侧、中间两部分可知,爆炸引发的冲击波首先在砌体墙迎爆面造成中央爆坑和纵向裂纹,在约400 μs 时逐渐开始在爆坑四周沿灰缝形成发散状裂纹,纵向裂纹扩展变粗;由右侧部分可知,背爆面墙体首先形成了纵向裂纹,自400 μs 起,墙体中央灰缝部分开始裂开,由图4(c) ~图4(e)可知,背爆面裂纹整体呈发散状(肋板部分除外)。
图5为不同药量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在t =1 000 μs时的破坏情况。由图左侧的纵断面可知,随着药量逐步加大,爆坑深度逐渐增加,并逐步出现放射性裂纹,墙体中心竖直方向即对称轴方向裂纹尤其深。可以定性地看出,在不同药量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爆坑的纵断面积S随着药量的增加呈逐步上升趋势,对应爆坑的体积同样呈逐步上升趋势。 由中间部分的迎爆面破坏情况可知,随着药量增加,应变逐步增大;接触爆炸所影响的区域面积也逐步增加,由图5(a)的球形到图5(b)的花瓣状,再到图5(c)、图5(d)的方形;爆坑四周的变形顺着灰缝发散,呈图5(e) ~图5(h)的放射状;墙体四周边缘处逐渐出现零星的崩落。 由右侧部分的背爆面破坏情况可知,随着药量增加,背爆面形变范围逐步增加,且灰缝处为薄弱环节,崩落和层裂同样顺着灰缝发展,但总体呈环形趋势(肋板部分除外),中央灰缝受创严重,形成贯穿裂纹。
图6为不同药量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形成爆坑的尺寸。
由图6(a)可知,当药量从0.25 kg 增加到1.00 kg 时,爆坑体积基本呈线性增长;当药量从1.00 kg上升到2.00 kg 时,体积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曲线斜率显著降低,增长缓慢并逐渐趋于水平。 由图6(b)、图6(c)可知,当药量从0.25 kg 增加到1.00 kg 时,爆坑深度h和直径d基本呈线性增长;当药量从1.00 kg 上升到2.00 kg 时,爆坑深度h和直径d的增长同样较为缓慢,接近水平。
2 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的试验验证
2.1 试验方案
试验墙体依据相关标准设计,墙体尺寸为2 000 mm×1 200 mm ×370 mm,墙体两侧对称布置一对肋板(扶壁),用于模拟实际建筑中周围墙体的支撑作用[14]。 为保证墙面平整美观,墙体表面用约2 mm 砂浆抹平。 所用炸药为TNT 圆柱形压制炸药,装药密度为1.63 g/cm3,采用两种装药规格,分别为0.50 kg(试验1#)和1.00 kg(试验2#),基本尺寸分别为∅100 mm ×39 mm 和∅100 mm ×78 mm。 试验1#与试验2#分别对应数值仿真(图4)中的b、d 工况。 试验现场布局如图7 所示,药柱由导爆管雷管起爆,雷管通过塑料导爆管与起爆器相连。
2.2 试验结果
接触爆炸后的试验结果如图8 所示。 在图8(a)中,砌体墙迎爆面中心出现爆坑;崩落破坏大多出现在砂浆位置,产生少量砌块碎块、碎屑向外飞散,碎块掉落在爆坑下方,碎屑布满试验墙前方区域。 墙体迎爆面爆坑的水平方向左、右两侧和上侧均出现大裂纹,裂纹贯穿至砌体墙背爆面;迎爆面爆坑四周还伴有蛛网状放射性细小层裂。在试验2#中,图8(b) ~图8(d)黏土砖砌体墙迎爆面中心出现较大爆坑;崩落破坏也同样大多出现在砂浆位置,产生大量砌块碎块、碎屑飞散。 墙体迎爆面爆坑水平方向和上侧在出现较大贯穿裂纹的同时,砌体墙左上部分沿着大裂纹向后倒塌,右上部分沿着大裂纹错开并发生小角度偏转,角度约为2.3°。
3 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3.1 现象比较分析
在数值模拟中,当药量小于1 kg 时,墙体变形主要以爆坑和纵向裂纹的形式出现;当药量大于1 kg 时,墙体迎爆面渐渐布满裂纹,背爆面同样出现沿灰缝的环状裂纹。 在试验中,试验1#药量较小,仅仅形成了爆坑和少数裂纹,而试验2#加大了药量,在形成较大爆坑、较粗裂纹的同时,裂纹完全贯穿墙体导致墙体脆性断裂,并在冲击波的作用下发生了错位、偏转和倒塌。
分析可知,当接触爆炸发生时,冲击波立即到达黏土砖砌体墙表面,压缩应力波在墙体迎爆面形成严重的毁伤,中央爆坑及其四周沿着灰缝发展,形成粗细不一的裂纹;冲击波传播至背爆面,形成较强的拉伸波,引起背爆面的崩落和层裂,背面的强拉伸波造成的崩落和层裂同样顺着灰缝发展,但总体呈环形的趋势,且在中央灰缝处形成贯穿裂纹。
由图6 可知,仿真中爆坑尺寸的增长在药量大于1 kg 后就逐渐停止;再联系试验2#中砌体墙的错位和倒塌可知,当药量较大时,冲击波的能量依靠掀动墙体释放。 即当药量小于1 kg 时,炸药对砌体墙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中央爆坑以及水平、竖直方向的十字形裂纹的形成上;当药量超过1 kg 时,炸药对砌体墙的破坏逐渐向四周(尤其是四周的灰缝)扩散,直至部分灰缝贯穿,导致墙体错位、偏转、倒塌。
从现象来看,数值模拟较好地展现了砌体墙在接触爆炸载荷下,形成爆坑、粗大裂纹沿着水平和竖直方向的灰缝逐渐伸展、直至贯穿的过程,前期破坏状态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说明墙体模型以及砌体材料模型基本能反映爆炸载荷下砌体墙动力反应的实际情况。
3.2 参数比较分析
墙体爆炸试验与仿真的参数对比如图9 所示。
数值模拟与试验尚有不同之处。
由图9(a)可知,爆坑直径d的误差较小(最大误差为9.6%)。 仿真计算中出现的误差主要原因为:数值模拟仅体现了爆坑的形成、裂纹的扩展,但缺少后续砖块的飞溅、倒塌现象。
仿真中爆坑深度h与试验有出入。
由于计算时长、文件大小等原因,数值模拟计算到t =1 000 μs,体现了爆坑的形成、裂纹的扩展,但后续砖块的飞溅、倒塌现象尚未出现;并由于缺少砖块的飞溅、倒塌,爆坑的最终深度难以确定,影响算例中爆坑深度的统计,使得深度h与试验有出入。
墙体边界的损伤模拟程度较试验严重。
在试验中,墙体与肋板之间连接不牢固,爆炸后甚至出现了缝隙,使得墙体在试验中产生摇晃,减轻了试验中墙体边界的损伤。 仿真中,砖块与砂浆采用共节点的方式连接;而在试验中,砖块与砂浆的黏合不完全牢固,存在一定的缝隙,这使得缝隙处更容易被摧毁,飞溅、倒塌现象更为猛烈。
4 结论
建立了空气、炸药、黏土砖砌体墙的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对黏土砖砌体墙在单方向支撑下的爆炸破坏进行了数值模拟,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分析了不同装药质量接触爆炸下黏土砖砌体墙的破坏特征和损伤机理,得到以下结论:
1)当TNT 药量小于1 kg 时,接触爆炸对墙体的破坏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央爆坑以及水平、竖直方向的十字形裂纹上的形成上;当药量大于1 kg 时,炸药对砌体墙的破坏逐渐向四周(尤其是四周的灰缝)扩散,同时,背爆面的层裂和崩落也显著增加,最终将会倒塌。
2)在接触爆炸下,爆坑尺寸的增长在药量大于1 kg 之后就逐渐停止,当药量大于1 kg 时,冲击波的能量依靠掀动墙体来释放。
3)数值模拟较好地展现了砌体墙在接触爆炸载荷下,形成爆坑、粗大裂纹沿着水平和竖直方向的灰缝逐渐伸展、直至贯穿的过程。 前期破坏状态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但对后续砌块的飞溅、倒塌过程模拟不足,产生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