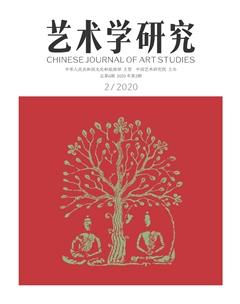论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宗白华经验”
陈旭光
[摘要]宗白华的艺术学研究成果是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一个富矿,他具有艺术学研究的文化使命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他的艺术思想、艺术学理论思考,以及研究中国艺术学、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包括艺道观与艺境论、主体论、作品本体维度、艺术接受)的成果和经验,需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着手予以分析和考察,并从几个维度进行梳埋和总结。
[关键词]艺术学研究;宗白华;经验;艺境
一、引言
宗白华先生是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一个富矿、一座高峰(美学界一直把他与朱光潜先生并称“美学双峰”),更像一个迷人的“谜”。
宗白华先生给我们的一个主体形象就是他所描述的“拈花微笑”的美学老人形象,如行云流水,从容不迫,面对美学宝藏和艺术画廊,他如数家珍、从容道来,与我们一起散步、品评、赏鉴。他的文章优美耐读,常读常新,或许语句上半文不白,个别地方也可能令人似懂非懂,稍有费解,但绝没有对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也绝不会影响你的阅读快感,更不影响他的文章深度。他的理论语言很多时候是一种独特的、诗性的、感悟性的文字。李泽厚评价宗白华的文字:“或详或略,或短或长,都总是那种富有哲理情思的直观式的把握,并不作严格的逻辑分析或详尽的系统论证,而是单刀直入,扼要点出,诉诸人们的领悟,从而叫人去思考、去体会。”汪裕雄、桑农也谈过自己的阅读感受:“初上手,如诗如画,能见作者性情,好读之至;待加思索,便觉如面临帝释珠网,层层互映,意蕴难穷。如欲稍加董理,便不免有治丝愈纷之叹。这好比读《庄子》,读时易得心越神游的愉快,但若想在学理上寻出庄学端绪,或者向别人介绍读庄的心得,便不免常常陷入困惑甚至苦恼之中。宗白华擅长于体悟,而体悟,正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确,读宗白华,会有味之无极,百读不厌,不断领悟,常读常新之感。
宗白华没有大部头的体系性的皇皇巨著,最精华的是论文集里的二三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还有几部有宏富的提纲但因种种原因未完成的讲稿或专著,但有自己的中国哲学研究体系的冯友兰先生却说“在中国真正构成美学体系的是宗白华”。如此之高的评价该如何理解?
从宗白华的文章看,笔者感觉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这些文章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古诗、新诗、书法、篆刻、国画、油画、戏曲、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摄影等。
二是这些文章几乎涉及了所有艺术创作的环节,如创作主体的涵养、人格和体验、观照,创作过程,艺术作品,审美鉴赏和艺术接受主体等,我们可以在宗白华先生仿佛零散的篇什中找出内在的体系性。
三是这些文章涉及大量艺术学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编撰“艺术学原理”“艺术学概论”等艺术学教材专著必然要涉及的问题或面向,如艺术的本质、功能、形态、形式、风格、结构、审美心理、艺术主体、艺术接受等。
四是宗白华在涉及众多的一般艺术学原理和众多艺术门类的具体问题上,其研究实际上都事关20世纪以来重要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化特质、艺术教育和美育等聚焦性的重大问题,而且研究在微观与宏观、经验与超验、感性与理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具体等方面,均有着很好的结合。
无疑,作为20世纪中西文化、中西美学碰撞的“宁馨儿”,中国现代艺术学学术史的“活化石”,宗白华的艺术学成就不容置疑,甚至仰之弥高。但更为值得思考的是宗白华取得这些非凡成就的“经验”,也即一种“宗白华经验”为何?也就是说,探究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富赡的研究成果?宗白华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学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在总结宗白华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接着讲”?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讨,我以为意义可能超越了其学术成就本身。
二、宗白华艺术学研究的
使命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宗白华具有自觉的学术研究方法论意识。概而言之,他最重要的方法特色是:其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强大的理论创新驱动力。宗白华认为:“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去德国留学时,宗白华更是发下建设新文化的学术宏愿:“我预备在欧几年把科学中理、化、生、心四科,哲学中的诸代表思想,艺术中的诸大家作品和理论,细细研究一番,回国后再拿一二十年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和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无疑,正是这种理论学术自觉和舍我其谁的宏大抱负,驱使着宗白华孜孜以求地进行具有不竭生命力的學术思考和探求。
其二,高瞻远瞩、由西返中的视野,中西互证、古典与现代贯通的比较思维。宗白华晚年曾总结自己的学术心得说:“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这就是要求我们在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时不要忘记同西方进行比较。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
他还特别注重西方哲学高度的思维和视野。“我一直对中国的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书法、戏曲等都有兴趣,自己也收藏了一些绘画和雕刻。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
的确,从宗白华的文章及学术兴趣看,不难发现,他年轻时多直接论述,评价康德、叔本华、歌德等人,而很少谈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他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的文章多写于归国之后,因为彼时他才可以“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
宗白华也没有信奉“全盘西化”而自我鄙薄,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他到德国留学后感受到了当时德国学界的中国热潮,“老子的思想直接道着欧洲近代社会的弊病,所以极受德国战后青年的崇拜;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了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zarnthustra),现在德国青年却带老子的《道德经》了”。因而强调“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但是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
他还明确主张融通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一方面,古典美学给他以厚实的根基与充沛的学术营养,他对康德、歌德等的哲学思想研习甚勤;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现代美学、现代文艺的情有独钟,则拓展了他与时俱进的学术视野。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叔本华研究的《萧彭浩哲学大意》。他身体力行地主张“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前者强调的是世界观、直觉、美学观,后者看重的是人格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他对非理性主义的重要哲学家柏格森也颇为推崇,认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对作为现代主义源头的康德,他则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更值得关注的是,宗白华还是未来主义画论的翻译者,而这与其说是宗白华新锐前沿,不如说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现代派美学的某种相通性使然。
就以经过他(当然不限于他)的阐发而成为中国艺术理论重要范畴的“意境”来说,其方法论和思维特点显然与西方分不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叔本华对现象世界的本体论思考,柏格森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时间意识,以及康德深邃博大的哲学时空观”,构成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
无疑,正因宗白华具有高瞻远瞩的视野,一种文史互证、中西互证、古典与现代贯通、各个艺术类别互证的比较艺术学的学术方法或思想,借西方美学、艺术学之光,烛照出了中国艺术的深层奥秘。同时,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既不会夜郎自大,也不会自惭形秽。
其三,艺术整体性:贯通理论与实践、特殊与一般,打通门类艺术。这可能与宗白华的德国老师——艺术学科奠基人之一的玛克斯‘德索的艺术比较观和艺术通观思想有关。在《美学向导》的寄语中,宗白华殷殷告诫后学:“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的规律来。”综观宗白华的艺术研究,这种打通比较、互文互见几乎是随手拈来的。与兴趣广泛、精通或广涉多门艺术的艺术教养有关,宗白华还具有一种艺术思考的整体观思想,也即汪裕雄谈到的“艺术通观”。汪裕雄认为宗白华“由中国绘画特有观照法、透视法,他发现了中国艺术共有的空间观——以时统空、充满节奏的空间观,由此辐射开去,统摄各个艺术门类,作出艺术通观”。这种艺术通观我觉得也可以称作一种“艺术整体观”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美术史学者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戏剧学者丁罗男的“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笔者的“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整体观”都有所体现,虽然上述整体观侧重于把整个20世纪作为整体的思想,但也与把整个大艺术门类里的各个艺术类别视作一个整体的整体观是相通的。
其四,恪守“以人为本”原则,旨归在于人格建设、生命美学,具有独特的艺术功能观。在艺术的功用观或功能观上,宗白华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但一直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如“人格建设”(“盖少年中国乃具健全人格之男女国民所共同组合而成者也”)。不像部分其他成员那样最终走上一条“武装救国”或“实业救国”的道路,宗白华实践了一条“学术救国”“人格救国”“美育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赞同学会主要发起人王光祈等所制定的學会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虽说也有“发展社会事业”的内容,但实际上是把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放在最后的。他更希望学会“建立各种学校,从事教育,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以后再发展各种社会事业”。
在艺术的功能问题上,他实际上并不注重艺术的直接社会功用,旨归在人格熏陶的方式和人格建设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是纡徐曲折的、间接的。故在宗白华的艺术研究中对特别强调社会功能的现实主义艺术似乎关注不多。他主张“少年中国精神”的建设,因为他认识到,在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者中,最重要者,“还是从教育方面去健进国民道德智识的程度,振作独立自治的能力,以贯彻民主政体的精神”。
另外,与“少年中国学会”中一批社会革命、武装革命的青年的追求不一样;与徐悲鸿专注于现实主义绘画,不屑甚至怒斥现代主义美术不一样,他对西方形式主义、超现实主义画论的译介很能说明他的现代主义趣尚。宗白华还以对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源头的康德美学和西方现代派画论的译介而表白了自己的艺术趣味并非仅为古典美学。就像康德美学代表了古典美学的“终结”和现代美学的开启相似,宗白华也以自己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跨越了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或艺术学。毋庸讳言,他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清醒选择的道路。实际上这种偏向美育育人或日艺术教育的思想在今天尤其凸显其重要价值。
其五,“散步”与感性、直觉思维。不妨说,宗白华是一个艺术研究的“散步者”,他对“散步”可谓情有独钟——“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斯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其“散步式”的偏向直觉、经验的研究方法,从他的一首小诗《世界的花》中也能见其端倪:“世界的花我怎忍采撷你?世界的花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想想我怎能舍得你,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这种研究,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式的强势武断的介入,而是首先“入乎其内”“游心于物”,感受之,经验之,在此基础上体验、感悟的思维方式。
近年来,在电影研究界,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也提倡注重经验、问题意识,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观念先行、大而无当的“中层理论”,这也成为笔者提出电影工业美学的一个方法论基础。
其六,辩证思维:“二元对立”及其超越。笔者曾论及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面对的几组“二元对立”。包括外来/本土、传统/创新: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主流/支流、中心/边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纠葛;正统/多元: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沉浮即与其他批评流派或方法的关系;现代/后现代:超越、反叛与融合的混杂。这几对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也即一种基本的“主题范式”,构成贯穿20世纪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之始终的重要线索。
不难发现,宗白华先生对包括又不止于这几组的“二元对立”均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作出了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宗白华的很多立论都从一对“二元对立”出发,如中/西、传统/现代、主流/民间、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美学/艺术理论的关系,艺术的本体/功能的关系,艺术风格的、艺术主体的抽象/移情的关系——也许正如罗兰‘巴尔特说的那样,“概念,尤其当它是成双的时候,就建立了写作的可能性”。而在处理这些“二元对立”时,宗白华恪守的都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在宗白华的艺术学思想中,还时时能够发现经常联袂出现的一些“二元对立”,如“醉与醒”“抽象与移情”“静照与绝缘”“造化与心源”“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等等。他在这些“二元对立”中辩证思考,从容出入。
三、宗白华艺术学
思想体系性的初步探索
综上所述,宗白華的理论是博大精深的。笔者试图对其艺术学本体思想,做一梳理、辨析、归纳,以期见微知著,窥豹一斑。
艾布拉姆斯曾经设置过一个著名的“艺术四要素图式”。刘若愚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础上作了自己的独特改造,侧重于展示“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构成了整个艺术过程(anistic pmcess)的四个阶段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曾经综合两家学说,构建过一个旨在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历时承续和共时发生并存关系的“艺术四维度”图式,并试图建构一个艺术学研究的学科体系构架。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成系统的创造工程,正是由这四个互相关联、彼此依托的要素或者说阶段有机组成的。分别从这四个维度切入,则可以把繁富丰赡的宗白华的艺术思想进行归类。
(一)艺道观与艺境论
艺术本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关于艺术与现实即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宗白华中国艺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对中国“艺道观”的阐释弘扬,以及由艺道观承续的、堪称宗白华核心美学思想的艺境论,都大体可以定位为与这一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艺术都是对客观宇宙世界艺术化的再现或象征化的表现,通过艺术家这一中介和创造主体与自然现实的交感契合而形成的第三种创造。真正优秀的艺术,都是“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结果,它来自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它不是自然界的某一具体的“奇峰”,却可以说是自然界的任何一个“奇峰”,因为它是自然界所有“奇峰”的某种集中和代表,它已经“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从哲学层次上的“道”与世象万物的关系,延及文学艺术与道的关系,就形成了中国艺术理论史上独特的“艺”与“道”关系的思想。刘勰是这一观念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就是探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的。《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日: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刘若愚在评价这一段话时,把刘勰的“文”“道”观命名为“形而上观念”,并认为“(刘勰)把文学的‘文与自然现象的形状的‘文合二为一,刘勰就能把文学的渊源追溯到宇宙之初,并把文学提升到具有宇宙意义的重要地位。他的观念衍生自《易经》和其他古代著作,进而推导出了宇宙秩序和人类心灵之间、心灵与语言之间、语言和文学之间多重对应的理论”,“是文学作为宇宙原理的一种显现和文饰之言的表象的观念”。
宗白华对此观念颇为赞赏并多有阐发。他借庄子在《养生主》中关于“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说明“道”与“技”“艺”的关系:“庄子是具有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在他是‘道,这形而上原理,和‘艺,能够体合无间。‘道的生命进乎技,‘技的表现启示着‘道。……‘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絪组,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按宗白华最后的概括就是:“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宗白华对“艺”与“道”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阐述,直抵中国艺术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和奥秘所在。
宗白华通过对中国艺术的分析来阐释艺与道的关系,或者说,这种“艺道观”几乎贯穿了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全过程。
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与自然界,与自然之“道”似乎更多一层密切关系。由于中国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抽象,但骨子里还保留着象形的精神,与纯粹抽象的拉丁语、西语语系不同,正如宗白华所言,“中国书法的抽象中间还有象形,有象形的文字,象形的东西就有了艺术的基础了”。因为中国汉字就因指事、象形、会意等六书的造字法而与大自然之道密切相关,而中国书法艺术更是要求书道与自然之道的合一。书圣王羲之从白鹅游水而悟出用笔之法;唐代书法家李阳冰在《论篆》中从大自然变幻无穷的景观物象中顿悟书法之“道”,“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牙齿,得摆牴咀嚼之势”;孙过庭在《书谱》中以各种奇异的自然物象与景观来形容书法之奇崛灵动,“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
宗白华曾谈到宋朝书法家雷简夫因听着嘉陵江的涛声而引起写字的灵感,“余偶昼卧,闻江涨瀑声。想波涛翻翻,迅肤掀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在笔下矣”。这正如宗白华所说:“节奏化了的自然,可以由中国书法艺术表达出来,就同音乐舞蹈一样。”由此,宗白华甚至把中国的书法艺术提升到“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的高度,揭示了书法所以成为艺术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
宗白华还非常推崇音乐与舞蹈。他借用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表达了对音乐与数学这两门最为纯粹的学科与宇宙秘密的关联:“毕达哥拉斯(Pymagoras希腊大哲)以‘数为宇宙的原理。当他发现音之高度与弦之长度成为整齐的比例时,他将何等地惊奇感动,觉着宇宙的秘密已在面前呈露:一面是‘数的永久定律,一面即是至美和谐的音乐。弦上的节奏即是那横贯全部宇宙之和谐的象征!美即是数,数即是宇宙的中心结构,艺术家是探乎于宇宙的秘密的!”因而,“音乐不只是数的形式的构造,也同时深深地表现了人类心灵最深最秘处的情调与律动……音乐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一镜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
舞蹈,则是因为除了具有音乐般的流动性、飞动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感性的直接性与具体性。生命与“道”有着更为直接的对应性,由是宗白华也把“舞”提到一个极高的评价地位:“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何以这么说呢?因为舞是“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宗白华把中国艺术精神归结为“舞”:“‘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表现着舞姿。”“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种特殊的艺术——书法,具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里面都是贯穿着舞蹈精神(也就是音乐精神)。”因为宗白华同时对音乐和舞蹈都评价特别高,而音乐和舞蹈实际上也很难分开,“舞蹈,尤其是中国舞蹈,可以说是乐舞一体,舞蹈即舞乐,是舞者与天地同和、同歌、同节”。故笔者在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时专门论及“乐舞”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表现:“中国乐舞是‘道的体现,是‘道的形式化、抽象化,也是肉身化。乐舞与空间表现有关。”关于舞蹈与空间,宗白华说过“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格”。而音乐则是时间的艺术,乐舞则成为时空艺术的综合,静态造型时则成为节奏和旋律仿佛刹那间“凝冻”的艺术形态(有人称建筑为“凝冻的音乐”)。
(二)主体论:主体精神、人格建设
这一维度主要体现在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理念、现实观念、创作观等方面。
1.充沛强大的主体性和主体观照态度
前面我们谈了艺术与道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艺道合一呢?这需要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来完成。艺术家为了能实现此一目的,即令他的艺术作品中能有所得“道”、体“道”,能暗合宇宙、自然、社会之规律,必得與世界对话,通过积极的对话,细致沉静的理解、体察和直觉性、超越性的感悟而把世界置入胸中。禅宗的最高境界(顿悟、悟道)与艺术的最高境界(意境)是相通或一致的。因为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和最高境界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虽“不着一字”,却可“尽得风流”。正如宗白华在谈到意境与禅宗时曾指出:“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张璪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极富艺术辩证法的,师法自然造化,还得与“心”结合起来,最后得之于心灵的深处。真正的艺术创造是艺术家主体与对象客体的融合,是主体心灵深处的“内形式”与宇宙自然之道的对应与合式。而张璪的这句名言,正是深得宗白华先生的激赏。在《艺境》原序中,他引述了这句话,并写道:“当我写这集子里一些论艺小文时,张璪的人格风度是常常悬拟在我的心眼前的。他的两句话指示了我理解中国先民艺术的道路。”
“静照”也是宗白华强调的一种主体艺术观照的态度。“‘静照(contemplation)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正是在“静照”中,艺术家主体“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2.泛神论
宗白华关于主体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泛神论”。作为《学灯》的副刊编辑,他发现了郭沫若的诗歌才华,认为郭沫若是一个“Pantheist”(泛神论者),“因我主张诗人的宇宙观有PantheisInus的必要”。这种源于西方的泛神论思想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如“天人合一”)不无相通之处,宗白华非常喜欢引用的王维诗句“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说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秉有的烛照万物的同化力,一种强大的主体精神和主体力量。
宗白华论及中国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时,特别谈到了音乐所具有的移情和人格培养的主要作用。他引用了《乐府古题解要》中记载的伯牙学琴于成连的故事,把“能移人之情”视为琴艺的一种极高境界:“‘移情就是移易情感,改造精神,在整个人格的改造基础上才能完成艺术的造就,全凭技巧的学习还是不成的。”这种“移情”也即沉醉于艺术,通过艺术的欣赏与自然的沉醉,与高山流水的大自然达成泛情或共情的境界,同时完成人格的养成。
3.主体人格理想
宗白华的艺术审美理想落实于主体的维度,则是与主体人格建构的理想密切相关。他对人格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曾引用德国心理学家维斯巴登的定义“人格也者,乃一精神之个体,其一切天赋之本能,对于社会处于自由的地位”。与这样的人格理解相对应,宗白华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是一种唯美的人生态度。其理想,一是“晋人的美”,二是歌德的美的人生观。宗白华倾心于晋人风流潇洒、不拘礼节、反礼教的精神,“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但宗白华对这种作为人格审美的人格力量除了美学方面的考量,显然还非常强调一种超越个体的社会的、时代的力量。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编辑后语中他说:“我们设若要从中国过去一个同样混乱、同样黑暗的时代中,了解人们如何追求光明,追寻美,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化苦闷而为创造,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请读完编者这篇小文。”
4.两种主体精神:醉与醒
宗白华在《略论文艺与象征》中说:“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两种态度:醉和醒。”这两种态度表征了艺术家与现实的两种关系。关于“醒”他解释说:“醒者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拿极客观的胸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他的心像一面清莹的镜子,照射到街市沟渠里面的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与黑暗,人心里的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并无差等。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人情物理,体会无疑。”“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散布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宗白华这里所阐述的“醒”的艺术思想,无疑很像一种积极入世,冷静理智地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以故他所推崇的作家是莎士比亚和司马迁。他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司马迁,都会留下‘一个世界给我们,使我们体味不尽。他们的‘世界虽匠心的创造,却都具有真情实理,生香活色,与自然造化一般无二。”他接着又谈到了“醉”:“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醉由梦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俗凡近,深深地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惝恍的境地。”相比之下,宗白华更为推崇“醉”的艺术精神:他认为有的“境地”“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因而“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表达。醉中语有醒时道不出的”。宗白华至为理想的艺术境界,即他认为的“最高的文艺表现”,是“宁空毋实,宁醉毋醒”。他举例说:“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手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像在他极端清朗秀美的面庞上,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在额眉眼角之间。”与对“醉”的境界的推崇相应,宗白华认为象征手法能够表达“醉”境,因为象征的要义在于以有限表无限,在于与对象拉开审美观照的距离。宗白华在这里所言及的“醉”与“醒”这两种艺术家主体精神,体现为创作方法的话,与“表现”
“再现”这一组对立范畴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醉”偏重于表现,浪漫主义化的;“醒”则是冷静清醒,偏现实主义,再现性的。
(三)作品本体维度:形式与结构
艺术作品维度的主要内容是对艺术作品形式与结构等的看法。宗白华给形式下过定义:“形式究为何?即每一种空间上并立的(空间排立的),或时间上相属的(即组合)一有机的组合成为一致的印象者,即形式也。”他还认为:“形式者如全体结构,颜色的组合,音阶的排列,节奏的调和皆是,但形式系由表现冲动而生,各艺术家之情感经历不同,表现冲动亦异,故形式亦因之终无相同者,情感经历,表现之冲动人人皆有,而形式创化力,则非艺术家不能办。”这主要是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谈形式。
宗白华还有一种艺术作品形式的结构层次分析思想。《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一文集中体现这种艺术作品本体论思想。他把艺术看作一种“三种主要‘价值”的“三层次”的集合体:一是形式的价值;二是描象的价值;三是启示的价值。分别对应于“形”“景”“情”的三层结构。从直观感相的摹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有三个层次。最后“‘形式为美术之所以成为美术的基本条件,独立于科学、哲学、道德、宗教等文化事业之外,自成一文化的结构,生命的表现”。
另者,宗白华在他未竞的哲学大纲《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中对“象”的描述似乎也可用来说明艺术作品:“象者,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
大体而言,宗白华的形式思想,既有形式超越内容而独立自足的形式主义美学特点,但又不是唯形式的,不同于部分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斩断作品本体与主体、现实等一切关联的纯形式本体论或语言本体论。他的形式观,也强调形式中的主体、生命、精神、意蕴、节奏等。因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超越了唯形式论,打通了中国艺术的生命美学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不难发现他的形式观与康德的“趣味无争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美学思想、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等的相通性。
宗白华强调形式生成过程中艺术家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交融等,则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有共通之处。在他看来,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他从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他所激赏的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显然也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
宗白华关于意境的研究可见其艺术本体思想之一斑。他对意境的分析首先体现了作品分层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思想;其次强调动态、开放,强调需要艺术主体的“静照”,“静观”才得以“打开”意境,因而他的“意境”也是动静结合而非孤立绝缘、静止僵化的。
(四)艺术接受:常人观与美育论
宗白华曾经提出艺术接受中“常人”的理念,这一概念与大众即消费社会中无名的大众很相似。他说:“所谓‘常人,是指那天真朴素,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与理论,却也没有文艺上任何主义及学说的成见的普通人。他们是古今一切文艺的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艺创作家往往虽看不起他们,但他自己的作品之能传布与保存还靠这无名的大众。……但常人的立场又不就等于‘外行,它只是一种天真的、自然的、朴质的、健康的,并不一定浅薄的对于文艺鉴赏的口味与态度。”这一理念体现了宗白华对受众的独特理解,也体现了宗白华大众化的受众理念。“常人”思想也启发了笔者在研究中国电影工业美学时对于受众之维的强调,中国电影所要服务的对象,正是这样的“常人”和“大众”,电影工业美学所打造的,亦即一种中和的、平均的“常人之美”。
对艺术接受效果的重视,对作为接受主体的“常人”的尊重,源于宗白华素有的民生、平民思想,虽然他个人的艺术趣味其实是偏知识分子精英化、文人化的。但如他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中认为的: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在于为中国“一般平民”养成精神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人生观。这与宗白华的一贯面向平民的美育思想息息相通。他曾忧虑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太困难,物质压迫太繁重”,过的是“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不曾感觉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因而,培养“常人”即普通平民的健全人格是不容易的,但又是美育工作的使命、职责与义务。因为只有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能使生命“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精神的美”。而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则是培养“艺术的人生观”,“将生活变成艺术”,完成人格教育,“‘美的教育就是教人‘将生活变为艺术。生活须表现着‘窈窕的姿态(席勒有文论庄严与窈窕),在道德方面即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行动与义理之自然合一,不假丝毫的勉强。在事功方面,即‘无为而无不为,以整个的自由的人格心靈,应付一切个别琐碎的事件,对于每一事件给与适当的地位与意义。不为物役,不为心役,心物和谐底成于‘美。而善在其中了”。在美育思想上,宗白华受席勒的美育思想影响明显。美育的对象自然主要是偏重艺术接受者即广大的“常人”的。
总之,宗白华先生的艺术学、美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本文在这里的粗略梳理,充其量只是略窥豹一斑,为进一步深入系统的总结研究抛砖引玉而已。而且从四个维度进行的梳理更是仅仅为了梳理、描叙的方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及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活动系统时讲道:“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不同的要素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从某种角度看,宗白华先生的艺术学理论、思想也是如此,是灵活自如、“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不拘一格的,也是没法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来框定的。但每一次努力都既是一次满怀敬畏之心的窥探,更是一次必要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