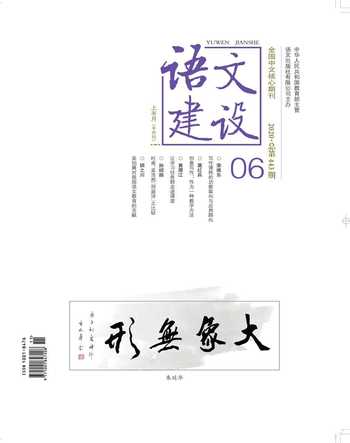杜甫、孟浩然“洞庭诗”之比较
孙绍振
杜甫与孟浩然两位大诗人面对洞庭湖,都奉献出了杰作。先来看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再来看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两首诗哪一首更好一点呢?这样的问题,按西方绝对的读者中心论来说,可能是个伪问题。但是,绝对的读者中心是空想的,读者不能不受到文本的制约,毕竟读者是可以分析的,如西方文论所说,有自发读者和自觉读者,有理想读者和非理想读者,有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对于文学教师来说,毋庸置疑的使命是,以毕生的精力争取从自发读者上升为自觉读者,从非专业读者转化为专业读者,从非理想读者变为理想读者。一句话,就是从外行读者提升为内行读者。要完成这样的转变,光凭强烈的愿望是不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批判地吸收古典诗话的成果,在历史积累的平台上,将解读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对于这两首诗,历代的诗话家们从宋朝争论至今长达近千年,似乎还没有停息的样子。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二者孰为更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牵扯出第二点:二诗之名句与全篇的关系。认为杜诗优于孟诗的争议比较少。最权威的说法出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浩然壮语也,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这个论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对于杜诗为何优于孟诗,却众说纷纭。
吴沆《环溪诗话》卷上说:“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吴楚东南坼,是一句说半天下。至如‘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说满天下。”这样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从数十里到数百里,从半天下到全天下的想象,并不是杜甫特有的胸襟。早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有“视通万里”之说,说的还不是诗人,而是一般文章作者。笼统地以视野空间之大来阐释“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好处,显然不够到位。陆时雍《唐诗镜》卷二十六就提出质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自宋人推尊,至今六七百年矣。余直不解其趣。‘吴楚东南坼,此句原不得景,但虚形之耳。安见得洞庭在彼东南,吴、楚遂坼为两耶?且将何以咏江也。至‘乾坤日夜浮,更悬虚之极,以之咏海庶可耳。其意欲驾孟浩然而过之,譬之于射,仰天弯弓,高则高矣,而矢过的矣。”叶秉敬《敬君诗话》提出:“咏洞庭诗以老杜为最。然细玩浩然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虽不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大,而要之实得洞庭真景。若老杜诗无‘吴楚东南坼一句,则‘乾坤日夜浮疑于咏海矣!”这两个人的质疑看起来有点拘泥,诗中之语乃情语,语义与日常语、书面语不同,乃非写实性质。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中对于诗的想象说得很到位:“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灵心妙舌,每出人意想之外,此之谓灵趣。”“吴楚东南坼”并不是说东南望去土地裂为二,而是可见二地之分界之远,提示视点之高,胸怀之广。至于说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之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好处在于“实得洞庭真景”,这个“真景”就站不住脚。洞庭湖的波浪若真的把岳阳城“撼”动起来,可能是一场灾难,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诗意。说它把湖写得像海,境界太大了。这个议论有点呆气,在诗歌里,不但把湖写得有海的气象,就是把山写得像海(“苍山如海”),甚至把山写得飞起来(“两山排闼送青来”),都是好处,而不是坏处。
其实,杜诗“乾坤日夜浮”的好处并不在空间,而在时间。对于这一点,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说到了点子上:“(杜诗)三四(按,即‘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雄跨今古,五六写情黯淡,著此一联,方不板滞。孟襄阳三四语实写洞庭,此只用空写,却移他处不得,本领更大。”关键在于,杜甫不仅仅是“目及”波撼岳阳,而且还“神遇”,想象天地日日夜夜沉浮于洞庭湖的波浪之中。在空间的阔大中融入了时间的流逝,这本是杜甫的拿手好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落木”是空间无限,“不尽长江”是时间无限。“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春色“来天地”,是空间透视,“变古今”是时间无限。相比起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波撼岳阳”只有空间的雄浑,而无时间的无限,在这一点上,孟浩然的气魄就给比了下去。
除这两句的比较以外,诗话家们还将两首诗整体作了细致的比较。一般来说,对于孟诗的不满集中在后面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六中说:“浩然‘八月湖水平一篇,前四句甚雄壮,后稍不称,且‘舟楫‘圣明以赋对比,亦不工。”这后面四句“不称”“不工”在什么地方呢?一般诗话家往往只下结论,不作说明。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则有比较细致的展开,王氏以之与杜甫的构思相比,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意思是,杜甫从望湖的视野,突然转入自己命运的困顿,这一大转折有潜在联想的意脉相连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钩锁”)。而孟浩然的则是前面雄浑的景观与后面四句毫不相干。毛先舒《诗辩坻》卷三中说:“‘欲济无舟楫二语,感怀已尽,更增结语,居然蛇足,无复深味。又上截过壮,下截不称。”持批判态度的还有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孟作前半首由远说到近,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
二者的批评都是从结构着眼的。这实际上是意脉的中断,孟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缺陷呢?诗话家们指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诗体的情绪结构以统一和谐为务,同时追求丰富的变化,至大的境界无以为继,必然继之以至微至小作对比。魏际瑞《伯子论文》:“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工部‘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气魄,已无可加。而孟则继之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则继之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者,皆以索寞幽眇之情,摄归至小。两公所作,不谋而合,可见文章有法。”另一方面是从诗体的功能来分析。黄生《唐诗摘抄》卷一:“(孟诗)前叙望洞庭,后半赠张,名‘前后两截格。……望人援手,不直露本意,但微以比兴出之,幽婉可法。”纪晓岚《瀛奎律髓刊误》卷一:“前半望洞庭湖,后半赠张相公,只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这本来就是一首干谒诗。前面的景观不管多么宏大,都要归结到委婉表述的目的上去。实用的目的性不管表述得多么委婉,總是要透露出来的,这样,渺小的目的就注定了要与“波撼岳阳城”的审美超越发生矛盾。从功利价值为之辩护,实在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这里比较的是诗的审美价值艺术水准。
杜诗之胜于孟诗,不仅仅在于纯粹抒情,更在于其结构。表面上看,从宏大的景观到个体的悲叹,其结构与孟诗极其相似。谢肇涮《小草斋诗话》卷三外编:“襄阳接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已觉索莫不称;少陵接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愈见衰飒。信哉,全璧之难也!”这是只看到杜诗与孟诗在结构上前后同样有反差。但是,孟诗意脉断裂,而杜诗意脉密合,这一点要害被忽略了。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引黄生的话說:“写景如此阔大,自叙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这本来可能引起结构不和谐,但是浦氏以为不仅不矛盾,相反是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这种对立而统一的理由,也可以用到孟诗中去。回过头来看黄生《杜诗说》卷五的原话,可知矛盾的转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前半写景如此阔大,转落五六,身事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结语凑泊极难。”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愈是对立,统一的难度愈大。使得这个对立得以不着痕迹地转化为统一的是:“不图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也。”与杜甫相比,孟浩然在转入个人愿望之后,就把前四句开拓的宏伟境界丢在一边了。而杜甫“乾坤日夜”之胸怀,又与“戎马关山”之远大笔断脉连。有了这个密合的联想,意境就和谐了。表面上看,杜甫比之孟浩然的情绪更加个人化,反差更加强烈,感伤到流泪的程度,但是,意脉连续性却更有层次,更加有序。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杜诗)上四写景,下四言情。‘昔闻‘今上,喜初登也。包吴楚而浸乾坤,此状楼前水势。下则只身漂泊之感,万里乡关之思,皆动于此矣。”这就理清了杜诗的情感脉络:从“昔闻”到“今上”之喜,再到景观宏大之壮,再到戎马关山之痛,引出亲朋无信之悲,情感层层推进,摇曳多姿。佚名《杜诗言志》卷十二说得明白:“盖昔闻此水时,只在天末,未必今生果能目睹。乃不料乱离漂泊,一程一程,竞流落到此。是今日之上,又迥出于昔闻之意外也。以此身世俱远,不独亲朋不见,并一字俱无。而老病随身,别无长物,只此孤舟一具。是‘昔闻此景,‘今上而见此景;而‘昔闻之情,则不料有今日之上之情也。是此四字,写一时隋景俱到。”这个说法把杜诗的意脉贯通说得比较精致。延君寿《老生常谈》说得更为严密:“工部之《岳阳楼》第五句‘亲朋无一字,与上文全不相连。然人于异乡登临,每有此种情怀。下接‘老病有孤舟,倘无‘舟字,则去题远矣。‘戎马关山北,所以‘亲朋无一字也。以此句醒隔句‘凭轩涕泗流。亲朋音乖,戎马阻绝,所以‘涕泗流。‘凭轩者,楼之轩也。以工部之才为律诗,其细针密线有如此,他可类推。”杜诗意脉之统一,层次之丰富,用字之严密,孟诗实在不可望其项背。
当然,孟浩然的诗也不能说没有意脉的暗连,如从湖水联系到舟楫,再到垂钓,但这只是字面上、形式上的联想过渡,而在内涵上,湖水的“涵虚混太清”“波撼岳阳城”,则与后面的干谒根本脱节。毕竟形式联想上的机制不能挽救内涵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