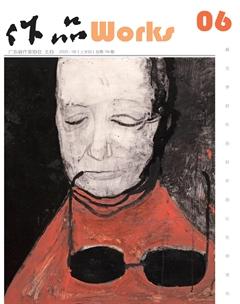在世界的版图写诗(评论)
蔡岩峣
2009年一次参观歌德故居的经历促使杨克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用平仄的汉语敲门/走进你二千五百首诗歌里/一蓬翠柳刺破墙头的秋色/德语的音节轻重扬抑/惊飞两个鸣叫的黄鹂//先是站在浮雕前与你合影/我身着西装牛仔/心依旧罩着一件长衫/东西方诗人朝着各自的方向凝望(《歌德故居》,2009)。如果说杨克“凝望”的是以歌德为代表的诗歌辉煌时代,那么歌德“凝望”的又是什么?在杨克的语境里,或许是那个颇为经典的“世界文学”幻影。悄然两百年光阴已逝,德国文豪的伟大预言似乎仍遥遥无期,然而在歌德的目光里,一种指向世界的写作却深刻地烙印进其后每一位具有时代抱负的诗人内心。在杨克的近作中,这种指向世界的气质益发清晰。
一、世界经验:画一张诗歌的世界地图
杨克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二十年《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者,因此评论界往往爱用“人民性”“民间性”“城市性”等概念对其作品进行阐释。然而与重复的写作令人厌倦相同,重复的阐释是对被阐释者与阐释者的双重消耗。那么,有没有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杨克的作品?在诗人的近作中,笔者试图撷取出一个新的特质:“世界性”。
这种“世界性”当然首先表现为一种物理经验的“世界”入诗。在他的诗歌精华集《杨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中,第一辑“苹果的另一半”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经验”的诗作集成。《地球 苹果的两半》《大》《罗姆尼新罕布什尔胜利集会》中的美国,《际会依然是中国》中的波兰,《给那个踢球的人当一回总理》中的西班牙,乃至稍前期的《人民》组诗之二、三、四中的伊拉克、卢旺达、苏丹、德国,《德兰修女》中的印度等,杨克用诗歌的笔触描绘出一幅世界地图,且这幅地图并非是对某一特定文化区域的想象与认同,它涵盖面广,美洲、欧洲、亚洲、非洲都有,涉及的题材也很丰富,政治、风物、艺术、体育都包括。如果说,前期有关世界经验的诗歌是作家“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么近年来,随着诗人走出国门,真正融入诗歌创作共时性的世界诗人群体,其完成的系列诗作则可视作某种带有自觉意味的追求。
如《热带雨林》(2018)中“亚马逊河流域和刚果河流域”“马达加斯加岛东岸”和“云南西双版纳”并举,不同空间下的热带雨林呈现出某种共同的、本质的特点即生命的“平等”与“茂盛”。再如《狗年在美国自驾车沿途听六神磊磊说唐诗》(2018)中,加利福尼亚公路上的经历与“诗仙诗圣诗佛诗狂诗魔诗豪诗囚诗鬼”的记忆巧妙融合,在某种“仿七律体”的结构中,中国元素与美国元素拼贴、融合、安置,浑然天成。
“世界经验” 作为一种主体化的“现实”并不是某一位诗人的追求,而实质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文学潮流的必然产物。“我们今天在英文中所描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由两个词组成的:cos-mos来自希腊语(κ?σμο?)意为宇宙或世界(universe),polis来自(Π?λη),意为城市或城邦(city or world state),这样我们就有了‘世界这个词。那些信仰其伦理道德的人便被人称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es),而他们的主张和理论教义便被称为‘世界主义。这就是世界主义概念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的形成。”[1] 在最早的一位“世界主义者”第欧根尼那里,自己的归属从来不限于某一个固定城邦,所到之处即是“家”。正是因为所到之处即是“家”,所以才能了解和转化从“此处”获得的经验从而写诗。把世界主义理解为抹除自身的民族-国别身份无疑不对,就像爱国与爱世界从来不对立一样,只不过评价一个诗人好坏的标准在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两种文化之间精妙的联系,并用诗这种特殊的文体给予传达。
地球是一个苹果/字母O是上帝挥起球棍/击中的棒球在宇宙不停翻滚(《地球 苹果的两半》2014)。据说这是诗人在西方世界最受赞誉的一首诗,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杨克诗集即以Two Halves of the World Apple命名。苹果(Apple)在西方的语境中无疑具有某种“神话原型”的意味,《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就因为偷食了金苹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宣告人类乐园时代的终结。今天,由史蒂夫·乔布斯创立的电子产品品牌“苹果”更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选用“苹果”这个意象,与字母O进行直觉关联,由实入虚,再用一种神话展开的方式,将其作为上帝与棒球、宇宙与地球关系中客体的喻体,不能不说精妙至极。而后三句:我很得意这美利坚的隐喻/却醉心于祖先的太极哲学 东西两仪/犹如首尾相衔的阴阳鱼,又在强烈的语境压迫下保持比喻的关系,并迅速完成一种文化的置换,从而构成与前文的张力。西方的哲学观念是“上帝完成了第一推动”,挥舞着棒球棍在宇宙中给予地球这个现实世界以一击,而东方的哲学观念则是“循环调和的阴阳两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生不息。诗人通过文化意象的摄取,在经验表述的层次之上进入到某种语言与哲学关系的思考,通过简单的两个比喻使西方与东方的世界观发生沟通,这无疑是当代巴别塔建造的全新实践。诗的结尾是:你一条微信/鲸鱼一般游过太平洋/苹果和另一只苹果/在手掌里 东半球与西半球/那么近 如同两个邻家女孩。蹈空的思辨还是回到最现实的生活,从神话原型的“金苹果”到苹果手机,一条微信,一只穿越海的“鲸”,可能就在描绘着此刻这幅世界文化地图的经纬。
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中,以“世界经验”入诗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穆旦写过死亡恐怖的“边缅丛林”,多多写过“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但杨克诗歌中的“世界经验”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改革开放时代的经验,由于中国在世界版图中整体地位得到提高,这种经验更能被当地所认可。
以《又见康桥》为例,作者给这首诗题写的题记为:“2017年7月末再次参加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徐志摩诗歌艺术节有感,2018年2月写于美国俄勒冈。该诗与拜伦、华兹华斯、徐志摩等数百年来写剑桥的诗一同收入英文版《剑桥最美的诗》。”两次参加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并获银柳叶诗歌奖的杨克感叹,到底是要写一首关于徐志摩的诗了。在这首《又见康桥》中,除了向那位经典的现代诗人致敬,并复用其意象与语式,最让笔者感叹的还是这一节:今夜我代你回到英伦/正如当年你代我离开/两个天空争抢/一袖子带不走的云彩。不同时间内的两种经验被共置到同一空间中,而这一处空间又如此富含可解读的意味——“康桥”。徐志摩笔下的“康桥”作为新诗人追求的现代性“幻景”被此刻的杨克完成,因此,现实意義上的“康桥”亦被虚化为跨越近一个世纪,东西半球近8800公里的文化联结纽带。拜伦、华兹华斯、徐志摩、杨克,在物理世界内几乎不可能发生关联的几位诗人,也终于在同一个文化文本中得以晤面。在此意义上,杨克诗歌所勾画出来的世界地图也就终于不再是某种表象的“世界经验”复合堆叠,而是指向世界共通文化肌理的“地图”。
可以说,“现实性”与“文化性”是杨克诗歌“世界性”的两个维度,然而使杨克真正在一种“景观式”的世界描写潮流中脱颖而出的,却是其“世界性”的第三维:“参与性”。在创作于2006年的《人民》组诗二、三、四中,杨克已经对当地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设身处地的思考与“参与”,而写于2012年的《罗姆尼新罕布什尔胜利集会》则可以视作对这一组诗的延续。该诗以2012年罗姆尼和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大选宣传的“事件”入手,细致描绘了两人选举集会的不同风格。以音乐作比,罗姆尼的集会近似“乡村”(Countryside),而奥巴马的集会则是“摇滚”(Rock&Roll)和“说唱”(Rap)。诗歌精彩的部分当然不在前百分之九十的细节记录,而在于全诗那个颇具黑色幽默的结尾:明天,明天投票的结局怎样?/今夜已一目了然/选民是一滴滴水珠/汇聚口若悬河的奥巴马/可说不定罗姆尼这种低调平和的人/才能真正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像他能让盐湖城冬奥会赢利/可选民却不再给他一天。对奥巴马的揶揄,并不一定代表对罗姆尼执政观点的认同,诗人只是用一种相当轻松的姿态进入美国的政治语境进行解构。如果说在《人民》组诗二、三、四中,杨克考虑的是第三世界的苦难,那么《罗姆尼新罕布什尔胜利集会》中,对第一世界“精英政治”的反讽则更可以视为一种创新。
二、形构中国:诗歌世界地图里的中国
只在宏观层面对世界作总描绘是不行的,就像画家,想画出好的“写意”还得有“工笔”的功夫。对于杨克来说,这“工笔”无疑就是写中国。
关于中国的诗杨克写了不少,粗的、细的都有。有《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那样从精致的比喻入手,从思辨到经验的诗;也有《人民》那样纯粹从感性经验入手,从经验到思辨的诗;当然,《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那样在具体化的某一块土地上透视整个中国城市化变迁进程的经典之作,也常为人称道。其实,由于杨克诗风温暖(杨炼语)、悠扬宽广(陈晓明语),其写中国的诗往往达不到那些“激烈”作品的爆炸效果,因此不够“出风头”。即使话题性很强、争议性很大的那首《人民》,在笔者看来也着实是诗人的诚意之作,无意作博人眼球之姿。在第三代诗人群体中,像杨克这样持续保持对国家思考,从微观与宏观层面予以表现的其实不多,而温柔敦厚的诗风更助益了其写作的耐力与长性。
观察诗人近期“写中国”的作品,可以发现,以往诗人常用的“城市/乡土”张力结构,似乎在往“世界/中国”的张力结构转变,这确乎是值得注意的事。
所谓“城市/乡土”张力结构是指,诗人诸多“城市之诗”所描绘出来的“显中国”,其实与一个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隐中国”对应。无论是“天河城广场”上的消费景观,还是各种各样的“时尚主题”,其所以具有时代语境下的阐释潜能,在于中国实际上还处在一个以乡土文化为主导,乡村人口占主体的发展阶段。“城市之诗”不能单作为“城市景观”来解读,而必须放在这种“城市/乡土”的张力结构之中,才能读解出更深刻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2001)能够具有突出历史价值并被评为经典的原因。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这是工业与城市对农业与乡土必然取代的现实状况下,后者所作的最后坚守。昨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东莞/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之间。这不仅是稻穗的欣喜悲痛,同时也是诗人和所有“被时代裹挟者”的欣喜交悲。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虽然“城市/乡土”的张力结构依然存在,但其“及时性”的意义已有逊色,且在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乡土文学作品稀释之下,诗歌作为精神与形式探索的先锋也就无法再在这一结构之中发挥效力。诗人必须重新考虑“形构中国”的问题,而杨克选择的角度是“世界/中国”。
在《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2006)的参照下,来读《我的中国》(2019)这首诗。杨克坦言:“上海作协的朋友,希望我再写一首祖国之诗给他们的晚会时,我认为这无法完成。因为写祖国,与创作其他诗一样,不是写套话、大话、相似的话,而是要寻找新鲜的角度,要具体而细致,可感可触摸。我13年前写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自以为几乎写尽了想象与联想,无法超越了。”[2]杨克此言不虚。从石榴果肉的亲密无间联想到人民相亲相爱自然寻常,但从果膜包裹的石榴籽聚合联想到省与省的相邻开始,诗人逐渐把石榴与中国一一对应。石榴的裂口是人民的苦难,石榴的枝条与花朵是多元的文化与精神,及至石榴树头顶的太阳则是一个“纯化”了的祖国之表征。最后,石榴树外还有一个我,主体与客体跳出意象的装置之外发生联系,我伫立在辉煌的梦想里/凝视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如同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掏出一颗拳拳的心/丰韵的身子挂着满树的微笑。既有佳作在前,如何再写中国呢?答案在“世界”。
“英国利兹大学邀请我9月份参加他们的一个诗会,之后我打算顺便旅游几天,我到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办簽证。等待面签和打手印期间,灵魂深处的记忆突然被唤醒了,灵感倏然降临。20年来,我受邀参加过好些国家的诗歌交流,每次出国几天后,最怀念的,是中餐,在外语环境里,最亲切的,是看到中文听见乡音,于是,有了突破口,我找到了进入这首诗的写作路径。”[3]《我的中国》里,纷繁的中国元素正是在这种“世界地图”的背景下展开。“中国美食”的精彩,在周游列国后受折磨的胃里感受到了;“金黄谷穗和黑铁齿轮的国徽”在海雕金狮双头鹰的国徽对比下感受到了;女高音《茉莉花》和小提琴《梁祝》在金色大厅里感受到了;北极熊、袋鼠和熊猫在同一个动物园里感受到了;看过了欧洲的石头城堡更感受到江南庭院的美;听过了《蓝色多瑙河》的曼妙更领悟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雄浑。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国”而变得具体、细致、可感,这可以视为汉语新诗表达新的突破。
在顾城、张枣的诗里,中国是文化记忆,剪不断理还乱;在北岛、多多的诗里,中国是巨大的他者,值得批判但不具备走向世界的意义。然而,正在进行的将来时态中,形构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仅是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电影导演、画家等文艺工作者都将面对。中国叙述的“中国”虽然未必能在上帝视角代表某种绝对的合法性,但却是一种世界主义潮流下有效的“反东方主义”式应对。而应该形构怎么样的“中国”,以及如何“形构”中国,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杨克形构的中国是当下的现实中国,也是文化中国。在《海浪》(2019)、《诗歌林》(2019)、《洋山港自动化码头》(2019)、《蓝鲸雕塑》(2019)、《霍童溪的石头》(2019)、《人杰地灵》(2019)、《柳叶湖》(2019)中,中国一幕幕的现实图景,诗人以真实之眼摄入,并用诗性之笔绘下;《大东湖》(2019)《平凉行》(2019)、《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2019)《非虚构族谱》(2019)、《新桃花源记》(2018)、《风度张九龄》(2018)、《在瓦口关品茗》(2017)中,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则经过转述重新获得现代生机。实际上,偏重哪一类都有问题,出入现实与文化才是将中国绘入世界文学版图最好的方式。以电影类比,从之前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文化中国”被质疑“东方化”,到第六代导演娄烨、贾樟柯的“现实中国”被质疑“矮化”,文艺创作要探索的正是一条两相融合、兼具的道路。
在形构的方法上,杨克当然一直未脱“第三代诗歌”基本的艺术主张,注重语言的平实、朴素与经验性。但在此之余,诗人的某些沟通传统又不失现代色彩的作品却极有趣。如《赴香港城大紀念杜甫千三百年诞辰戏仿杜甫》(2012)这首诗中,全部化用杜甫26首诗歌中的名句。在属于“文化中国”的系列诗作中,《非虚构族谱》《新桃花源记》《风度张九龄》等都可以发现诗人这种试图跳出现实束缚,重新捕捉诗性灵光一现的“冰雪聪明”。
三、“介入”:绘图与形构的方法
无论是以“参与”绘画诗歌的“世界地图”,还是以“世界/中国”的张力结构“形构中国”,其背后根本不变的诗学观念在于“介入”。这种“介入”是杨克一直以来的诗学主张。
早在1986年“两报现代诗大展”中第三代诗人集体亮相以后,第三代诗人持续写作的原动力就在于将原属于“朦胧诗主流”的话语权力从精英那里夺过来,并重新安置到一种名为“民间”实为“自由”的言说空间之中。然而伴随着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后不断深化的后现代语境,诗人们发现自己的言说并不是不自由,而是太自由了。网络诗歌、下半身诗歌等,将自由空间的边界无限扩展至再度不自由化。这种再度不自由化意味着,在题材无禁区的言说空间中,除了置换经验的新奇性,无法再在思维、语言、智识等方面给出新的突破与尝试。因此,经历21世纪论战中的另外一方完全有理由进行如下诘问:“这就是你们要的民间立场与自由吗?”
另外,受西方当代诗歌影响的“技术主义”重新席卷当下的汉语新诗写作。众所周知,第三代诗歌以后无主潮,如果说非要概括一种潮流,那就是技术主义的回归与重提诗歌的“智性”。在近年来较受关注的北大“未名诗歌节”与复旦“光华诗歌节”参展作品中,符合上述诗歌特质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这意味着,在年轻诗人群体(以大学生为主)那里,“智性”取代了其他概念成为首要之义,而这无疑可以视作对第三代诗歌遗产的一次反拨。在这种反拨过程中,读者也不难发现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某种“精英面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克诗歌的意义更加明显。21世纪面向世界的中国诗歌不应只是智识的游戏,而应与现实发生更密切的关联。所谓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法”要以“中国经验”为先决条件,在第一线的文艺创作者那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在《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2012)这首诗中,杨克的“介入”之姿明显。城市的高楼越建越多,但在繁荣的表象背后是深刻的“不平等危机”: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可似乎并不被高高在上的国家掌控/也跟为口腹忙碌的蚁民无关/一枚大印在暗地里把几个人的商机/盖得皇天浩荡/开发商是承包大户,贷款雇人耕种/种植能手依旧是农民,那些长工短工/戴上工人的安全帽/粮食不断涨价,政府和商人赚个盆满钵满/财富和政绩芝麻开花节节高。在全诗的最后一节那个经典的“矮脚稻”[《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2001)]意象又出现了,这次出现,其代表的含义不再是时代发展过程中某种可被理解的无奈,而是被拆迁者权力受损的一个明证。当宏大的时代主题聚焦到个体身上时,其蕴含的暴力性与残酷性就淋漓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体现需要有人诉说,而杨克承担了这个责任。
其实回溯杨克早年的诗歌作品就能发现,“介入”一直是他的诗学追求。对比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类作品,杨克的《天河城广场》《在商品中散步》《广州》等,并没有选择直接走向“现象的反映”和“语言的狂欢”,而是穿过语言,继续进行对现实生活的思辨。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这种中正的取向似乎比较保守,但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保守”对应了某种只能在未来才能兑现的价值。在一篇与阿斐的对谈中,杨克提到:“我要表达的只是一种大的走向,诗歌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窄了。我们要不要恢复更开阔更撞击胸腔更与人们生存的公共空间有某种关联的写作。”[4]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在《光影编码的摄影哲学》(2017)这首诗里,诗人有意无意将诗与摄影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关联起来,从而营造出丰富的阐释空间。诗歌,特别是“介入”的诗歌,在当代生活中到底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高于额头的天眼/手指轻轻按下快门 告别经验/咔嚓打开双重视野 像素的火眼金睛/将古与今的焦距 对准/一个簇新的花园/这个世界存在吗/众生诸物 若近 若远。诗歌里的世界与镜头里的世界一样,在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消失之后,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不仅是传播的歪曲和阐释的误解,甚至连诗人本人都要怀疑自己写作的真实目的何为。凭借镜头的引领大师们“洞见”“捕捉”,我们无法不怀疑这样的“洞见”是炒作而不是真诚。在这首优秀的作品里,杨克对现实世界的“影像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刘禹锡时任连州得诗七十三首/当今刺史打造国际摄影城,是一种时空鲜明对比下的现实景观错位,古与今对现实的重述纯然不同。连州在单反镜头/替无雪的岭南下了第一场初雪,更是标准的“后现代事件”,真实地介入需要介入的真实,否则没有意义。外国摄影家频频地曝光/连州人也有幸见识了超现实世界。最后,在一种“世界”的语境下,诗人点出了这不是某一部分人的遭遇,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危机。可以说,《光影编码的摄影哲学》是诗人近期的最佳之作,其对现实的深度理解,对诗歌手法的娴熟运用,对哲学层面的超越反思,都达到了相当完满的高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完满依托的不只是中国的现实,还是一种世界版图之中的“中国现实”。
无论是“写意”这幅诗歌世界地图,还是“工笔”这诗歌世界地图里的中国,你都无法不喜欢,或说无法不重视杨克的诗学观点,因为在他的观点背后站着的,其实是他诗里反复提及的诗圣杜甫。从写作的气质来看,杨克没有杜甫的那种沉郁顿挫,其时常流露出来的自信与轻松反而更像另一个常客苏轼。作为诗人的杨克,其现实境遇当然要比两位诗坛前辈更有余裕。杨克常说,自己是一个比较“顺”的诗人,正是这种“顺”造就了其不急不慢的特征。按加斯东·巴什拉以“火、水、土、空气”对四种本原性想象法则进行划分的标准来看,杨克属于“空气”。“正如一位旧时作者莱希于斯(Lessius)在《长寿的艺术》中写道:‘肝火旺的人的梦幻是火,大火,战争和谋杀;心情忧郁者的梦幻是下葬,坟墓,忧虑,潜逃,坑穴以及各种各样的悲伤事情;黏液分泌过多者的梦幻是湖泊,河流,水灾,沉船;多血质的人的梦幻是鸟飞翔,奔跑,盛宴,合奏,是一些难以命名的东西。因而,肝火旺的人,心情忧郁的人,黏液分泌过多的人,多血质的人各自分别由火,土,水和空气为特征。”[5]继承杜甫的现实关怀是十分重要的,以一种“飞翔”的姿态高于现实世界进行反思也同样是重要的。在经历了“苦大仇深”的20世纪以后,中国诗人有理由,也应该以一种从容淡定的姿态在世界的版图写诗。
注释:
[1]王宁.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J].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2]杨克.记忆中那一阵桂花飘香是我的祖国[J].粤海风,2019年第2期。
[3]杨克.记忆中那一阵桂花飘香是我的祖国[J].粤海风,2019年第2期。
[4]杨克.阿斐.诗歌的精神是自由,也是收敛[J].南风窗,2016年第25期。
[5]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顾嘉琛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5月。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