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回顾青葱岁月
邓郁

图/本刊记者 梁辰
66年人生里,大概沒有哪一场雨,会比1994年北京城的那一场,让学者金雁更嗟悔和心痛。
那年金雁结束波兰的访学调进北京,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当时单位给她分的房子在北外附近一幢6层红砖房里。
因为空间狭窄,她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挪到了阳台上。谁料碰上一场瓢泼大雨,家里没人,门窗敞开,屋里淋得狼狈不堪。回家后,金雁急慌慌地抢救被雨打湿的书籍,却忽视了阳台上的旧物。很多天之后想起来再看,年轻时和父亲的通信、自己的日记早已发霉板结,笔迹掉色,晕染成一片片,无法挽救。
身为西北局干部子弟,金雁经历过票证时代的短缺经济,目睹了老辈人的公私合营,以及全家下放、从相对舒适的大院搬到干旱苦寒的甘肃定西。一系列政治运动、工农兵学员的光环与失落,统统都没落下。两代人的书信和日记成为历史的明证。
“起初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觉得当年那些幼稚的笔触、带有浓厚时代语言痕迹的东西价值不大,算不上什么太珍贵之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个体记录的感悟,每每想起来都会心痛不已。如果有这些文字材料作为辅助,帮助回忆就会准确容易得多。”金雁抱憾。
直到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如今,金雁都常常会梦见,自己用电脑帮父亲抄写检讨。“我(在梦里)跟他说,有了这个东西就方便了,再也不用一遍遍地抄写、改正。那个时候稿纸改得真是一塌糊涂,因为你写的老通不过,明明自己没有的东西非要上纲上线,是非常痛苦的。”
遗憾不止一桩。父亲当年受到批判,金雁小时候经常听到议论,除了大环境使然,还有人性恶的一面作祟。等她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父亲已经得了脑中风,丧失了语言功能。“再往后,我意识到,不是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被罗织在一张网里,(出问题)只不过或早或晚。”
好在还有父亲从1938年到1978年整整40年的日记。几年前,她开始写回忆文章,2020年春结集成《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出版。她一直认为,和自己从事的有关苏俄史、东欧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俄国知识分子等学术研究相比,这类随笔属于可有可无的“闲文”,没想到却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肯定和在线追等。历史学者雷颐指出,虽然那些风波很多家庭都经历过,但金雁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亲历过西北局这个特殊历史机构,她从干部子弟到民间的历练与感悟颇为难得。“尤其年轻一代建议读,否则历史就(被)泛化了。”
“浊自浊清自清”
书中的第一张照片,是1960年代初金雁姥姥李彩绚和姥爷的合影。姥姥眉目清秀,简单的收领棉服和发式也盖不住五官的大气雅致。手自然地搭在腿上,眼里笑盈盈的,给人一种平静的力量。
但正是这位慈眉善目的姥姥,不断激起童年金雁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
李彩绚的父亲李佩实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1920年代经营皮革厂和布庄,后来到天津发展,“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织线毯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姥爷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家里坐拥日据时代棉纺厂的木楼,花布沙发、冲水马桶不说,连碗盘都分米饭碗、面食碗、鱼盘、汤盆、水果盘。
在西北局大院长大的金雁,成长的环境再简单不过。“好像觉得世界上就红和白这两种颜色,到了姥姥家,咿,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这样的物件?”
1965年,金雁去天津治疗眼睛,住在姥姥家。那一年也是外孙女和老人的“博弈”之年。她不爱听姥姥给她讲述老辈创业发家的经历,反驳“还不是剥削得来的”;厌烦跟着姥姥去探望舅姥爷、姨姥姥之类的“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居然有人称呼姥姥为‘大小姐,听着别扭死了。”
姥姥告诉在外地的父亲,父亲写信批评金雁不尊重老人。但那个年份正高谈阶级斗争理论,11岁的金雁已经会用报纸语言顶撞父亲。“我父亲知道其实这些眼下时髦的东西,不是做人之根本。他不愿意我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但又不能告诉我,这是政治流行的宣传语言。”左右为难的父亲,只好召回了金雁。
好些年之后,金雁才看懂了姥姥——不但是个很懂生活的女性,而且早已阅尽世态炎凉。当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连家人一时都难辨真伪,姥姥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浊自浊清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
金雁有三个舅舅三个姨,姥姥总能把每个小家都照顾周全。只要谁家大人缺位,她立马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眼前,而且手里总像变魔术一般掏出一块奶糖、一把花生、几粒虾仁来。用姥姥的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金雁暗自惊讶,姥姥小小的个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虽然是“资产阶级大小姐”,但各类生活小窍门如数家珍:染过的衣物用盐水浸泡不易掉色,白球鞋刷过之后蒙上一层白纸晾晒不会泛黄,用白醋浸泡泛黄的浅色衣服可使颜色重新鲜亮。
有了姥姥这些结实的生活经验垫底,什么样的日子,金雁觉得都能对付了。
少年时,她爱上阅读和思考,来自父亲濡染;后来尝试画画、爱做手工,遇到大事不慌,爱笑,多少有姥姥的影子。跟着爱缝纫的姥姥久了,她学会了改衣服。“其实衣服改成什么样倒在其次,从坐下来拆、量、缝、熨的过程中,心一下子就能够沉下来,可以像旁观者一样把自己抽离出来,冷静而平和地看待问题。”衣服改完,心情也调整复位了。
小小“生命供给者”
采访那天,摄影师选中了金雁所在小区的一片石头景观作背景。只是,老有那么几袋施工留下的水泥袋,“不知趣”地和拍摄对象同框。摄影师正走过去想搬走水泥,穿着半截裙的金雁径直上前,把几十斤重的水泥袋徒手搬到几米开外。看着文文静静的女教授一点不含糊,让人一下想起了她笔下的陇西担水岁月。
1965年,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的金雁父亲被发配到西北农村的基层生产队去“改造思想”。那年儿童节,金雁离开了从出生就厮混在一起的伙伴,和当时算得上舒适的大院生活,与家人一道迁往甘肃省的定西专区陇西县。

1970年代初,在供銷社任职的金雁 图/受访者提供
定西长年干旱、赤贫。她后来下乡插队的地方,老乡们早上起来洗脸都用碗,一共三口水,一口漱嘴,一口擦眼屎润脸,剩下一点搓搓手。那时整个陇西县城有六七眼长年不断水的方井,金雁他们家离每一眼井的距离都在一里路以上。父亲要去生产队“劳动锻炼”,母亲要上班,挑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兄妹三人的肩上。
两个成年人用的大铁皮桶,装满水有七十斤重。桶大人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金雁通过观察和琢磨,发现挑水要用巧劲,“起身要稳,走路要扭,腰肢借着扁担摆动的节奏使劲。我还懂得水桶上有漂浮物,摇晃中的水就不易洒出去,于是夏天摘两个向日葵叶子,冬天放两块三合板。”
她自称是家里“70% 的生命供给者”——因为课本里说,人体物质的构成70% 以上是水分。
但比起后来在北部山区插队的弟弟,她已经算好很多。陇西北部要吃“窖水”:挖一眼窖,把雨水积攒起来沉淀后饮用。窖底积的水如黄泥汤,也被当成“活命水”。去看弟弟时,他给金雁讲过一个故事:村里一个小伙子,盛了半碗干炒面,本来应该加水搓成块状吃,但他整个脸埋在碗里吃得急,竟让炒面给呛死了。
多年后境况改善,姐弟俩对水的态度大相径庭:金雁在家,洗衣服剩的水会留着再洗拖布,“恨不能上厕所都赶堆的,为的是少听一次那让人心疼的流水声”;弟弟却什么都可以省——就是不能省水,“见了水亲得跟什么似的,恨不能把上半辈子欠的水债全补上。我也能理解他,因为当年的生活烙印太深了。”
爹妈不在,自己当家。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脖子上挂着钥匙行走,用老人的话说,“像门后的笤帚一样,搁在一边就长大了。”
她跟着男生一起运煤,脱煤;和女生一起拾柴,“剥麻秆”(陇西种植亚麻,亚麻长成割下来先在池塘里沤几天,等纤维与茎秆剥离后便可剥麻)作引火材料。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地方,她照样学会了腌咸菜、做浆水(当地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做搅团、补鞋,挑和身体等重的两桶水,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

插队的日子 图/金雁
父亲说过,艰难岁月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男孩一样的装扮给金雁添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而在异域旷野和汹汹而来的运动里,她也锻炼出了不怯场、不轻易服输的个性。
甚至还培养起连父亲也不太擅长的技能:学会一口溜溜的当地方言,和乡民们打成一片。“随着局势变化,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多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我父亲是搞理论工作的,他不太能够在人际关系上打得火热,只是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当中。我母亲后来就要好得多。每次邻居们向妈妈要点边角纸张或喂鸡的落土粮食,她都尽可能地有求必应。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爸‘金老师,叫我妈‘他金婶。看似没区别,其实透着亲疏的。”
饥馑之困与供销之谜
父亲沦为“黑五类”,金雁兄妹虽然偶尔心底里无奈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拜和谐的家庭气氛和开放的教育所赐,不能读书的年代没有被完全荒废。随着生存能力和抗压力的生长,她也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例如极度的贫苦究竟源于何处。在陇西她结识了一对姐弟,姐姐叫“改改”,大冬天光身板穿着一件烂棉袄,“她说她从来没穿过毛衣、没穿过袜子。弟弟坐在炕上,就是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在她插队的生产队,光景最差的家庭,碗、盐都买不起。把盐化在瓶子里,吃饭的时候用筷子伸进去搅一下,在锅里涮一下,就算吃盐了。
虽然情况比改改家强得多,但在菜子公社插队的金雁也会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她曾和几个知青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几个人走了15里山路,好不容易拉了一口袋120斤饲料玉米回去。然而等到月亮爬出山坳,大家才看到玉米里有太多沙粒和小石头,没法下锅,还得先晾晒簸干净。
就着凉水嚼饲料玉米,有同伴抽泣哭出声来。已经心肠变硬的金雁没掉泪,脑子里反复盘旋着小饲养员的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她心里犯起嘀咕:为什么所有人累死累活,就是养活不了自己呢?不论是期盼父亲平反,还是指望招干招工,她还是存着“他日跳出农门”的念想。公社搞返销粮,可当地农民呢,他们种的粮食为何不够自己吃,有没有改善生活的一天?她陷入了困惑。
1972 年,金雁被分配到离县城40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按1950年代初推行供销合作的初衷,它应当是农民自发的结社购销。然而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供销社演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金雁所在的供销社是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相当于县商业局的分支,完全处于垄断地位。“农民自己种的米,养鸡下的蛋,都不能买卖,卖就是违法,必须送到供销社去。”
她回顾,“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文革时期又第二次被收上来;1975年又与国营商业分离,变成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不过,两次‘下放都不是真正恢复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供销社的经营更与他们无关,对屡次的‘折腾也没有说法。”
金雁到供销社时,刚刚经历过“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甚至有人因贪污罪自杀——多半是因为货物短缺一时说不清楚。
会计出纳们最怕的是盘点,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一打三反”后改为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账、货、钱“三清点的三讫”。社里规定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不能超过“个位数”,也就是10元以内。
对这个规定的“不近人情”,下面多有怨言,但都不敢提。一次,金雁在工作当中吃惊地发现,鞋帽组老实巴交的师傅,床下居然藏着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价值大约在两百元左右。
“难道是私藏、贪污?”她犹豫半天,问起老营业员才得到答案:“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大家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从顾客那里克扣出来。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惯例。”她这才明白,鞋帽组师傅的一箱鞋帽,是用来贴补盘点差额的。
“不近情理的苛刻盘点要用这类办法应付,不成了越反越腐了吗?”她有些迷惑,但也无处诉说自己的感受。但渐渐明白,不是所有的规矩都理据充分,不是所有的“违规”都该一棍子打死。
在商业局系统的那几年,金雁耳闻目睹了好些女性的风雨人生。在《五朵金花》这篇阅读量很高的文章里,她引为业务偶像的“算盘仙”A,与飞行中队长结婚,没想到贪污近两千元,获刑10年;年轻貌美的B被猥亵后与大自己20岁的男人速婚;风风火火的播音员、团委书记C先是公开为受侮辱的B出头,后来却又因为嫉妒心与其翻脸,“揭发”B的作风问题,还演出一场“见义勇为受伤,不料却是苦肉计自残博出名”的闹剧;D个性爽朗,是月琴、篮球高手,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生下私生子;E有侠义和正气,指出C“英雄事件”的漏洞,是一片喧闹里难得的清醒女子。
因为和叙述对象比较熟悉,原型也都健在,金雁采用了半虚构的写法。
“你遇到这些女性时,自己还不到20岁。那时能明白那些人情世故吗?”

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
“好多事是后来才懂。当时商业局是(运动)‘重灾区。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她们都是‘高颜值女性。我那时小,又觉得那些运动是应该搞的,又觉得其实她们都是好人,有的還是我挺仰慕的人物。”金雁说。而雷颐从故事里读到的是,为了生存,各家有自己的门路、本事,“这就是在建构很复杂的社会关系。”
对俄罗斯和东欧风云变幻保持关注
1977年,金雁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苏俄历史专业硕士。哥哥和弟弟也同时考上本科。一门三人同时“中举”,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
滴水穿石。下乡的时候,金雁定期带着一个小木箱,只要回家便会换几本书,无非《鲁迅全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还有从老高中生那里搜罗来的俄罗斯小说,连高中的语文课本也反复摩挲了好多遍。本子则是自己裁切的纸张订成,读书笔记、书信、日记,什么都写。弟弟也时常拿食品去跟过去的老师换一些书,英文、数理化,拿起啥就读。没有功利心的求知,却为日后打下了基础。
不过,各类“全集”连篇累牍,如何克服枯燥感?
金雁说,总是可以超脱一下现实。“毕竟把自己放在历史当中,可能还会好一点儿。后来我们也谈起,说在那个年代,又不像现在这样什么信息都了解。我们为什么还要表现?那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因为你要抓住一个东西。不管它是虚无的还是别的什么,但有这个东西在,就比没有强。”
1990年代初在波兰访学期间,金雁透过自己的亲身观察,把东欧见闻带到国内。也实现了个人学术历程的转型:从研究一切“从哪里来”,加上“到哪里去”。“之前我觉得我跟时代一点冲突都没有,就沉浸在我的专业当中。后来才有了(研究转轨、关注现实的)自觉。后来有了一点感悟,也许我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给中国读者带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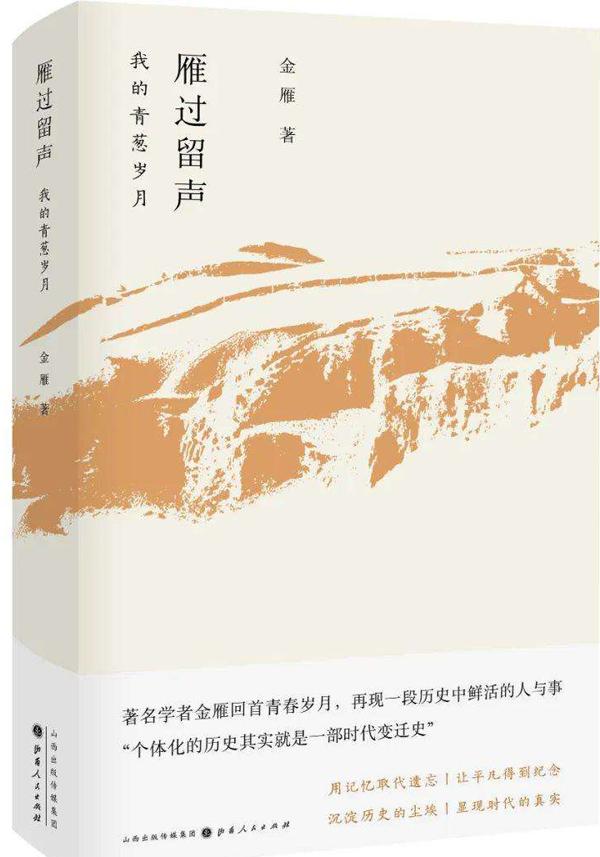
从回国之后写就的《新饿乡纪程》《火凤凰与猫头鹰》《十年沧桑》《从东欧到新欧洲》,到后来获得学术、读者双重口碑的《倒转红轮》等著作,再到今天,金雁始终对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的风云变幻保持关注。
文学评论家李静是在1980年代末念的大学。她说自己所属的70后是最早进入庸常时代的一代人,“再也没有大时代的轴心话语、轴心思想和轴心阅读,大家都比较分散,比较个人化和日常化,有点历史失焦的感觉。”她觉得幸运的是,那时受到过金雁、王小波等人思想观念的熏陶。“真正的思想烙印还是中国这些50后学者和作家给打下的。像金雁老师谈到的《路标文集》、路标学派,都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撑。”
而在《雁过留声》这本里,李静感受到了作者蓬勃的生命力。“那时候人对于环境的耐受力和从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是现在的人没有机会体会的。现在的人有点过于安全了,保护过度了,这是不好的。”
尽管如此,金雁认为,对逆境的抗争本身不能成为歌颂逆境的理由。
“你说回过头去,我要感谢和赞美那段生活吗?当然不要!”采访结束时,谈及此,金雁忽地肃然。“回忆和记录,是为了让人为阻断的历史不要失真,是为了我们不再犯错。”
按道理,此时的金雁是她自认为最好的时候。“想写的东西很多,再也不用被工作琐事纠缠,我特别喜欢资中筠先生说的一句话:我笔归我用。”
当欧洲一体化遭遇难民问题、民粹化,再到谁也无法把握的新冠疫情,当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未来会成何种走向?人类是否能够超越所谓激进与保守,去寻求真实的价值?金雁没有停止过观察和思考。
(参考资料:《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及该书线上读书会会议记录。感谢李占芾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