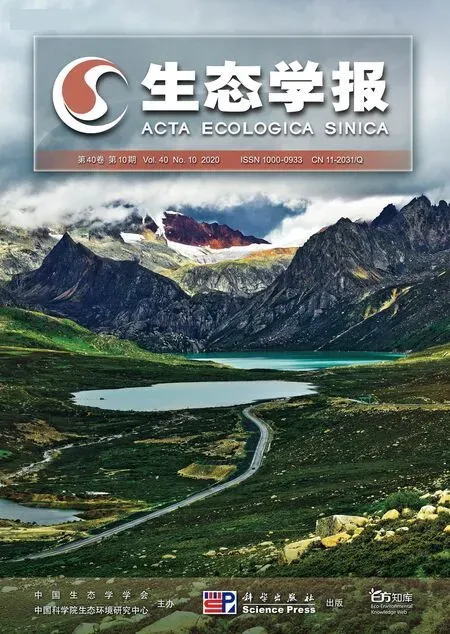基于景观格局-服务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以广州市为例
刘珍环,张国杰,付凤杰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2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州 510060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近年来为支持景观生态建设和管理而发展起来的有效工具,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愈来愈受到研究者和管理者的重视[1]。城市是景观变化的热点地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干扰[2],因此,完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可为景观管理和综合风险防范提供定量依据[3]。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关注对特定区域景观组分、结构、功能和过程所受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进行判定或预测,特别关注城市化、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下的景观生态风险[4- 5]。基于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互馈作用视角评价景观生态风险,可以揭示景观对风险来源的空间影响和应对措施[6- 7]。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受地理学研究生态化和生态学研究宏观化的影响,从生态系统尺度迅速扩展到景观尺度,评价对象由单一类型生态系统扩展到多种生态系统的空间镶嵌体[8]。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分支,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尚待进一步改进[9],特别是评价尺度变化导致生态风险评价在景观尺度上比生态系统尺度更难确定胁迫因子,而又比区域尺度更强调空间异质性,因此更关注景观的综合风险[10-11]。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常用风险源汇法和景观指数法,两种方法都遵循概率乘以损失的风险表征范式;景观风险源汇法关注区域内具有明确胁迫因子的特定生态风险[12],但多因子景观生态风险叠加的复杂函数关系并不清晰,难以区分不同因子间风险的相互影响;景观指数法关注景观镶嵌体相对于最优格局的偏离程度的生态风险效应[13-15]。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强调景观格局对风险的定量影响,通常将格局纳入评价要素,而将损失看作社会经济过程的结果,忽略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和生态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16],评价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经济脆弱度往往只能通过专家打分等主观方式开展,难以评估其不确定性。为避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单纯运用景观格局指数计算和堆砌[17],需要引入新的评价体系定量化脆弱度。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景观格局与过程的有效途径,也是连接人类福祉和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桥梁,其脆弱性与景观功能密切相关[18-20]。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异质性最能体现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最终后果,是定量景观脆弱度的最佳指示指标,将其纳入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定量化脆弱度,可以进一步对区域进行风险评估[6]。
城市是复杂的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1],其景观生态风险的特点是多来源和多受体的复杂暴露和干扰,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的相互作用及其带来的风险在城市高概率地综合涌现,亟待建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预警体系[22-24]。广州市是华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已成为我国典型的大都市地区之一,该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城市扩张的权衡是难点,洪水、热浪、水土流失、台风等自然灾害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居民健康造成较大风险,亟需探寻以景观为基础的应对生态风险的适应方案。研究该城市的景观生态风险及其变化特征,可为城市景观生态建设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源
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中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数字地形数据、土壤粗砂含量、粉砂含量、有机碳含量数据、广东省气温和降水产品等数据集,主要数据来源见表1。采用中分辨率遥感数据,经大气校正、几何校正、图像增强等预处理,采用最大似然监督分类和目视修正相结合的方法,将广州市分为农地、林地、城建、水体、草地和湿地六类景观类型。1990—2015年各期的整体精度介于85.33%—93.51%,Kappa系数介于0.81—0.93。

表1 数据源及说明
1.2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研究改进基于景观指数评价方法的景观生态风险模型,以景观格局指数表征景观干扰度,引入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指标定量化景观脆弱度,相关评价模型如下:
(1)
式中,LERk表示风险评价单元k的景观生态风险,Rk,i为风险评价单元k中景观类型i的景观干扰度;V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景观脆弱度;i为景观类型;N为景观类型数;Ak,i表示风险评价单元k中景观类型i的面积;Ak表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单元k的总面积。
景观干扰度指数(Rk,i)反映了景观格局变化造成的潜在生态损失和风险,研究运用风险制图方法,将风险小区定为1 km×1 km格网,其计算公式如下:
Hk,i=aCk,i+bNk,i+cDk,i
(2)
(3)
式中,Hk,i为风险评价单元k中景观类型i的景观干扰度,Ck,i、Nk,i和Dk,i分别是风险评价单元k中景观类型i的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在Fragstats 4.2软件中运用移动窗完成,a、b和c是各个景观格局指数的权重,公式内容及意义详见参考文献[25-26]。参考他人研究[27-29],结合城市景观变化的特点,分别赋以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和景观优势度指数的权重为0.6、0.3和0.1。
景观脆弱度指数(Vk,i)在以往研究中采用生境脆弱性[30]或专家打分法[31]确定,景观脆弱度越高,则景观功能越弱,景观对于各种干扰就越敏感,抵抗干扰的能力也越弱。采用基于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的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提供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景观脆弱度[32],计算公式如下:
VZk=VCk+VSk+VWk+VHk
(4)
(5)
VCk=NPP×(1-VCnpp)
(6)
VSk=NPP×(1-VCnpp)×(1-K)×(1-Fslo)
(7)
VWk=NPP×(1-VCnpp)×Fsic×Fpre×(1-Fslo)
(8)
VHk=NPP×(1-VCnpp)×Fpre×Ftem×D
(9)
式中,VZ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生态系统服务值,VC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植被碳固定量;VS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土壤保持能力;VW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水源涵养与提供量;VHk为风险评价单元k的栖息地提供量;NPP:植被净初级生产力;VCnpp:NPP年内稳定性因子;K:土壤侵蚀因子;Fslo:坡度因子;Fsic:土壤入渗能力因子;Fpre:年均降水量因子;Ftem:年均气温因子;D:地表粗糙度因子。NPP计算采用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模型),其中NDVI数据采用两种数据产品,2005,2010和2015年采用500 m分辨率的MODIS-NDVI数据;1990,1995和2000年采用Landsat TM计算的NDVI值并重采样至500 m分辨率。将景观生态风险值归一化并制图,按照自然断点法[26,33]将风险等级划分为极低风险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四级。
2 结果分析
2.1 景观干扰度分布及变化
广州市景观格局干扰度空间分布显示(图1),广州市景观干扰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南部和西部,低值区则集中于北部和东北部,表明广州市景观格局所受干扰强度南部大于北部、西部大于东部。从时序上看,2000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1990—2000年,景观干扰度逐渐增强,中干扰度和高干扰度占比之和由28.16%上升至48.39%,南部干扰度上升最明显,西部和东南部干扰度也有一定的上升趋势;2000—2015年,景观干扰度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到2015年,中干扰度和高干扰度比例之和降为31.13%,北部和南部干扰均有降低。1990—2015年,低和极低干扰度比例之和由71.84%变为68.87%,等级占比相差不大,但空间分布趋于破碎化。25年间,景观干扰度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小的过程,这与城市扩张由粗放转为精细,注重城市内部结构调整有关。
2.2 景观脆弱度分布及变化
由图2可以看出,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功能脆弱度逐渐上升,中脆弱度和高脆弱度占比之和均维持在60%以上,高脆弱度比例增加明显。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高脆弱度地区集中在南部,中脆弱度地区广泛分布于北部和东北部,低脆弱度和极低脆弱度地区聚集在广州市北部区域的行政边界交界带附近,以山地丘陵为主。近25年,景观脆弱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城市发展显著降低了中心城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也削弱了建成区周边景观的抗干扰能力。
2.3 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
图3展示的是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景观生态风险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总体上广州市以低风险和极低风险区为主,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有所增加,25年间,中风险区增长幅度为5.78%,高风险区变化幅度超过50%,说明景观变化主要造成高风险的提升。2000年是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的转折点,前10年风险趋于增大,后15年风险趋向降低。低风险和极低风险区占比最大为1990年的76.52%,最小为2000年的55.16%。极低风险区景观以大斑块林地为主,主要分布在与天河、白云和黄埔交界的白云山区以及增城和从化;低风险区景观以农业用地和林地为主,少量草地和滩涂湿地。中风险区的整体变化趋势表现为2000年最高,占25.24%,覆盖范围主要是城市建成区及城郊建设用地区、农业景观分布区。高风险区在2000年比较突出,占比19.61%,主要分布在南沙万顷沙、番禺与南沙交界带、番禺与海珠交界带、白云区和花都区的城乡交错带,是城市蔓延的主轴,少量分布在荔湾和天河等地的城市开发建设区,如荔湾的广钢新城、天河区东部,还有少量分布在湿地滩涂景观中。

图1 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干扰度空间分布图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disturbance in Guangzhou during 1990—2015

图3 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Guangzhou during 1990—2015

图4 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图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changes in Guangzhou during 1990—2015
2.4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特征
运用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图4),近2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保持低风险(低和极低风险)以下的比例为40.74%,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高风险(中高风险)的比例维持在6.67%,主要分布在南部的番禺和南沙。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比例为32.28%,分布在城市边缘带和城乡交错带,包括花都、白云、从化、增城、天河北部和番禺中心区。由高风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20.31%,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荔湾、海珠、越秀和天河南部,这25年间景观生态风险的变化反映了景观城市化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景观干扰度与脆弱度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改进脆弱度的评价方法,选取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提供等4种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定量表征脆弱度,构建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采用1990—2015年广州市的多源数据,分析了城市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及变化特征,基本结论如下:
(1)25年间,景观干扰度经历了先增加后降低的过程,2000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1990—2015年,景观脆弱度不断增加,抗干扰能力下降,中脆弱度和高脆弱度占比之和均维持在60%以上。景观干扰度和景观脆弱度在空间分布上均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
(2)1990—2015年广州市景观变化明显,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格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以低风险和极低风险为主。2000年是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的转折点,1990—2000年间景观生态风险趋于增大,2000—2015年间景观生态风险趋向降低。
(3)近2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与景观变化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低风险区比例保持在40.74%左右,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而高风险的比例维持在6.67%,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比例为32.28%,由高风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20.31%,反映了25年间景观城市化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
3.2 问题讨论
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一直以来重点关注景观格局导致的生态风险,对于景观功能的易损特质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研究尝试性将生态系统服务引入表征景观功能的脆弱性,用于评价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生态风险,改进基于景观指数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从评价结果看,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比单纯的景观格局指数法更容易刻画城市景观变化引起的风险,也更容易空间化景观生态风险,减少了主观定量过程,提升了生态风险制图及评价的可信度。然而,以下两点仍需要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一步关注:(1)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缺少验证,降低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可靠性。(2)风险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难以圈定特定的防范区。例如广州市主要的景观生态风险防范应在南部中心六区和西部的白云和花都区,然而这种景观变化带来的风险会随着景观变化而变化,只能表征当下景观生态风险,不能够预测和预警未来的景观生态风险。为此,需要通过时序变化来探寻景观生态风险的演变规律,再辅助以情景变化,方可为景观生态风险的具体应用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