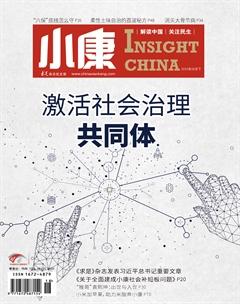城乡一体化驱动乡村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其要点包括: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等等。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项目执行研究员
上述部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对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治理区别对待,也没有出现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等乡村领域的专门性概念,而是使用了“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市域治理”等表述。这意味着,在推进治理现代化问题上,中央的精神是对城乡基层治理进行统筹考虑。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并不是要构建一套区别于城市的特殊的治理体系,其前途与目标是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途是城乡治理一体化
城乡治理一体化实际上是世界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社会治理是通过配置公共资源以构造乡村社会经济秩序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城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主要发达国家很少有区别于城市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只是作为一种区别于城市的自然空间、生产空间而存在。欧美等国主要依据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和经济通联等指标来划分城乡,但划分结果只与特定产业政策的投放相关,而不会据此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
历史上,中国乡村人口数量庞大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这是形成特殊乡村治理体制的经济根源。尽管中央作出了城乡治理一体化的战略部署,但当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特殊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现阶段为了理解和分析的便利,在相当长时间里仍然要沿用乡村治理这个概念。但在运用这一概念特别是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时刻不能忘记城乡治理一体化这个根本目标。
乡村发展中的若干趋势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人口布局发生质地之变。人口布局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人多地狭不但会导致农业生产的过密化从而阻滞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普遍贫困还会强化乡村社会依附性关系,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障碍。正常的农业生产不需要大量人口堆积在村庄,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以后,大部分农业村庄将不复存在。乡村治理現代化有赖于乡村人口大幅减少条件下城乡人口布局的结构性转变。从世界经验看,一个国家的乡村人口比重降低到25%以下,农业人口比重降低到10%以下时,城乡关系将实现均衡。近20年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乡村人口比重、乡村就业人员比重和农业就业份额都大幅下降,城乡人口布局发生质地之变。当前,我国乡村人口已经降低到40%,农业人口已经降低到20%以下,乡村治理现代化具备了初步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专业农户阶层日渐崛起。近几年,特别是在传统农区,一个最显著的发展变化就是专业农户的崛起。专业农户具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高、经营收入高等特征。据笔者估算,当前活跃在规模种养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的专业农户数量已经超过1500万户,且还在不断增长。
第三个特征是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土地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密切,特定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型塑不同的产权秩序,从而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结构性变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围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作出若干重大部署。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正式确立,农村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一系列改革带来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乡村经济活力的增强。特别是在前述改革基础上,中央对广东、浙江等地探索多年的“政经分开”改革予以认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尝试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分开运行,实现了产权管理与社会治理的专门化。这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不可估量。
第四个特征是全面脱贫改变乡村结构。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从全国形势看,脱贫攻坚胜利已成定局。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脱贫攻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把乡村中处于最底层的、最困难的人群直接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短时间内实现乡村社会结构的全局性调整。绝对贫困消除,一方面意味着乡村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大幅缩小,另一方面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乡村人口和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社会化分工体系。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促成了乡村现代性水平的普遍提升,这将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开辟新空间。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多样性不相适应。近年来,各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正规化。但在实践中,正式的治理体制却无法直接导入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传统农区和山区的许多村庄,人口外流严重,常住人口早已难以支撑村庄组织建设,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乡村治理正规化是无从谈起的。而对于很多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而言,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产业特征来说,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城市形态了。这个时候,再赋予其一套区别于城市的乡村治理体制,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第二,城乡空间布局阻碍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一般来说,现代化的乡村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人口1—3万人的小城镇中,而专业农户则靠近地头相对分散居住。从国际经验来看,处于城乡之际的小城镇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特别是承担着周边乡村的教育、医疗、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功能。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大量脱离农业的人口无法向城镇转移或者适度集中居住,只能继续居住在分散的自然村落中。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遍地都是千八百人的中小规模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十分低下;另一方面,大量的乡镇驻地人口不足万人,无法形成人口聚居的规模效应。人口和资源分散,中心镇区的专业化水平也就上不去,难以发挥带动整个镇域进入专业化市场分工的节点作用。这样的布局长期得不到调整,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与中央提出的“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去甚远。
第三,产权秩序阻滞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尽管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但制约城乡之间人口和土地等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仍未根本消除。尤其是,进城农户在农村各项权益的“退出权”没有得到实质性落实,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麻烦。城市这一头,进城农户无法将农村权益变现,也就无法将其作为进城的启动资金;乡村这一头,真正从事农业的专业农户流转土地的交易成本高昂,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提升。此外尚有很大一部分村庄没有很好落实承包期内不调整承包地的法律规定,频繁的土地调整造成了不少冲突事件。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出在土地产权制度上,不解决这个问题,乡村治理现代化没有指望。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走乡村善治之路
第一,科学划分村庄类型,分类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改革。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达到市(镇)规模标准的村庄组织逐步转置为城镇政府;分散居住在开放式乡村的专业农户归属到附近的市(镇)或村庄管辖,不再建立专门的政治或者行政组织;衰退型村庄设立过渡期,不强行增加村级组织规模,只保民生底线。
第二,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提升镇区服务带动能力。调整人口布局,引导脱离农业的人口逐步向小城镇集中。教育、医疗等基础性公共服务向镇区集中,乡村道路建设资金优先用于确保居民点与中心镇区的联通性,周边乡村居民通过校车及公共交通分享专业化服务。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启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集体成员权(益)的“一揽子”退出改革,鼓励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上述权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再造新模式,允许打破既有集体经济组织边界,通过合作社等形式组建跨社区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以凉山州同城化区域“一市三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