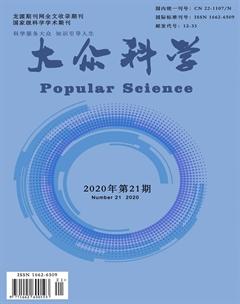行之若木
刘笑笑
人是一棵会行走的树。
走到哪儿便扎根到哪儿,接受那儿的阳光雨露,偶尔念念自始至终的故土,想想自始至终的木。
我希望人的本质是木质,只会生长和摇曳。
可是,人需要时便把自己造成弓箭,猎杀鸟鹿,需要时便把自己劈成斧子,砍下其它的树;需要便把自己造成舟车,一定要快过其它行走的树。
行走,未尝不是一种奢求。
行走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就必定有它的作用。
脚是人的有感觉的一部分肉体,大地是世代立足的根基,无论走到哪里,还在大地之上;无论飞有多高,仍要回归大地。
我惊叹于西亚的朝圣者,三步一跪拜,五步一叩首,朝着日落的方向,硬是一步一步捱到麦加,捱到了耶路撒冷。曾经看过一本书中写到:这些朝圣者有很多死在了朝圣的路上,死的时候脸依然朝着西方。我很是不解,不明白意义何在,但如今我想通了一些,朝圣者无论死亡,都一步一步用双足踩着大地把自己的心送上了回家的路。
这是一种信仰。
中国自古以来,苦行僧好像已经成了形容词。但略微区别于西亚——他们的路更难走。西藏冰原,脚下的冰冷,头上的炽热,即使从阳关到拉萨仅垂直落差便三千米。近万里的徒步跋涉,从白走到黑,从南走到北。我告诉爸爸,我们若是开车去西藏,路上一定要載他们一程。爸爸抿嘴没有说话。几年后,我在翻阅一些旅行者的记录时,发现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了同一件事---不要载朝圣者。说这些苦行僧朝圣者要的是走出一条通天之路,并不需要任何搭载,只是建议驾驶者遇见他们给他们留下一块面包几瓶水即可。让他们在朝拜的路上,一路苦行。
这是一种回归。
有时候,足下的力量不容忽视,也无可比拟。
近现代以来,天上地下水中都有了人的不知疲倦、神通广大的座骑,连外太空也没有漏掉。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世纪以来,人类登顶珠峰一个又一个,然而并没有哪一个是车送上去或者飞机扔下来的。这种极限的所在人类并非不能征服,而是除了他们自己再也创造不出更先进的机器。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点雪中,再高的山峰两脚攀登,再陡深的谷双足丈量。最豪迈的事不是登顶,而是成峰。
《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他们到过一个地方,这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殖民地。这儿的人靠采珠为生,潜入到水下20米的地底,近海珍珠盛产,而对于他们,一公斤的蚌珠只能赚一美元。做这一行当的人不长命,却总是有人前赴后继,因为他们被需要;为什么被需要?因为除了人工,没有任何机械可以代替得了。
这是一种天赋。
一个纯人声清唱组合的介绍中提到过一位音乐大师说过的话。人名我早已不记得,可是他无论是谁他说:“人类的嗓子是这世上最美妙的乐器。”人身体上的任何结构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和脚一样,承载着无与伦比的使命,也值得被重新认识,重新生命。
无论是拉萨的雪还是阿拉伯的沙,朝圣者风雪载途,风尘仆仆,立地风化为一个小丘;无论是登峰者还是采珠人,每一步都踏得大地神经震颤。沈从文说:“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触地,表示皈依真主。意思是如此一来,虽不曾接近真主,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人是一棵行走的树,
扎根于热土,生长于大地,
吐出最后一口浊气。
赤脚行走。